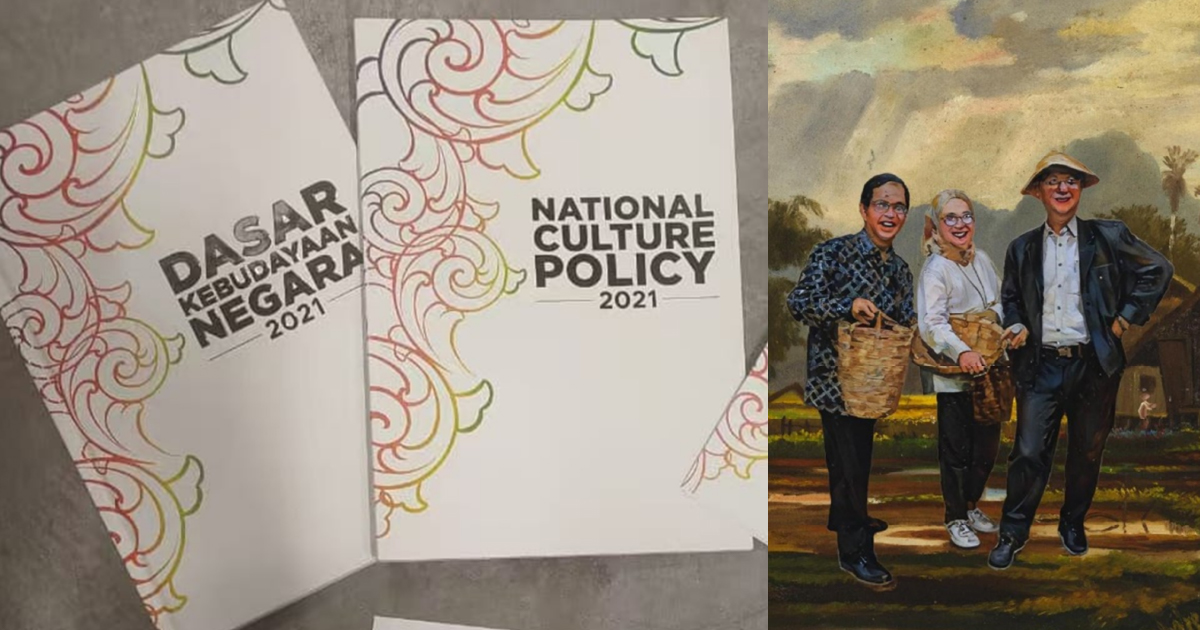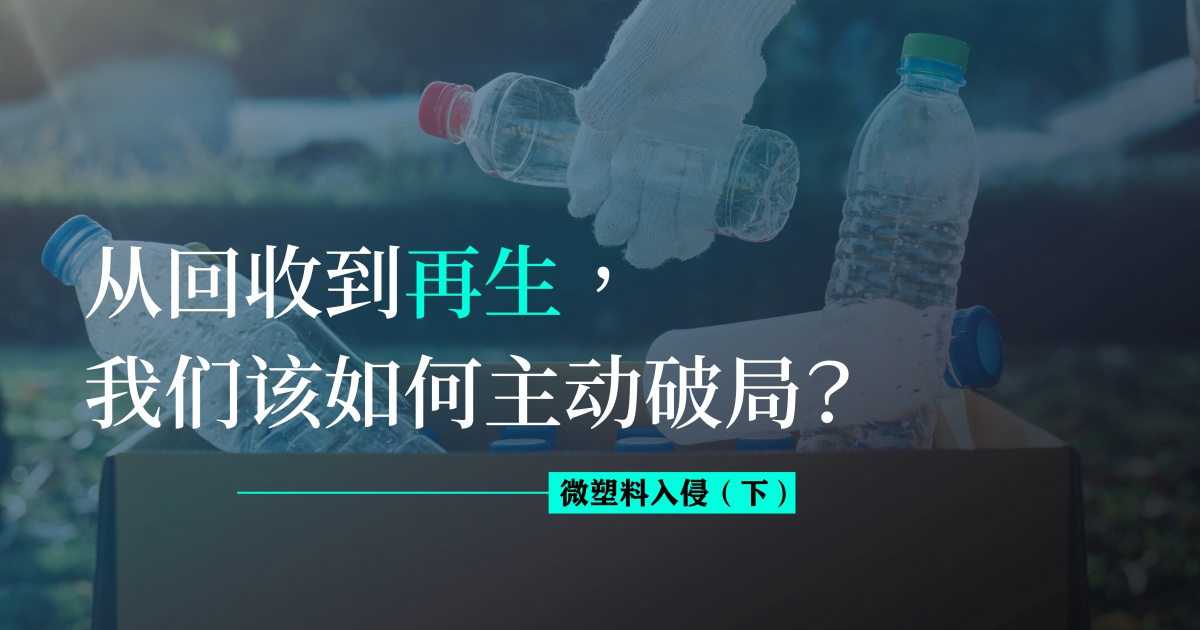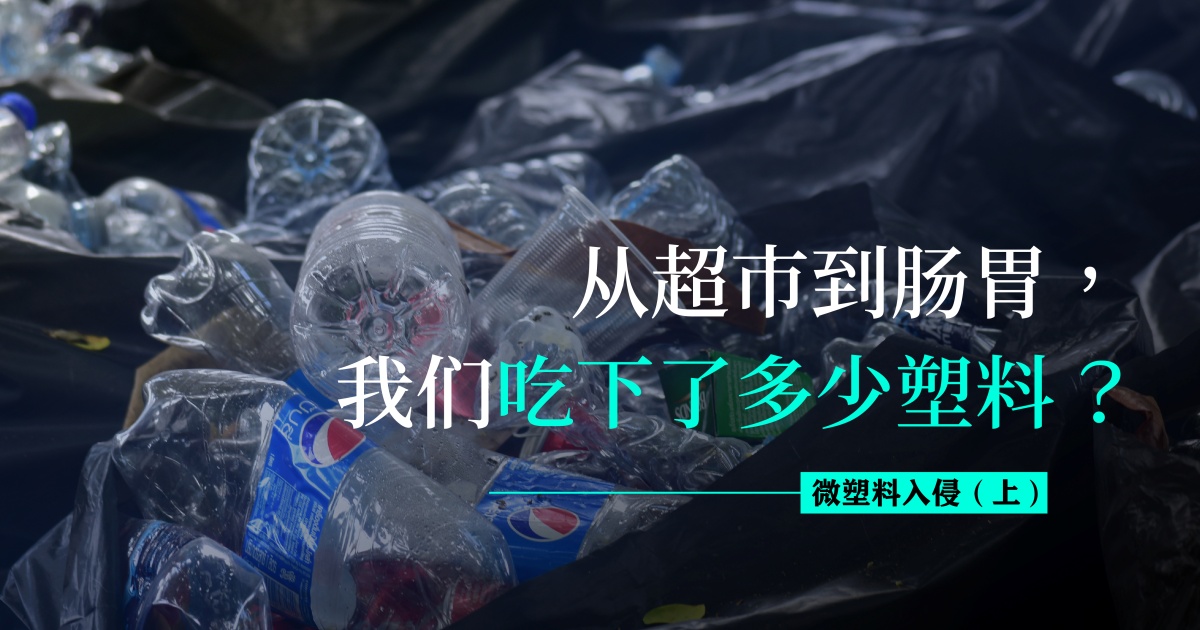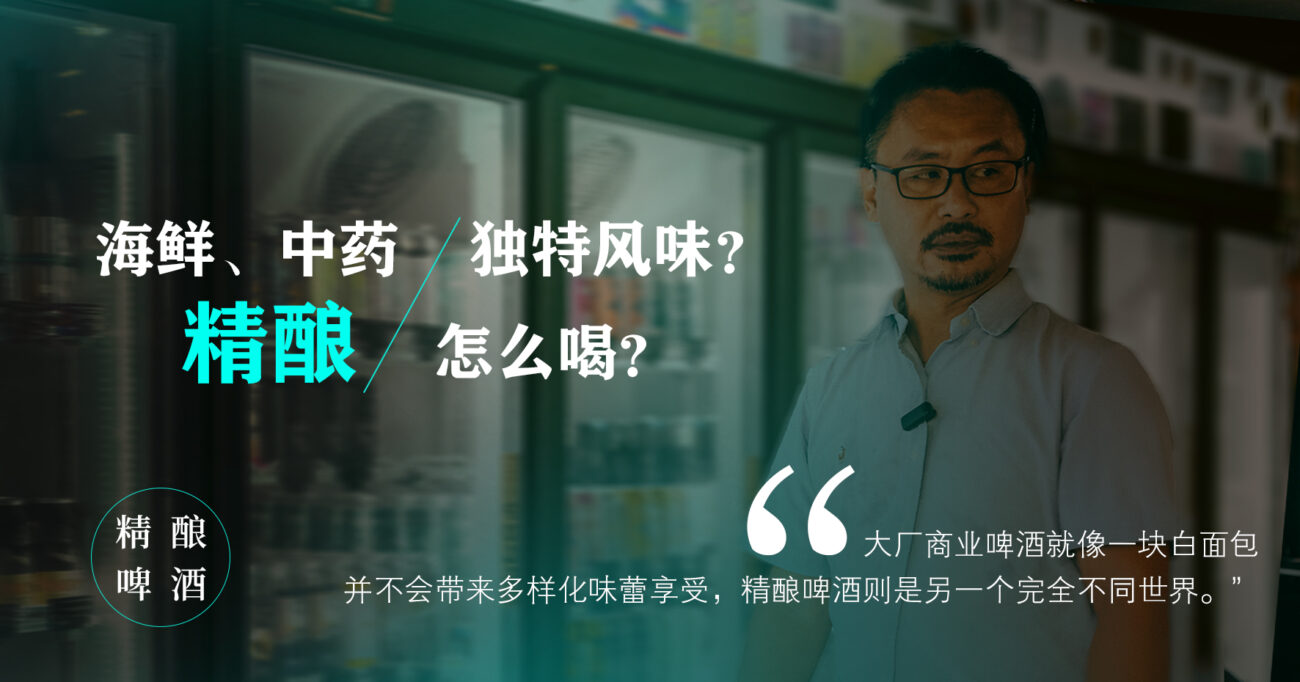2025年6月11日至12日,我有幸参与马来西亚国家文化理事会在吉隆坡举行的第一次实体会议。虽然此前我们已举办过两轮线上会议,但唯有亲身参与面对面的讨论与交流,才能真正感受到文化工作者之间沉甸甸的责任感与使命意识。
在本次会议中,我们不仅重温了《国家文化政策》(Dasar Kebudayaan Negara, DAKEN)自2021年发布以来的理念与目标,也坦诚探讨了其在多元族群社会中的落实路径与挑战。而我在会上不断思索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文化政策如何真正走入人民?如何让它不仅存在于纸上,更融入人民的日常生活?为此,我愿以两个看似简单却意味深长的概念作为回应的主轴:文化人生与人生文化。

“文化人生”指的是个体在人生旅途中,如何在国家文化价值体系中被滋养、被引导、乃至被成就。此概念强调国家通过制度、教育、媒体、礼仪等多重途径,潜移默化地影响人民的价值观、行为方式与生活态度。
DAKEN明确提出“高价值文化”为发展主轴,包括礼貌、公正、诚信、敬老尊贤、热爱知识等核心价值。这些价值不只体现在学校的德育课程和公务制度的服务标准上,更体现在人们日常应对进退之中。政策的目标并非“教人做文化人”,而是“让文化成为为人处世的根本”。
在“文化人生”的构建中,国家的角色至关重要。一个国家若无法在文化上塑造有尊严、有责任、有品格的公民,即使拥有经济成就与科技飞跃,也将失去深厚的精神支柱。文化不仅是“软实力”,更是支撑国家认同的“硬支柱”。
当然,我们也必须警惕陷入单一化的“文化统一论”。多元文化是马来西亚的根本特色,国家文化的建构不应抹去差异,而应在差异中寻求共通的价值。DAKEN清楚指出,国家文化不是民族文化的替代,而是促进各民族文化对话与融合的平台。文化人生的理想状态,是每个族群都能在国家文化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并因其而贡献、因其而自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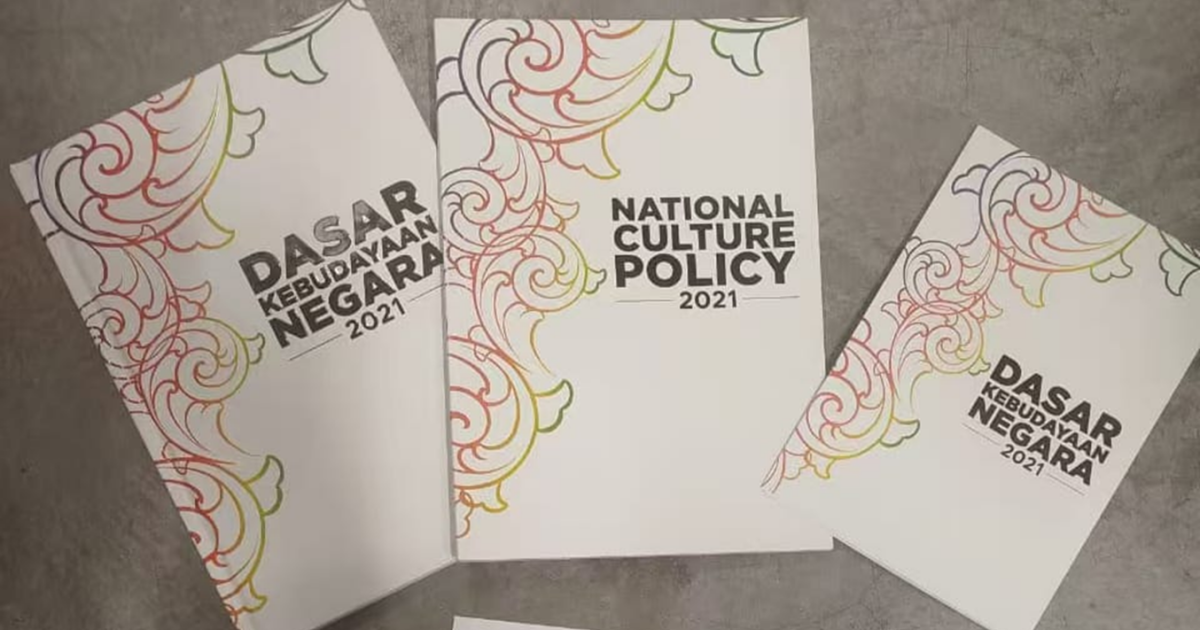
另一方面,“人生文化”强调文化的生命力并非源自政策,而是深植于人民的日常生活。文化不是自上而下的灌输,而是自下而上的创造;不是仅存在于文告、节庆或礼堂,而是在厨房、街市、田园与网络中自然流露。
马来人烹煮传统佳肴、华人延续节日习俗、印度家庭点亮节日灯饰、原住民族传唱古老歌谣——这些都不只是“表演文化”,而是真正“活文化”的体现。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是文化的建构者。
DAKEN所倡导的“让文化归于人民”,是一种对人民文化主权的肯定。文化不是政府的行政方案,而是人民的生命轨迹;不是静态的展品,而是日常中的活态表达。
尤其在偏远村落、B40群体、新村或长屋中,我们常能见到许多未经“官方认证”却充满美感与生命力的文化实践。虽然未被记录于文化数据库,但正是这些朴素而真实的生活,构成了马来西亚文化深厚的根基。

与此同时,年轻世代也在不断创造属于自己的“人生文化”。他们透过TikTok讲述族群故事,以本土语言创作歌曲,以手绘、摄影或时尚重新诠释传统。这些新形式并非对传统的挑战,而是其延续,是用新时代的语言讲述祖辈的记忆。
在“文化人生”与“人生文化”之间,最关键的是互动与连结。政策不能只是单向推动,人民也不应只是被动接受。文化既不应仅是纸上文件,也不应只流于感性情怀。要真正建构属于马来西亚的国家文化,必须推动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双向互动。
在这方面,DAKEN已展现前瞻性的规划,例如推动文化经济、提升基础设施、支持地方文化人才、建立文化创意产业生态等。然而,所有政策唯有深入社区、融入人心,方能真正发挥效用。
作为国家文化理事会的一员,我深感自己肩负着三重角色:一是翻译者,将政策语言转化为群众语言,把文化愿景转化为生活实践;二是连接者,将基层文化工作者的声音带入政策讨论,使文化教育与政策制定形成对话;三是守望者,守护那些濒临失传的乡音、技艺与精神,并唤醒它们的生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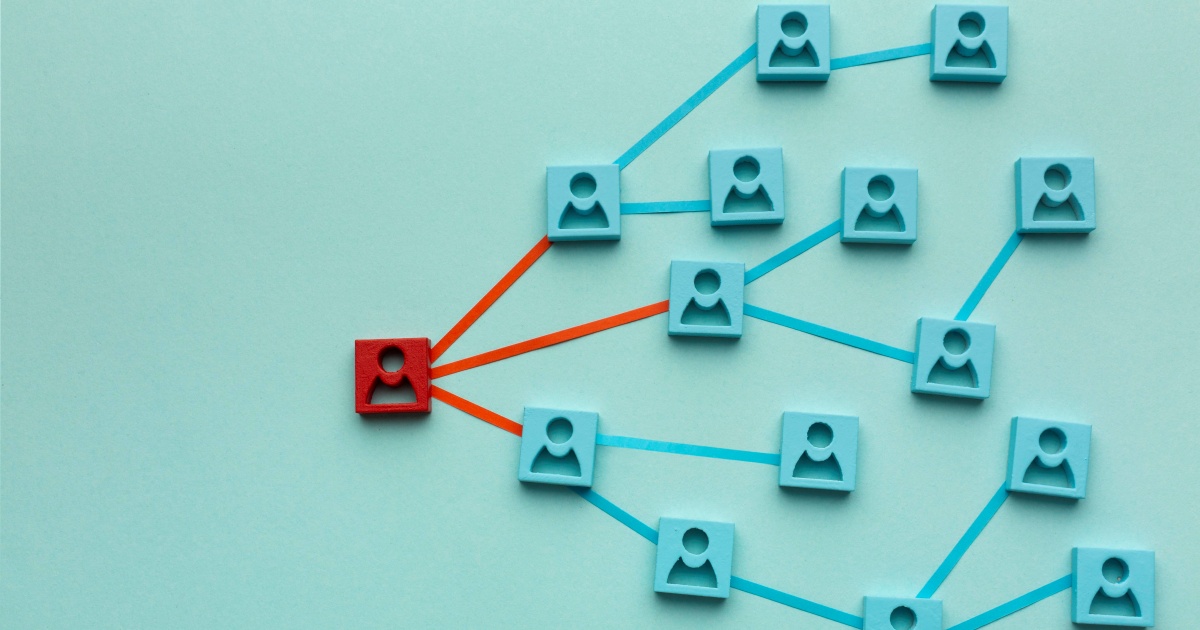
我们可以构想更多“生活中的文化政策”:在校园开展地方文化艺术周,在媒体平台推广本土文化创作者,在节庆活动中鼓励文化共创,甚至通过数码平台赋能青年,让他们成为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新中坚。
衡量文化政策成效的标准,不应只看活动次数或预算规模,而应看它是否真正让人民更热爱、理解并珍视自身的文化资产。
文化不是展示品,不是装饰,也不是节庆时的点缀。文化是我们如何说话、吃饭、行走、思考与相处。它不是“装出来”的,而是“活出来”的。
当国家文化能被人民内化为自我认同,当人民文化能被国家接纳为政策资源,“文化人生”与“人生文化”便不再是两个概念,而是一个融合的文明生态。
让我们继续前行,作为政策制定者、文化实践者,也作为马来西亚人,一同走在这条双向的文化之路上,把文化活出来,把国家爱得更深。
▌延伸阅读:张炳祺专栏《乐活系述》其他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