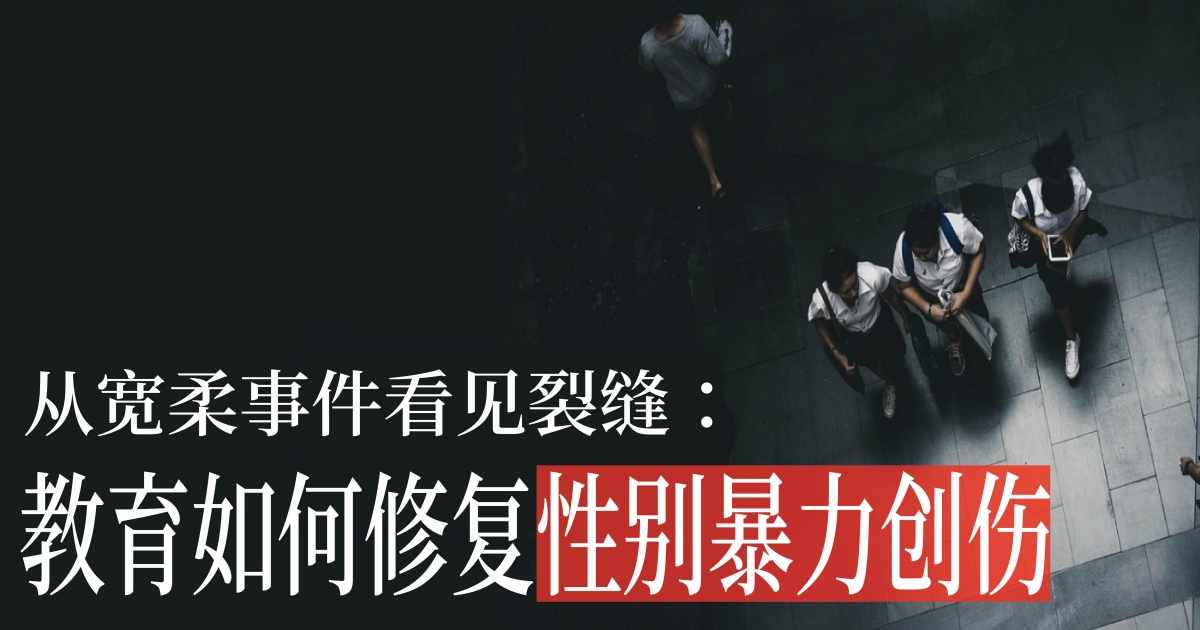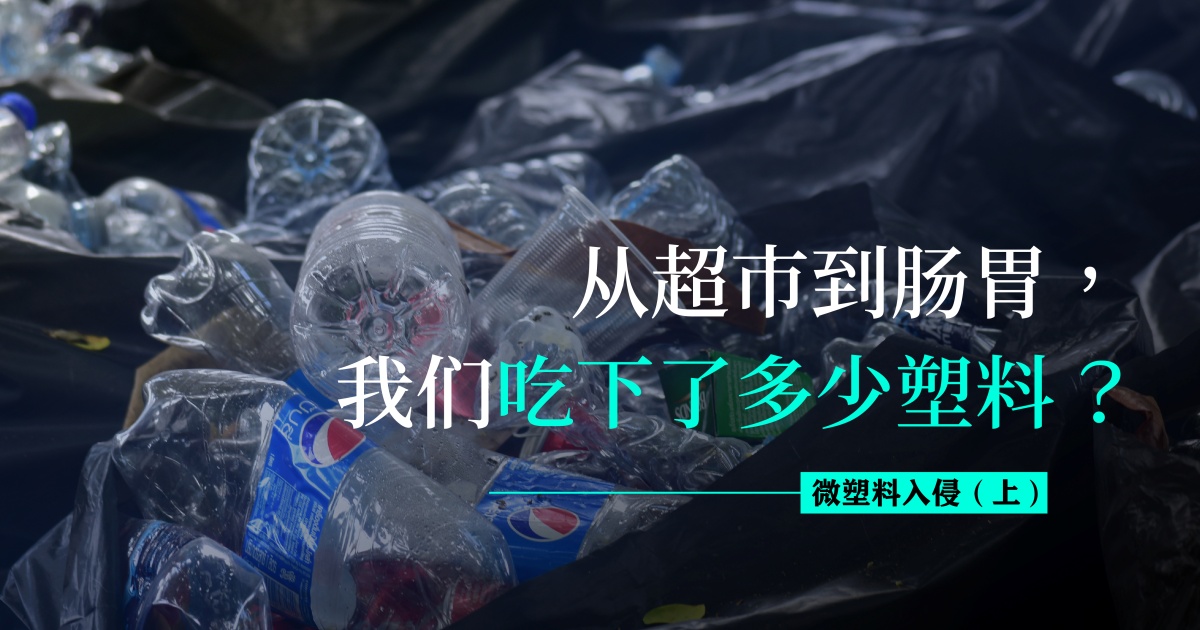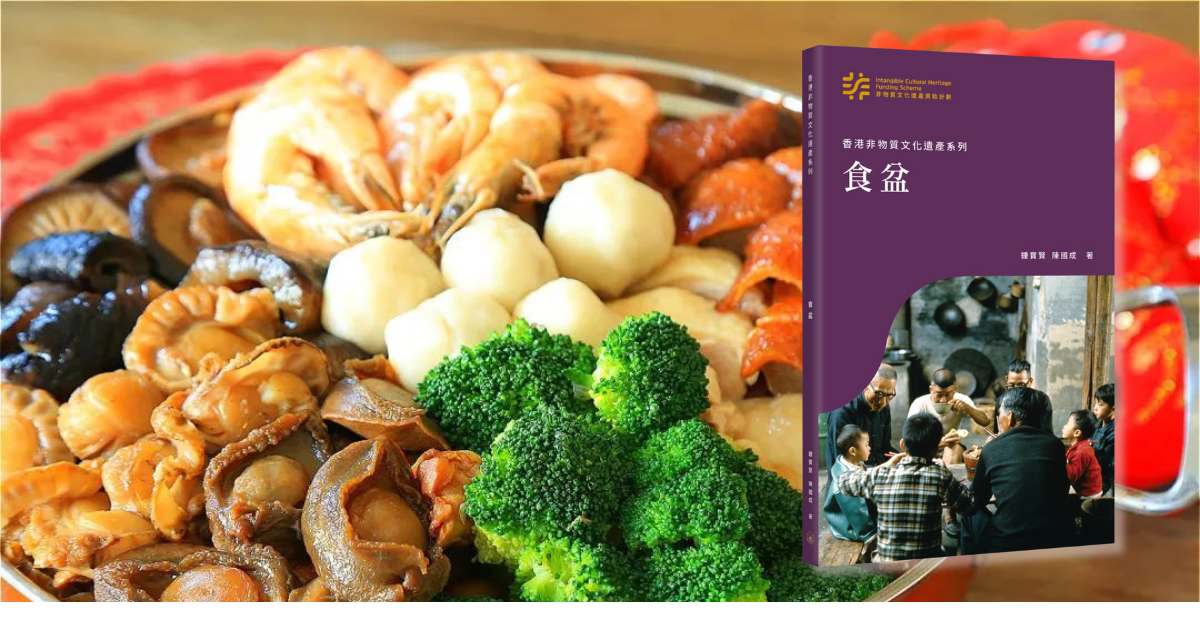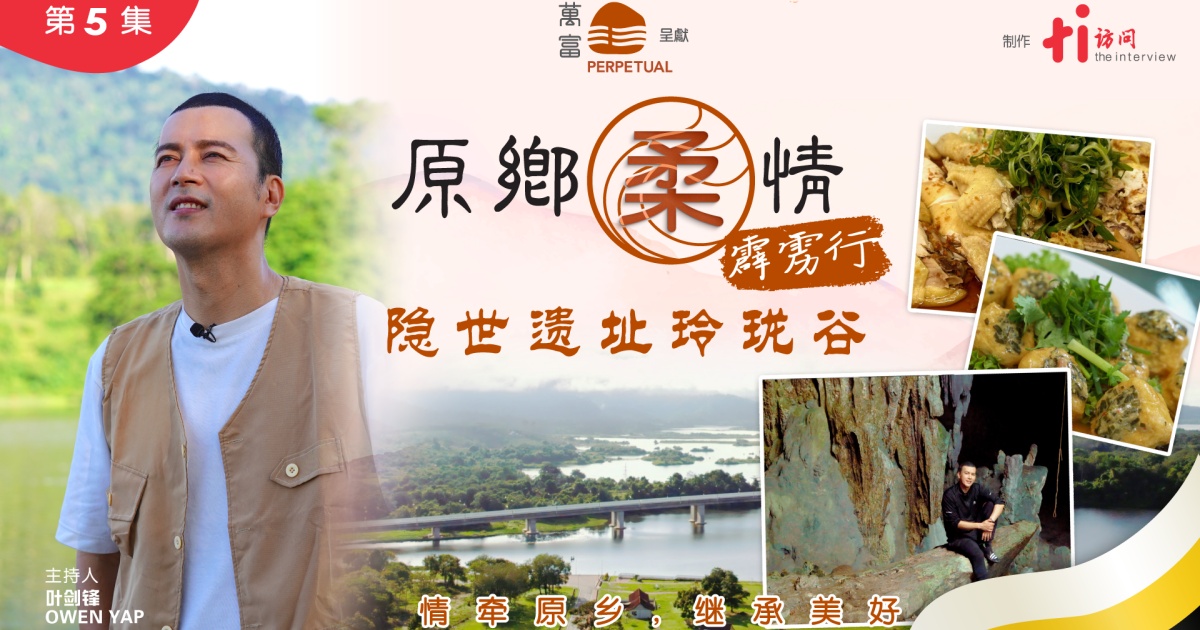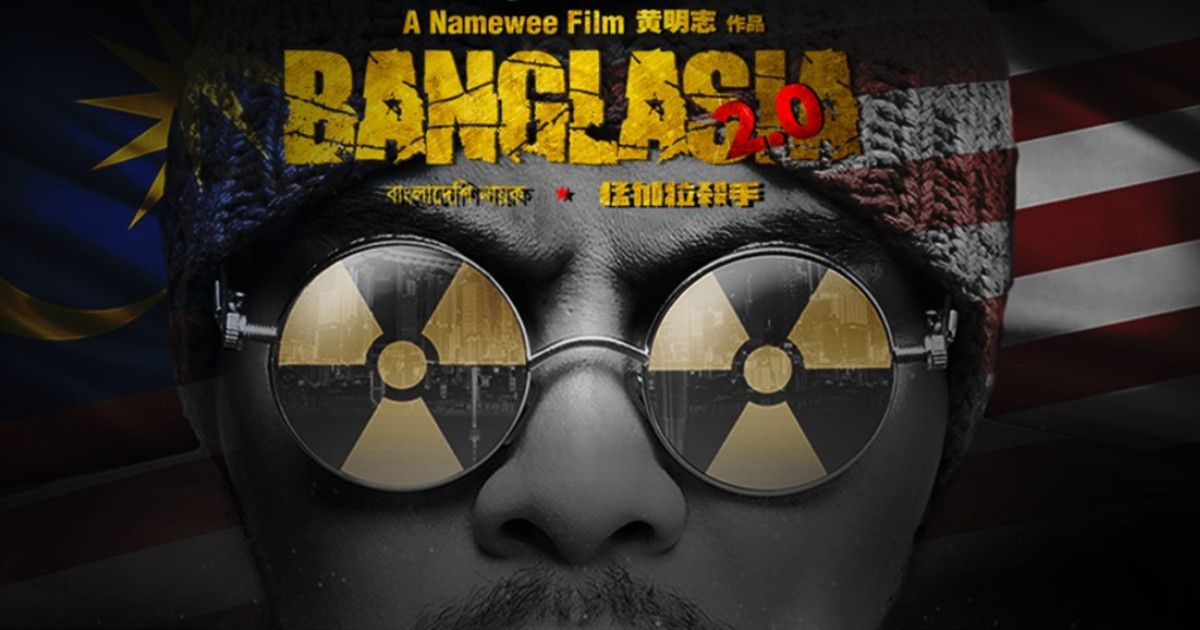留台,长期以来是马来西亚独中生重要的深造管道,历届留台生返马后投入华教领域者也为数不少,在中文教育与文化传承的“道脉”承续上扮演积极角色。然而,这种积极性的发挥并非恒定不变,而是随时间推移,呈阶段性的起伏。与此同时,留台生的参与并不局限于语文教育,亦涉及多元专业领域。

以我的母校新山宽柔中学为例,自1970年代后半期以来宽中校务已是稳健发展,学生人数逐年暴增。当时的宽中师资结构,新加坡南洋大学与留台背景师资可谓平分秋色。惟就音乐、美术与体育等领域则几乎完全由留台师资承担。1970年代以降,宽柔中学在美育、体育与表演艺术等方面的优异表现,深受留台师资的影响,扮演奠基角色。包括后来获颁国家文化人物的陈徽崇老师、画家贺金泰老师等,皆为1970至1990年代宽中的杰出“名师”。在美育与课外活动领域,留台师资之贡献卓著。
就我个人的求学经验而言,印象很深刻的是初中二那年,受教于贺金泰老师。贺老师在美术课中教我们立体广告设计,并经常会将学生的优秀作品展示于课堂,现场阐释其中之美感所在与技法优劣,且还借此进一步引介色彩学的基本原理。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初二某一时期,他特别鼓励学生尝试水墨画。当时我仅是很随意以数笔勾勒作画一幅花叶树木,作品虽简笔而成,但因其“留白”与色彩运用而获得老师肯定,并公开展示评析。此一经验倒是成了我的艺术启蒙的重要记忆。及至今天,我在大学中文系讲授《中国文化概论》,亦时常会在白板几笔潇洒作画,跟学生解说中国美学之“留白”与虚实黑白的关系,其基础认知正是奠立于当年宽柔中学初中阶段贺金泰老师的美术教育。虽然当年我并未代表学校参与任何的美术竞赛,但由贺老师当年引导所培养之美育素养(对欣赏美与理解美的鉴赏能力),至今仍然受用无穷。贺金泰老师的美术教学,不仅注重技法,更以“留白”“虚实”等美学观念,引导学生体认中华艺术精神。此种教学实践,使美术课程超越技能训练,成为培养审美感知与文化理解的重要场域。上述的个人受教经验显示,大马华校美育的意义不仅在于陶冶性情或提升艺术修养,更在于其承担了文化启蒙与身份认同建构的功能,对于学生的长远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然而,需要说明的是,留台生返马服务华教,有其时代因素及双向变迁的影响。亦即在不同时期,既有大马本土的政经文教气候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不能忽略台湾的政经社会文化演变的因素。台湾“侨教政策”的演变,台湾民主化进程,都会是影响留台人在返马后对华教投入的热度。进入1980年代至1990年代,旅台大马青年感染于台湾学术和民主化进程,并有感于大马时局的困惑与寻路,而把目光回望自己的乡土马来西亚,舍我其谁,“回国”是要以“言论建国”、以“学术建国”,意识很强烈地要为马华文化尽一份力,却因内在的民族情怀,让当年的大马留台青年的认同意识常在土地(马来西亚)与民族(华人)之间挣扎,却也有着民主人权意识和理想的渲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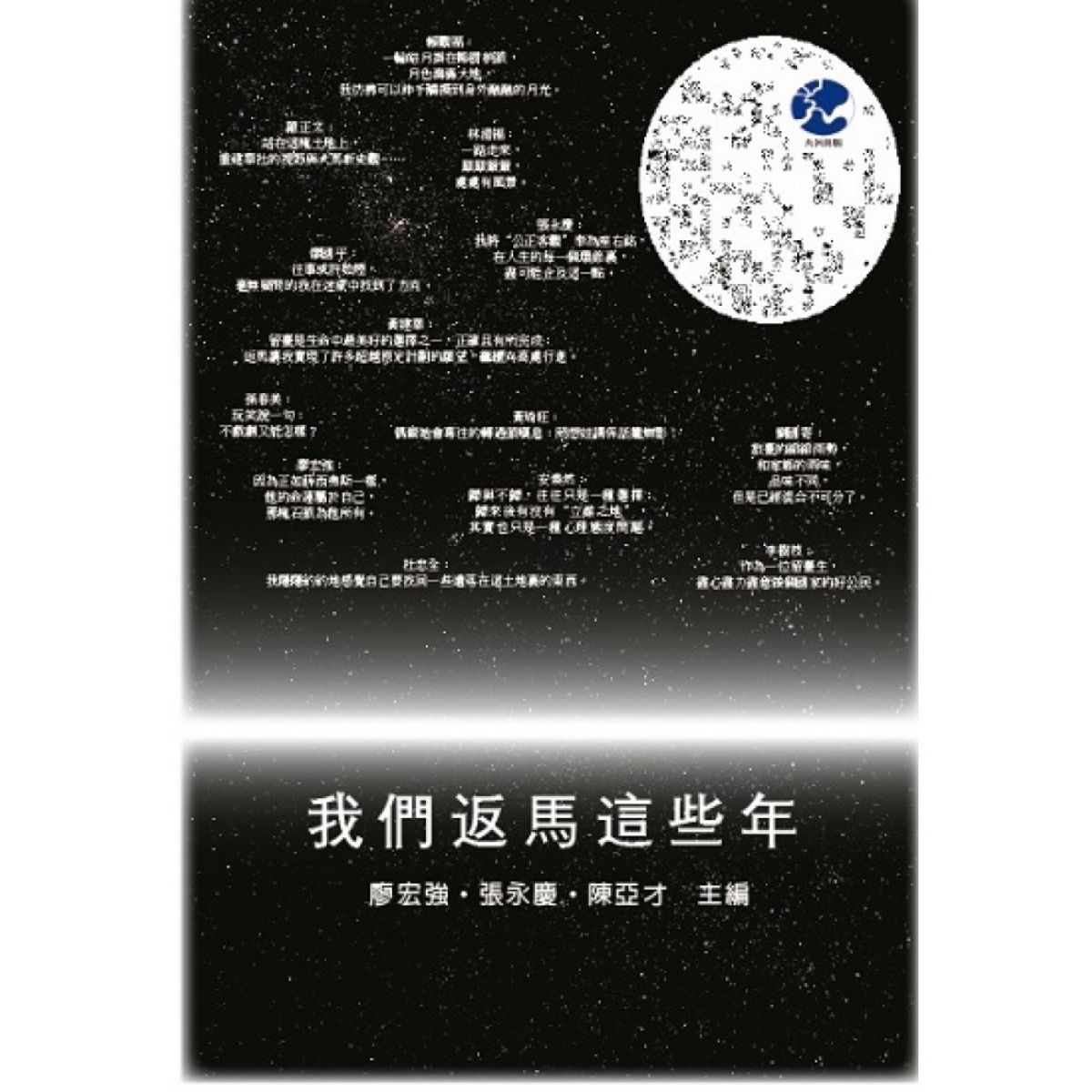
廖宏强、张永庆、陈亚才主编的《我们返马这些年》(居銮:大河文化出版社,2018)大抵反映了我们那一代留台人返马,积极投入华教运动及文化事业者不少确实有一份赤忱之心,具有强烈的华教意识。
然而,随着近年来各种升学深造管道的多元选择和“市场竞争”,台湾侨教政策的滞后,大马留台生已大为锐减。加之于碎片化、个人化,集体意识的涣散,近来甚至因发生“ME TOO”校园性平事件,引发的“怎么又是留台(老师和学生)”的舆论,留台人还能延续“华教”之主导角色吗?间中到底又是什么因素在发酵?是误读,是不满,还是“事实”?
▌延伸阅读:安焕然专栏《五味杂陈》其他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