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作家要出新作品,大家自然会联想到新书。但2020这年,作家可能要出不是书,而是一张音乐专辑。周若涛、王修捷和龚万辉,三人都是马来西亚优秀的作家,但书写文字不是他们唯一的才能。由周若涛创作、王修捷谱曲和龚万辉绘画的《神秘之歌》,从一本2011年出版的诗集摇身一变成了一张诗曲画像的专辑,十首诗谱上了曲,同时也变成了画。三人的努力,再加上歌者欣彦,让一首诗不但可以读,可以唱,还可以画呢!
现代文学可分为四大文体,即诗歌、散文、小说与剧本。同样是承载文学的载体,但这四种文体却有各自不同的特征。要说散文像一个步履缓慢而扎实的人在散步,思绪一点一点在脚步中印刻下来。小说与剧本是叙说故事的载体,它们更像是一段漫长的接力赛,不写到最后不知道故事怎么发展。而诗歌,是这之中最小巧、最轻盈的文体,是跳跃在平面上的文字,恰似一个人在跳舞。舞姿或张扬或含蓄,每个人从舞者身上看到的事情都不一样,诗歌就是这样。
诗歌,也被称作诗,它承载诗人的思想与意识形态,唯有阅读的人才能与这段文字心领神会,形成独特且微妙的体验。但也恰恰是它的独立与暧昧性,成为了诗正在面临的困境。诗的文字是抽象且充满隐喻的,需如猜题般去解读作者留下的暗号。有时可以猜到,但有些时候读不懂,就是读不懂,反而会让人对这类文体产生疏离感。“看不懂”大概是诗听过最多的批评了。
但如果诗的呈现方式,不只是局限于在文字书写,人们不再只是透过阅读去认识它,也许情况会变得不一样,也许诗有了更多不一样的表演机会。《神秘之歌》正是这样的一张专辑。

《神秘之歌》是马来西亚诗人周若涛2011年出版的作品,收录了他自1998年到2010年十年以来的创作。如今来到2020年,《神秘之歌》再度跨过了一个新的十年,已然变成了一张音乐专辑,更是一张绘图画册,让这些诗不再只是纸上的文字创作。
但,诗依然还是主角。
“诗曲”专辑的诞生 集合本地创作者的诗情与画意
“我们一开始做的时候,定位就很清楚,就是以文字作为出发。所以里面的歌曲都是先有诗的文字,才谱成曲的。在谱曲的过程中,也是尽量不改动原来的文字,可能有改动一两个,但大致上还是忠于文字。所以我们觉得《神秘之歌》是一张文字先行的专辑,所以就把它定位为一张‘诗曲’的专辑。”若涛如此说。

《神秘之歌》最早并没有要变成一张音乐专辑,只是有着丰富作词、作曲经验的作家兼音乐人,王修捷和若涛提起的想法。“修捷在看到我的《神秘之歌》之后有跟我表示想为其中的作品谱曲的想法,当时我本来想着是小规模的计划,我们可以带到《动地吟》上去表演的。可是后来我们就接触到欣彦,那时候我们找欣彦来帮我们录demo(试听带),她就建议为什么不把它录制成一张专辑。这句话就打开了很多可能性。”


欣彦Z Yan是马来西亚女歌手,于2007年发行过第一张专辑。擅长的曲风除了流行乐,还有爵士乐、巴沙诺瓦曲风等等,更是第一个将巴沙诺瓦曲风融合在中文流行乐中的女歌手,有“芭莎公主”的美称。
经她这么一提,若涛便把自己的老同学,同时也是声乐家和音乐制作人陈颖豪,作家兼音乐人王修捷,音乐总监和编曲人Ken Hor(何福权),作家兼画家龚万辉以及负责摄影的陈子韩等等不同才艺的人都拉进来参与这次《神秘之歌》的专辑。


於是谱曲、编曲、歌手、画家、摄影各色人物都聚齐了,这张兼顾耳听与眼看的专辑就正式进入制作过程。但如若涛所说,这是一张以文字先行的专辑,也就是一张先有文字,后再谱曲的专辑,这就为谱曲人增添了许多局限与挑战。担任专辑谱曲人的修捷表示,这是相当少有的创作模式,但所幸若涛的诗歌本身就很有音乐结构,在谱曲的时候没有遇到太多困难。
近百分百的文字先行
“所谓文字先行指的就是完全服务《神秘之歌》这本诗集的。不只是这样,从作曲人的角度而言,在市面上经常会听到一些作品出现‘倒音’的部分,比如说萧亚轩的〈爱的主打歌〉,‘原来原来你是我的主打歌(猪大哥)’,乍听之下像是‘猪大哥’,是因为平仄有违旋律起伏。会出现这样的倒音问题,有时是偶然情况,有时则是因为先有词才交给作曲人谱曲,一般比较理想的情况是先有曲再填词,因为作曲人是很自由的,往往没有兼顾到文字的平仄、读音,只专注于谱上旋律。”
“可是这张专辑却是文字先行的。我花了很大的心力去还原诗集中的音调,虽然做不到100%,但是很多的曲它是跟着诗的律动而谱出旋律的,很尊重诗原本的面貌。而且我也不太敢更动文字、诗的内容,比如说它的诗歌到哪里是高潮,适合当作副歌部分。像〈神秘之歌〉就是最好的例子,一开始是‘你邀我到内城密林,哪里再没谁会离开谁’,而当它中间语气转折,成为‘但我已到过了所有河流断绝的地方’这个部分开始我就把它当成了副歌部分。”
但我已到过所有河流断绝的地方
过去与未来,我们的干渴
汇流成一株古树
那样的荫蔽下,才看得见初升的星辰
你不记得我们曾是树上的藤蔓
相缠,互噬,盘旋而上
吐蛇信的毒花
你邀我到内城密林
那里再没谁会离开谁
但雨停之前我终将离去
回到所有河流断绝的地方
——〈神秘之歌〉节选
由诗入画并不容易
除了谱曲工作遇到“先诗后曲”的挑战,绘画工作也同样不容易。
“我觉得从诗到画作其实并没有那么容易。因为从画插画的经验来说,散文和小说比较容易画。因为散文和小说有人物、故事、情景,比较容易画成插图。但诗往往只有意象,我觉得诗最难画。”

龚万辉是星洲日报《副刊》的常驻插画家,经常为不同的作者和文字配上相应的图片。所以当若涛带着诗集和录制好的试听带找到他时,他二话不说便答应了。虽然当时有些诗曲已经有了音乐雏形,但他还是回到诗最本身的文字上寻找灵感。
“我也是从诗开始,就是从若涛的诗出发。歌曲的部分没有特别影响到我构思的方向,当然有时我也会想画不需要根据歌曲的脚步,变成我只能从文字去挖掘我所看到、我所感受到的东西。所以有些段落我觉得比较有共鸣,或者是有画面浮现的部分,我再由此去延伸更多的枝节,更多的想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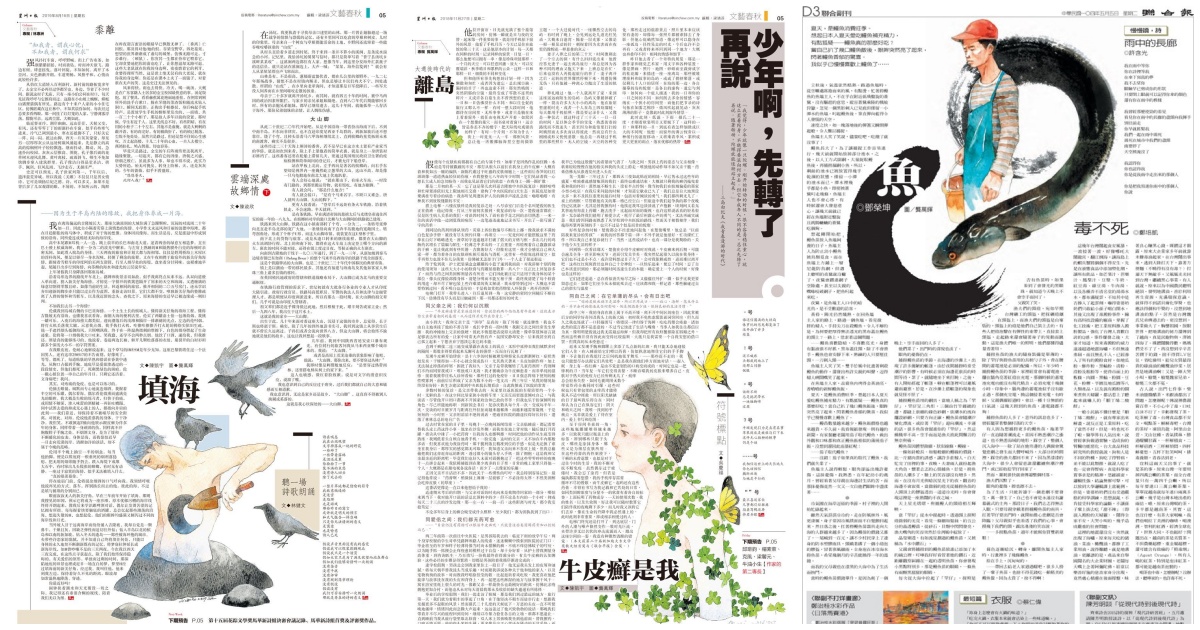

“我觉得我交出来的作品应该跟若涛或者大家想像的不太一样吧,大家可能一般上看到的是我在副刊或者文艺春秋画的作品,可是这系列的作品就跟报刊的插画很不一样。在主题、美材、质感各种表现的方法都不太一样。给报纸的插图我一般上都会用水彩和纸张,而这系列的作品我就用了压克力颜料和油画画布,对我来说也是一次有意思的挑战,交出来的作品会和在报纸上刊登的不太一样。”
万辉说这一系列的画作将会成为这张专辑的一张脸。大众可能在读到诗,或者听到歌之前,首先就会看到这张专辑的脸,所以他希望这张脸是能够引人注目的。所以他赋予了这系列作品一个统一的主题——少女。

少女作为《神秘之歌》的脸孔
“我一开始就希望这十幅作品是由一个统一的主题的,若涛这系列的诗最可以感动到我的部分应该都是情诗的部分,爱情的主题。情诗应该是最能够表达到诗人的情感。那选择少女作为主题是希望这些诗作在变成具象的画时,会有一个情感投射的对象。而少女是我一直在创作的路上迷恋的主题,我觉得会选择少女是因为她是一个身体、心理都还没有真正变成大人的阶段,可能少女保留了比成人更多的善良、纯真或者爱,就是这么一个我们都无法返回的阶段,这种时间的距离感可以让我们有更多的想象和宽容吧。”
万辉描绘的少女,是人最年轻稚嫩的阶段,透过少女来展现的善良与真实。如他自己曾经在文章〈少女作为方法〉里所写的:
如岩井俊二电影里头的苍井优,如川端康成的伊豆舞娘,总是一再藉由少女的目光,看去这个不甚完好的世界。有时犹如对已逝时光的一种徒劳追忆,有时也是欲望的投射。少女成为了故事的入口,因为我们相信,即使是虚构的,少女仍像是大理石刻的维纳斯那样,千年过去,依然在内里保留着我们已经磨损不堪的善良和真实。现实在她们身上留下伤痕之前,她们让所有精密的虚构,都有了一种依托。——龚万辉〈少女作为方法〉节选

这也许是每个创作者都在追寻的,如同少女般稚嫩,未经饱受风霜,未经命运打压的,犹如深居在花苞中的拇指姑娘,一个在心中尚未崩坏的地方。
神秘的〈渔夫与国王〉 首次编曲中融入马来传统玛蓉乐
《神秘之歌》十首诗曲作品,〈神秘之歌〉、〈昨夜晴雨〉、〈如果世界末日我不在妳身边〉、〈昨夜她来〉、〈昨夜花园〉、 〈无话〉、〈烟花季〉、〈昨夜余光〉、〈渔夫与国王〉与〈盛世夜店〉,大部分都是情诗,编成诗曲后长度与我们一般听的流行乐相同,介于3到4分钟之间。而其中却有一首7分钟长的作品,在一众情诗中显得特别引人注目,名字也在情诗丛离中特别显著,它就是〈渔夫与国王〉。
这部作品之所以会有7分钟的长度,是因为它是一首叙事诗,书写的是2004年12月26日发生在印度洋的大海啸。当时在印度一座沿海古城马哈巴里普南,在汹涌的海水退去之后,发现了一座水下的古城遗迹。诗歌描述的是一名渔夫目睹到海床露出古城的遗迹,印证了当地流传已久古文明传说的故事。
海洋把领土归还给传说
那曾瞬间覆灭一座王朝的灾劫
瞬间又赐予短暂的复生
仿佛集生灭于一身的湿婆神
于天界偶然忆起遗弃千年的大陆
仅仅一念的潮起潮落
——〈渔夫与国王〉节选
此外,这部作品的编曲,也是首次在中文音乐中加入马来传统乐曲的元素,玛蓉乐。
“〈渔夫与国王〉是以一个古印度王国为背景,在它变成现在这个版本之前,修捷也有尝试把它变成另一首曲子,它其实经过很多演变,后来找到了陈颖豪和我们的音乐总监Ken Hor,颖豪对本地的民族乐是相当有研究的。所以当他看到这首诗和曲的时候,他就联想到玛蓉乐。”
被禁的马来传统乐曲 周若涛:时刻提醒马来半岛的多元文化
玛蓉(Mak Yong)是盛行于吉兰丹、吉打、玻璃市与登嘉楼一带的马来传统戏曲,结合唱、舞、演、宾白与音乐演奏等等的表演艺术。从古流传至今大约有超过800年的历史,还在2005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但这项传统音乐却因为宗教元素,而在1991年被吉兰丹州政府禁止公开表演,一直到去年才获得部分解禁。
“因为玛蓉乐是马来半岛最古老的乐曲形式,它是有受到印度文明的影响,有印度乐的成分在里面。所以跟诗中的古印度背景有一个重叠。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这张专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创作,所以我们希望把一些本地的在地元素放进去,让它更有机。还有第三点就是因为这个玛蓉乐的背景,我觉得它可以更好地呈现马来半岛多元文化的背景。当我们说马来西亚是多元背景,它不只是一个现况,不只是一个从独立才开始的东西,而是从更久以前就存在的。在回教文明进来之前,马来西亚有印度文明有中国文明,这一点我觉得我们是有必要时刻提醒自己的。”
他们找来了玛蓉舞者Zamzuriah Zahari以及Kamarul Baisah为〈渔夫与国王〉演唱和演奏。来自吉兰丹的Zam是马来西亚传统舞蹈与剧场的舞者,她专研玛蓉乐多年,在2006年曾获得青年、舞蹈类别的国家艺术奖。现在更是国家艺术文化遗产大学的兼职讲师,负责设计传统舞蹈课纲。

Zam之所以会如此钟情于玛蓉,源自于她的童年记忆。小时候Zam的祖父是乡里受人敬仰的宗教司,在他晚年病危的时候,特意邀请了剧团来演出传统玛蓉剧。Zam觉得祖父在那场表演中似乎获得了某种神秘的慰藉,身心都好像因此而解除了痛楚,不久后便安详地离世了。这段记忆一直留在Zam心中,成长后便立志要传承玛蓉。

这次遇到《神秘之歌》的专辑制作,和〈渔夫与国王〉作品一拍即合,成就了一次跨族群的音乐合作。若涛他们表示Zam并不知道〈渔夫与国王〉诗中每字每句在说什么,只是简单地从若涛等人口中知道诗歌大概在写的是一场海啸,便能理解其中意境,唱出的歌声也如海啸卷席、霸占众人的注意力。
“阅读本身是比较费力的,有时是很吃力的。但我们把它变成音乐之后,就好像为作品裹上糖衣,即便你不了解那段文字,也可以通过那段旋律去记得那段文字。”对若涛而言,这些声音、音乐、绘画、影像都成为了诗意的一部分,让诗不再只是文字,诗意也不再是难以想象的,而是有了更多表现的可能。
音乐画作都是诗意的延伸 诗就是世间的神秘之歌
“其实我们各自的创作方式都是各自进行的,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正确的方法。”若涛表示这次无论是作曲还是绘画,每个创作者都是站在同样的起点上,从文字出发,用其他艺术载体来回应诗的文字。
万辉和修捷也认同,这次的作品更珍贵的是,这些不同的艺术载体并不是彼此的附属品,而是可以特立独行,去回应诗的存在。万辉:“我觉得这系列的成品,音乐、诗和画作,是彼此的一个对照。它也不是彼此的附属,不是买牙膏送一个杯子那样的附赠品。它比较像在一个花瓶里面有不同的花插在一起,我觉得这是这张专辑跟别人不一样,又最有趣的地方吧。”
但这里回归到我们一开始所说的诗的暧昧性,因为其朦胧的特性,常常每个人读都读出不一样的感受来,这是否会导致各自不同的人和艺术作品的解读不同,而有分裂的状况呢?若涛、万辉和修捷都表示,这并不是一种可怖的分裂,反而是诗最玩味的地方。
“文学作品,尤其是诗,它不是一个要被看懂的东西。我觉得看懂这件事情是很salah(错误)的,它不是一个正确的approach(理论、手法)来对待一个文学作品,或者说一部作品。尤其是诗,它对我而言,可贵的地方正正就是它的暧昧。它可以打开一些未知的领域,打开一些日常以外的一些你看不清楚的境界。我觉得那些虽然是很抽象的东西,但也是生活的一部分,作为人的一部分。”若涛这么说。
对于万辉来说,读诗最重要的经验不是读懂了,而是去感受的过程。
“我觉得我们这个年代是被图像轰炸的年代。我们有不同的小说被拍成电影,可能散文也可以被照片一张张取代也说不定。我有时候会想文字有什么是不能被图像取代的?我觉得那就是诗。诗的那种文类,它是经过淬炼的文字,回到文字最纯粹又最隐喻的一个形状。我觉得这些东西是不能被图像所取代的,那么你可以想象有些诗句,像〈渔夫与国王〉中的“我于无数愁闷的时刻,阅读浪在海面的书写”,这东西是画不出来的,你就会发现不是所有文字都能变成图像。那图像只可以呼应它,转化成另一个形象,或者是创造成另外一个样子。”


修捷:“这个计划好玩的地方在于它是没有一个主人的,万辉的说法是一个花瓶里面插着很多花,我的看法是现在我们在用各自不同的专业,去回应这首诗。比如说我站在音乐的角度,这首诗应该要怎样怎样,到了编曲人Ken Hor那边又会有不同的讲法,这边加滴水声、脚步声,又是另外一个看法。尤其Ken Hor和他的制作团队Inner Voices Productions发掘出作品间的联系,用相呼应的音乐元素呈现出来,让专辑的结构更紧密,概念性更强,奠定了专辑的方向。”
IVP编曲团队擅长电影配乐,曲风从古典、爵士、摇滚、电音或是流行乐都能驾驭,从《神秘之歌》这张专辑中编曲的多元就能体会到。这次与《神秘之歌》的合作,也运用了大量的电影配乐技巧,让音乐听起来十分有画面感。
“它就像是诗在正中央,大家围绕着诗,各自提供自己的专业去诠释他的诗意。透过这样的诠释,大家可以看到一首诗是可以多么地多元。”修捷说。
而他们围坐
焚尽了诗酒
花园逐渐塌陷
星空已然枯竭
一切生灵归隐
你枯坐成石
该断绝的都断绝
都已经断绝
她来
静立身后影子淡静
敷在背上像一场细雨
让它轻覆隐藏着你
她来
眼底星光遥远如谜
草茎钻入指间那微痒
百转千回
——〈昨夜花园〉
譬如以上这首〈昨夜花园〉,修捷说他读完之后觉得这首诗非常悲伤,但其他人读了觉得是一首浪漫情诗说不定。这就是诗神秘的地方。
诗,不需要被读懂
这也是诗注定无法讨好所有读者的地方。被“诗不是要来读懂的,而是要来感受的”这样的总结告知,会让人觉得这不过是文人式的推搪,四两拨千斤想要打发读者。但仔细想想,我们的生命中,绝大多数的事情都不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包括人类的起源、宇宙的诞生,至今仍是一道难以被证实的理论而已。
当生命的起源本身就是神秘的,何况是诗。
诗也许是所有文体中最小巧轻盈的,但它的暧昧不清却如宇宙黑洞那般可以容纳许多事情,充满了神秘。也许你探身而入之后再也走不出来,但漆黑的黑洞中也许是另一个宇宙的出口,如若涛说的,诗能够打开一些未知的领域,从此改变你看待世界的方式,也说不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