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这几十年来我在四家报馆打拼,工作除了深具“使命感”,还得为赶截稿时间而跟时钟的分针秒针赛跑,所以经常也要“死命赶”!馆方为免员工出去外面用餐耽误工作时间,都在报社里附设食堂,好让我们快快填饱肚子后立刻开工。
上回谈过在《新明日报》和《通报》食堂用餐的激气事与趣怪事,这回且续谈在其他两间报社“咬米”的经历。所谓“咬米”,就是“吃饭”,这是几十年前郑裕玲在一部港剧(好像是《执位夫妻》)所讲的潮语,但如今似乎没有人听得懂了,难道就此失传?
现在我记忆力越来越衰退,忘了是在《通报》或是《南洋商报》任职时,曾有几姐妹合力经营食堂,全都长得很胖,而且煮很多肥肉给我们“叹”。那时刚好香港发生一宗趣闻,有个肥婆乘搭德士时刻意不付钱,宁可“车债肉偿”,吓得那德士司机“走夹唔唞”,于是八卦周刊替这肥婆取了个外号叫“欲海肥花”,轰动一时。我们一些缺德的同事有样学样,竟也把那几个常煮肥肉的食堂肥版姐妹花暗地称为“肉海肥花”,真系“衰多口”兼“衰臭口” !

《南洋商报》的食堂时常换人经营,我最满意一个好像叫阿巧的老板娘,很舍得煮虾给我们吃,而且收费廉宜。有些人“发花癫”,我却“发虾癫”,见到虾就搏晒老命猛咁擦,几乎餐餐都无虾不欢。可惜这段吃饭吃到“虾虾笑”又“笑虾虾”的幸福日子并不长久,食堂又换人了。
接手的新老板似乎比较斤斤计较,却练得一手神乎其技的刀功,切午餐肉可以切得奇薄无比。还好食堂有冷气设备,不用开风扇,不然我们饭碟上那片薄到风都吹得起的午餐肉随时都有可能“Gone with the wind”被风吹走,那我们就得像足球门将那样飞身扑救了!
这老板聘请的印尼婆煎荷包蛋另有一套,烧红一个大油镬,把一大堆鸡蛋一颗接一颗打下镬里去,总之“唔理好丑,求其快手”,这已不是煎蛋,而变成“炸蛋”了!结果所谓的“荷包蛋”每个都被炸得干干硬硬燶燶,蛋黄和蛋白混在一起,简直就是“混蛋”!
有次我央求另一名伙计为我另外煎一个半生熟的荷包蛋,最重要是不要弄破蛋黄。他本来已答应了,但不一会却走过来跟我说:“老板说不可以另外再煎一个荷包蛋给你,不然那一大盘已经煎好的该怎样收科?你要吃就吃那些吧。”
唉,我只不过想吃一个比较“正常”的荷包蛋,没想到这么卑微的心愿竟也无法达成!
我下一份工作是在《光明日报》,隶属星洲媒体集团,我们的饭餐都在《星洲日报》的食堂解决。刚在那儿上班时,食堂老板娘每天都有煲老火汤,常有汤水滋润。


但过了不久,食堂经营者就换人了。这业者十分精打细算,我试过只吃白饭和一些香港芥兰,竟敢收五块钱,这在十二年前算是贵到离谱了!其“理由”是:“这些芥兰是坐飞机运来的,当然贵啰!”
有个同事选了几朵不是很大片的焖冬菇,竟然每朵收块半钱!同事惊讶地讽刺道:“哗!原来这不是冬菇,而是灵芝!”结果,有大批员工联署签名写信投诉,这“食水太深”的经营者只做了两三个月就离去了。
食堂下一个新业者稳扎稳打,餸菜不错,收费也公道。久不久就会有些新菜式增添新鲜感,大家都接受下来。
有次我要求为我煎一个不要弄破蛋黄的半生熟荷包蛋,也没有托我手踭。上次在南洋吃不到,这回终如愿以偿了。我浇少许豉油下去,先吃嫩滑的蛋白,再戳穿蛋黄,让蛋液覆盖捞匀在白饭上,吃来齿颊留香。只不过是一个那时才收七角钱的简单荷包蛋,就吃得非常开心,也满足了我这个卑微的要求!

新业者每个星期一都有只卖五块钱的白斩鸡鸡腿饭,虽不能和南香鸡饭相比,但味道也不差。才五块钱,你还想怎样?每星期三还有卤鸡脚、鸡肫、鸡心,卤得十分入味。一些师奶同事,吃完还打包回家为晚餐加料。星期四则有好味的纸包鸡,也是我的至爱。平日有时会炮制卤味饭,包括卤蛋、卤豆腐、卤猪大肠,才卖六块钱,抵食之至!

这新业者胜在烹调下足功夫,却不谋取暴利,对员工食客将心比心,没有乱砍菜头,所以长做长有,直至如今仍在继续负起填饱大家肚皮的重任,这才是正确的经营之道。
你也可以看:
延伸阅读:李系德专栏《你係得嘅》其他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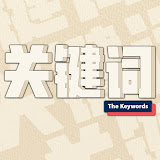

















作者用词粗俗,很明显是想耍些文字幽默,然而看了且教人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