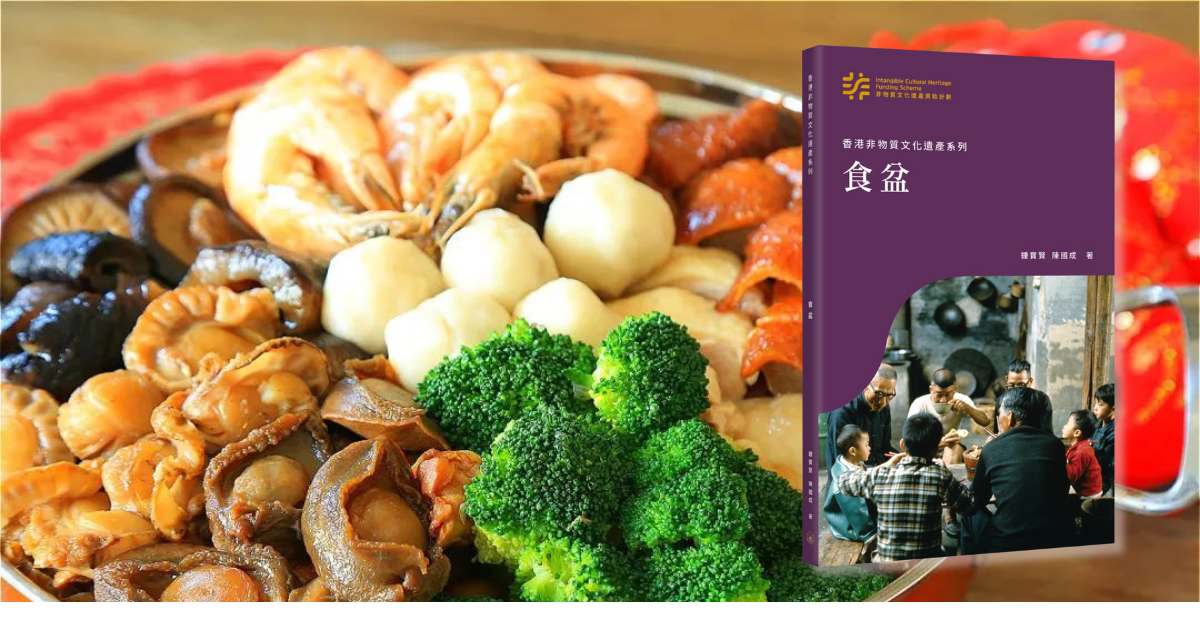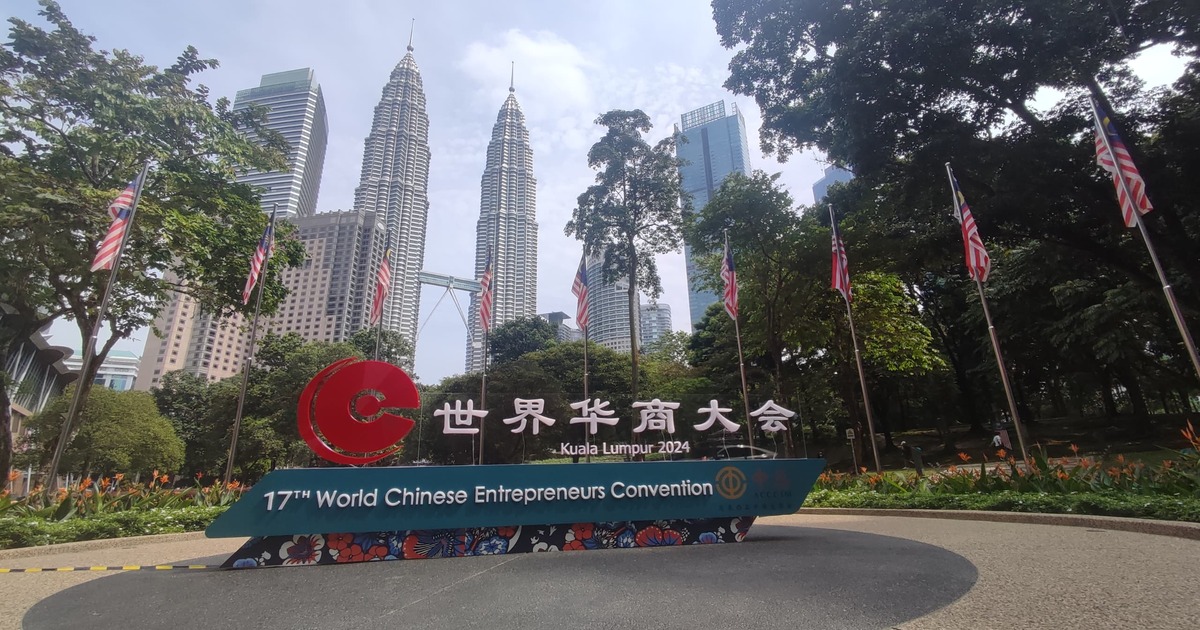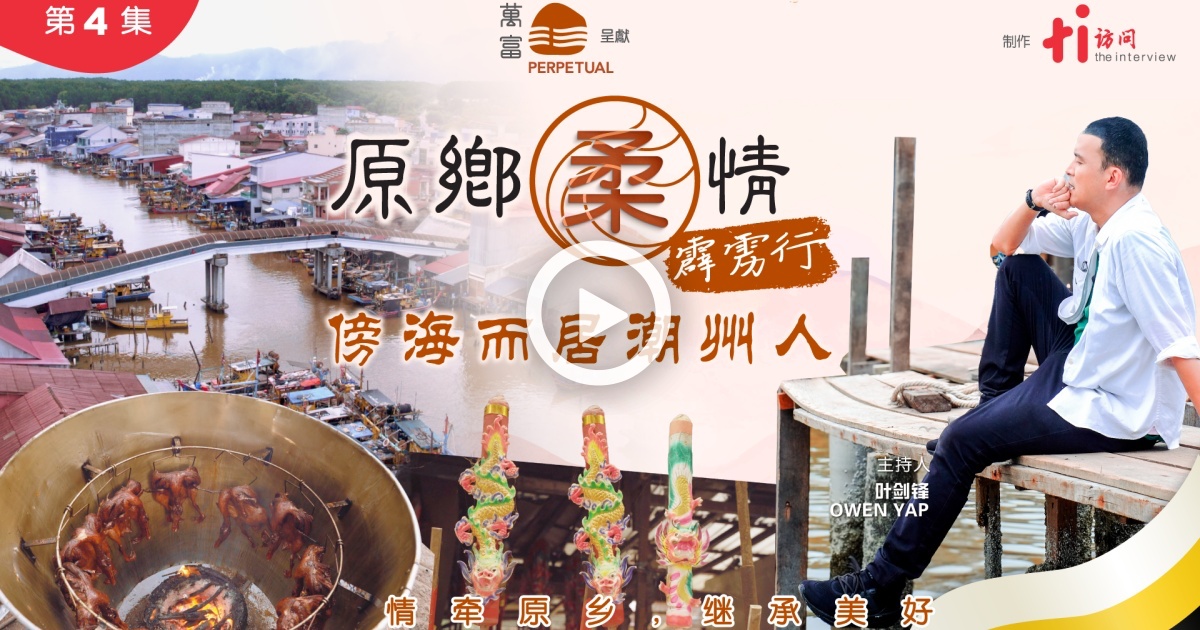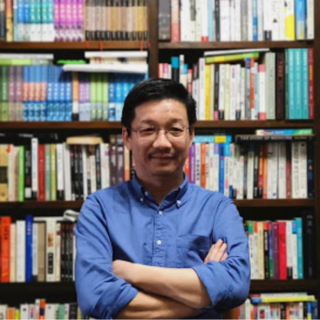我是陈桂恩,朋友叫我Karen,是一名礼仪师。从业23年,我陪过无数人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
外界对这份职业的想象很多,但说到底,我们只是用专业素养,帮逝者和丧亲家属完成一场好好告别的仪式。
人生没有take 2,如果我们能用爱迎接一个新生命,那他们的离开,是不是也值得被温柔对待?
很多人以为,我们这些天天面对死亡的人,早就看淡生死、不再害怕。
我觉得,是,也不是。
一般人一生会经历几次亲人的离别?四、五次而已。而我,每一天都在接住死亡。我听过太多哭声,也知道人是怎么死的,意外、疾病、抑郁、自责……每一种离开,都有一个破碎的故事。
所以,我其实很怕死。怕是因为我很清楚,生命原来可以随时中断。看着我年幼的孩子,我知道,对我来说,还不是时候。
42岁那年,我被证实患上鼻癌
2022年某天早晨,我和往常一样在厕所盥洗一番,结果吐了一口的血,血很多、很鲜艳。
我马上告诉丈夫,然后预约了耳鼻喉专科医生。医院里,医生把管子插到我的鼻子里,说看到了不太好的东西。
被证实患上鼻癌的那一刻,我的脑袋一片空白。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后,我询问医生:我需要做什么?

医生非常专业地给我解释了接下来治疗的流程和注意事项,听着听着,我发现医生说的每一句话,原来我早就在家属的口中听过无数遍,这些话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陌生。
所以我知道好好治疗,是当下唯一的选择。
不幸中的大幸是,因为我早期就诊,病情正处于第一期和第二期之间,我顿时松了一口气,那些事前在网络上查阅后的担忧顿时消失不见。
那个当下,我感恩自己进入了这个行业,每天游走在不同的家属之间,面对病逝的家人,他们总是离不开那句“早一点发现就好了”。所以只要当有一点点迹象发生在我的身上,有任何地方开始觉得不舒服,我就会马上求医。
这次的疗程需要进行35次电疗和七次化疗,一共耗时七个星期。治疗开始前,医生一再重复化疗会带来的副作用以及可能发生的种种症状,也强调疗程一旦中途放弃,体内的癌细胞会翻倍地回来。
很多人认为癌症是一种因果报应,我也听过很多癌症患者总是抱怨:我没做坏事,为什么是我?
我曾经和丈夫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一度以为我开始抱着许多负面想法,正准备安慰我,我摇摇头,告诉他:
为什么不是我?如果不是我,难道希望是别人吗?
很多人生病后,总会问:“为什么是我?”仿佛生命欠了我们一个公道。
“难道每个苦难都必须是别人来承担吗?” 既然它来了,我愿意用尽所能,和它一起走得温柔些、清醒些,也许,这就是命运要我修的功课。
癌症是很羞耻的事情吗?
我一头扎进漫长的疗程中,像回到上学时一样,每个星期一到五都按时到医院报到。化疗一点都不轻松,但我不会在儿子们面前袒露自己的辛苦。

直到第三十次电疗的时候,我的生理和心理开始逐渐被击垮,医生当初的叮嘱开始一个个发生,颈部开始出现溃烂、我吞不下任何食物,就连喝水就像在吞玻璃一样扎人。丈夫把所有食物都搅成汁,我耗尽所有力气让自己吞下这些食物,生怕医生因为我的虚弱,阻止治疗继续而前功尽弃。直到第三十五次的电疗完成,我开心地和陪伴我数个星期的器械合照,也和所有医护人员道谢。
回到家后,我难忍体内的痛楚,为了不让自己辛苦的模样被孩子看见,我再次入院,注射吗啡舒缓痛楚。
就这样反反复复地治疗,我成功抵抗体内的癌细胞,也重回职场。
自从回工作岗位,我常跟身边的人分享自己的抗癌经历,也总是劝大家,有病就要赶快去看医生。
但慢慢地我发现,身边如果有人也得了癌症,他们反而会选择隐瞒病情,接着突然从大家的生活中消失。
我一直不太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他们也不懂,为什么我可以这么坦然地说自己的事。
但我常想:
患癌,真的那么羞耻吗?
生病了,不是更需要被理解和陪伴吗?为什么要把自己藏起来呢?
抗癌之前,我自认是一个脾气很大的人,为了把工作做好,我每天都活在压力之下。

但从这一次勉强算在生死关头走一遍的经历,让我慢慢放下许多事情,我学会把事情交给团队处理,更是明白尊重家属意见的重要性。与其用“专业”提意见,不如随着家属们的意愿,让一切顺其自然地发生。对于癌症患者,一味地“建议”他们提早准备自己的身后事只会更加让人反感,毕竟没有一个癌症患者会想过自己抗癌失败,然后就这样离开。
一场病,对家人的影响有多大?
在治疗鼻癌的过程当中,我一直不愿意在孩子面前表现出自己的难受和痛苦,每次治疗回到家,我都对着两个儿子说,妈妈没事。直到抗癌成功之后,尽管后遗症、疤痕依然没有消退,我也不让家人担心。
有一天,十二岁的大儿子放学回家突然问了问:“妈咪,你的病真的好了吗?”
一问之下才发现,大儿子朋友的妈妈因为抗癌失败离开了,而父亲选择抛弃这个孩子,最后这个小朋友被迫成为一名孤儿。我好奇地问儿子,这位母亲得了什么癌症?
大儿子却在这时突然打断我:“妈妈你不要再说了,我不能再听到‘妈妈得癌症’这句话了!”
孩子的眼眶马上就红了。那一刻,我沉默了。
我拍拍儿子的背,反复告诉他,妈妈没事了。儿子望着我,和我反复确认。那一刻我才知道,这场病情,对孩子的影响有多大。
后来我还是告诉儿子,自己终有一天会离开,但儿子似乎有些抵触,即便他们从小就知道死亡是什么,但他还是告诉我,妈妈你不要那么快走,等你老了再离开好不好?
我忍住眼眶的泪,克制自己不让眼泪掉下来。但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如果有一天我躺在病床,看着手无寸铁的孩子们,他们该怎么办?我真的很怕,自己的离开,让身边的人不知道怎么活下去。
原来我可以扛住病痛,却扛不住孩子眼里的恐惧。

后来,每当我遇见年纪相仿的女性逝者,我总会下意识地查看死因。若发现她身后还有年幼的孩子,心里就会泛起一阵难以言说的心酸。作为一位母亲,我无法不设身处地去想:如果是我,我的孩子该怎么办?
这些年来,我始终不太愿意接过任何儿童死亡的个案,并非能力不足,而是因为那样的场景会轻易撕开我作为母亲最柔软的部分。那份痛,我知道自己接不住,也怕在职业角色中崩塌。
从事这份工作已经二十多年。有人说,我很幸运,至今未曾收到一封投诉信。但在我心里,真正的幸运,不是“零投诉”,而是我始终没有变得冷漠、没有让专业遮蔽了我的人性。
礼仪师的专业,并不仅仅在于仪式流程的精准无误,而在于我们是否还有能力停下来,用心看见一个家庭的痛、听见一句句说不出口的遗憾。很多时候,家属需要的并不是一个解决方案,而是一双安静接住情绪的耳朵,一份愿意陪伴的心。
这些年,我陪过无数场告别,看过人们如何在眼泪中整理回忆,也看过最倔强的人,在离别面前终于学会放手。但我也一次次地提醒自己:不要让所谓的 “经验丰富”,让自己对生离死别变得麻木。专业,是更有能力去共情、去承接,甚至,去给予。
身为母亲,我学会了理解失去的重量;身为礼仪师,我愿意陪着每个家庭,把无法承受的痛,慢慢交还给时间。
编按:本文乃作者口述之内容,由访问网记者余坤恬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