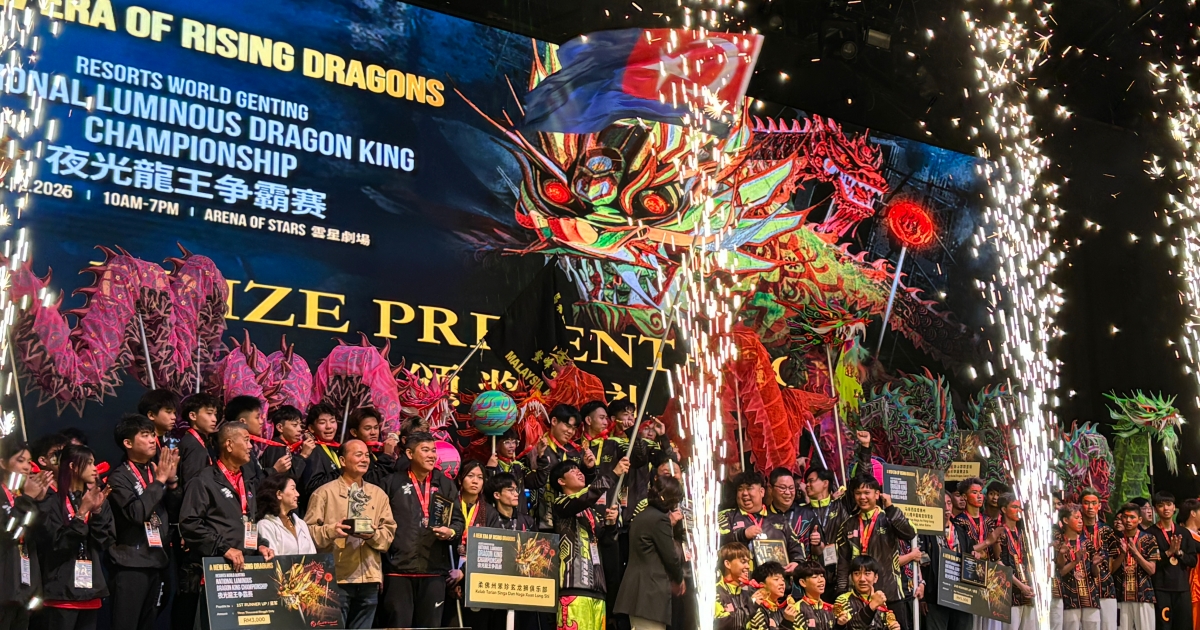海朋森成立于2011年,是一支来自中国成都的后朋克乐团。中文团名是英文Hiperson的音译,有打招呼之意,目前发行的专辑有《我不要别的历史》、《她从广场回来》以及《成长小说》。2024年六月,海朋森的巡演来到吉隆坡站,当站在现场聆听时,耳机里激烈的爆破和冲撞具象化了,直击心脏,并没有一丝歪斜。海朋森的歌词是主唱陈思江所写的诗句,叙事元素围绕集体与个体的关系展开,先写出信仰整齐划一的人群,又写出个体在集体中心之外看世界的视角,既唱绝望也唱希望。
初听海朋森,最深刻的印象是诗一般的歌词被陈思江用歌唱、朗读、呐喊等形式,融合编曲表现。海朋森擅长抓住想表达的重点,将其打磨、推进到高潮又坠落,展现突破框架的生命力,让人打从心底觉得“原来歌也可以这样唱,原来诗也可以成为这样的歌”。新诗本身就是一种对语言结构的颠覆和破坏,与后朋克这种在摇滚之上又进行一层颠覆的音乐类型结合,一拍即合,听起来既反叛又言之有物。
“为什么不可以有一个东西,它是既严肃又是让人愉悦的呢?”海朋森曾在〈草莓〉的幕后花絮中提出以上疑问,他们希望做出这样的音乐,并且告诉人们——再微小的感受和声音都是真实存在的,即便没有被大量讨论、没有被多数人看见。怀抱这样的念想去发出声音,能走向更深的思考,做出更多的行动。
大太阳下的人群,走在通往剧院的大路
在海朋森的歌曲里头,世界仿佛剧院,人们还未精准排练便要被推着上场,进行一场完美的演出。〈幕布〉的歌词为这样的意象铺了一条路:“这是通往剧院的大路/人们交头接耳觉得兴奋/人们想要看到一些事情/那些还没发生的事情”。“有人说那是一出喜剧/立刻就有人发出大笑”,“有的人即将看见自己/更幸运的看见未来的自己/未知的舞台正在闪光/而这条长路就是幕布”。当一群人聚集在一起,便有了对话语的附和以及对未来的想象。人们走在这条路上,向往着舞台,从不停下。
〈每日的行军〉则是描述社会运行的规律,以及相信命运的人们,机器一般运作的模样。“看/远远地看/河边步道上的人走成了竖列/慢慢向前走/看上去就像他们有一个命运那样”。“层层叠叠的路径和楼房/就像是河与山一样啊”,路径和楼房成为山河,现代城市的风格,始终不是一双眼睛可以捕捉和定义的。“向前走/向前走/失焦的目光看见的就算是未来吗?”,但人们宁愿相信战斗是生存的真理,相信每日都是一场行军:“战斗/战斗/战斗/生存就是战斗/经济就是战斗/他们相信”。
集体的样貌是怎样的?可以在秩序的调整下看起来整齐分明,也可以在秩序的破坏下有着反叛的喜悦,但以集体为出发点产生的场景都虚幻易逝。信仰集体的人总是看到中心,而中心之外永远无可避免地存在不一样的个体,当所有的人在唱同一种歌谣,不歌颂的人便违反了这场演出。
于是,人们的歌谣在大太阳下站不住脚。 〈我们的歌谣〉先写出个体融入集体的开端:“我们的人民/用血肉和商品相互摩擦/自从有了异物/我们的创造开始了”,“我们的兄弟/其实根本互不相认/自从有了尴尬/我们的友谊开始了吗?”。然而人的本性是“各自怀着各自的心事/各自握着各自的苹果”,当你听清了人们信仰的事物,却察觉自己根本说不出像对方一样肯定的话,唱不出像对方一样肯定的曲调,才会发觉他们的歌谣在大太阳下根本站不住脚。“我”明了了歌谣的罪恶,却无法脱离它,感到自责与折磨,于是“我削掉了自己的头把它放在胸口”。
〈追和等〉开头的歌词叙事可以视为一种对于集体的美好想象。“鼓励你的孩子追求他的幸福/即便那会使他离你很远/鼓励你的父辈追求他的幸福/即便那会使他离你很远”。在为命运战斗的现代社会里,这样的想象会不会实现?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你不确定什么在追你/你不确定什么在等你”。面对未知的以后,总是有声音告诉你“在幸福里我们团结一致!”,你偶尔说服自己相信这个幻觉,但公共生活没有幻觉,现实总是把你的幻梦击倒。双手与舌头之间,你选择留下双手,“这是权宜之计/但劣势不会保持太久/鼓励你自己”。
每日的排练和行军仍在继续,你却偶尔感觉路上的自己,永远走不到剧院。
大路之外,个体的欢愉与疼痛
通往剧院的大路之外,还有什么风景?
〈红色街区〉写出人生这场演出背后的丑陋。“街道/发臭的人群/凋谢的花已经准备好了很久”,为这一刻人们很不容易才找到自己的位置,既希望自己的表演成功,也希望看到世界给予他们的表彰。可演出一旦被集体的中心统治者定义为“不够妥当”,就会被破坏。 “我很失望/我的歌声失败了”,你无法再“苟同着/持续着”一场表演。在通往剧院的大路上,你被掉下来的路灯砸中脑袋,开始意识到向往的舞台灯光并非永恒,也并非为了所有人闪烁。“还剩一点灯光/我们还可以再开心一会儿/直到那许多的路灯/一定会掉下来砸中你的脑袋”。
〈新都人〉一阵见血地唱着:“国家比爱情更远/广场比舞蹈更远/旗帜比景色更远/但花园最远/花园最远”。你看见和你一样的年轻人们,在路上游行、交谈,但在“有人举手支持白色的谎言/更有人为单一的美独断统治”的世间,他们永远会受到所谓正义的折磨。所以,你选择远离国家、爱情、广场、舞蹈与旗帜,远离这些由人群虚构的想象与狂欢,走向花园。 “你的正义早把我折磨得半死/在遥远的花园里我活得更好/那时年轻人在园中忘我地交谈/年轻人抱着石头渐渐入睡”。昔日觉醒的年轻人们是什么结局,你选择不去想象,高高在上的统治者早已告诉你答案:“我们应该像从前那样把结局遗留在/不会发生第二次的对话里”。
在这样的世界里,还有不一样的人吗?在大路上,〈他打定主意做一个游客〉,不是观众也不是演员。“我想就这样的生活下去/就像不再面对任何谜题/天空代替脑海/生活不需要什么意义”。当有了这个念头,你的眼睛自然而然地望向那自由的游客:“他遇上路口就右转/遇上行人他脱帽示意/他像鸽子轻松地飞过我们的头顶”。你向往他脱轨的姿态,所以也选择远离篝火与宁静,以此摆脱束缚:“我不是鸽子/甚至不是乌鸦/我现在必须游戏来获得宁静”。即便飞不到多远的地方,你在框架里游戏。
一个人的欢愉和所有路径一样,必将伴随痛苦,但至少你不再为了虚幻的追求,与无头苍蝇般的人群一同走在庸常的路上。〈我进入了绝望的时期〉里,唱着“我无法说服自己/什么东西可以恒久不变/值得信赖/我无法找到它/以前我想像中一颗太阳”,“驱散夜晚的太阳在夜里不出现/我知道”。脱队的人像是孤儿,找不到对家的想象。但“在我跳跃的瞬间/我得到了他的眼睛/那完美的无障碍的眼睛”。你拥有太阳之外灼烧的双眼,这双眼睛看见的东西或许危险,或许突破界限,却是最真实的悲欢。
黑暗裏灼燒的眼睛
〈撞进白昼〉写了黑暗里的双眼注视白昼的目光。“撞进白昼比滑进夜晚来得困难/光线使你迟钝的头颅开始发痒”,这双眼睛意识到“白昼意味着把自己交给光线/而光线也许会带你进入他们的世界/那并不一定是他们内心的世界/但那又有什么问题呢/这毕竟是一个水泥蝉鸣的共同世界”。它提醒认为自己身处白昼的人们,“别做一个残忍的人/你们的自由屈指可数”,并且独自“在柳树闲/在荷塘边/在闪电下/蔑视他们的骄傲”。
你在黑暗里〈找到了〉自己的语言。“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曲子/拿在手里像一个五线谱的图/发生在生活里面的事情就像谱子上面的音符一样/它们长短不一轻重分明”。从尝试捕捉现代城市的风格,尝试成为它的一份子,到现在怀抱自己的语言,你意识到“有些谅解是多余的/有些安排是多余的”,你的世界可以是空旷的,不由人与人之间、人与工作之间的交涉与价值堆砌起来,而“这片空旷对我有益”。
无论面对的是黑夜或白昼,或许生命的尽头是〈春风〉迎面吹拂,邀请旁人走进风里,听歌者倾诉爱意。这种爱是拉着那个人走出硝烟弥漫的路,向他展示和倾诉世界另一端拥有的风景。“除了你的除了我的/是不是还存在别的世界/在那里犯错和成功很少伤害到人们/各种花样层层剥开诸多形象无穷地消长”,“去了那里你一定不再需要瞻前顾后/我兴许也能摆脱邪恶的罪名/只见前前后后是深不可测的景色/没有故事只有一个声音在回响”。
每个人难免背负着生活结下的果实,但愿你都能生活在一个没有约定成俗和成败的世界,用自己的姿态存在。这是一种渴望,也是一种对他人生命的祝福。“欢迎你过来/人类的成就是这里的一座小土坡”,我们渴望人们可以在这样的祝福里生根发芽。“你飘啊荡啊/双腿竭力地模仿行走在地上/你呼啊喊啊/竟然只听见声音消失的声音”,在世间走过这么一段纠结的日子之后,我们的声音将会以一种仿若从未出现的姿态,消逝在时间的长河里。
大太阳下的世界没有真实,但海朋森的表达在向人们发出邀请:在光照不到的地方,永远还有不起眼的人正在直视幕布前方的虚假。脱离虚幻的表演与命运,脱离那条恒常而反复的路径,你要游戏,并且拥有自己的眼睛。在生命消逝前,去看见自己的绝望和希望,也看见自己之外所有微小的存在。
“倒霉的草莓,我们却都看见你了。”
▌延伸阅读:傅译萱专栏《声音译览》其他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