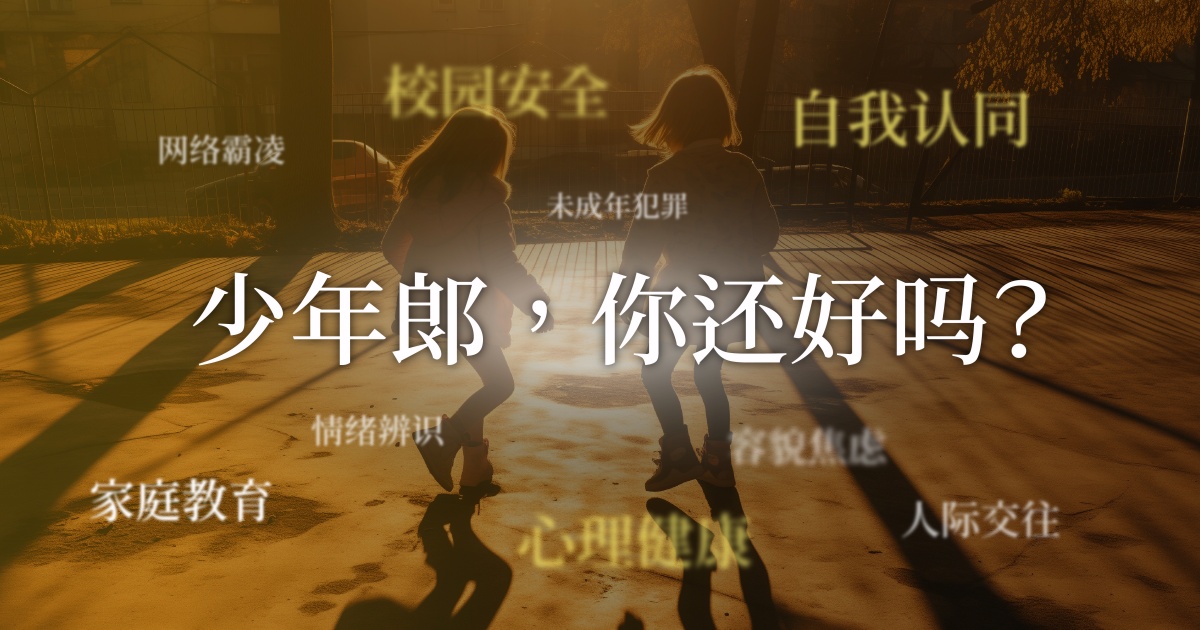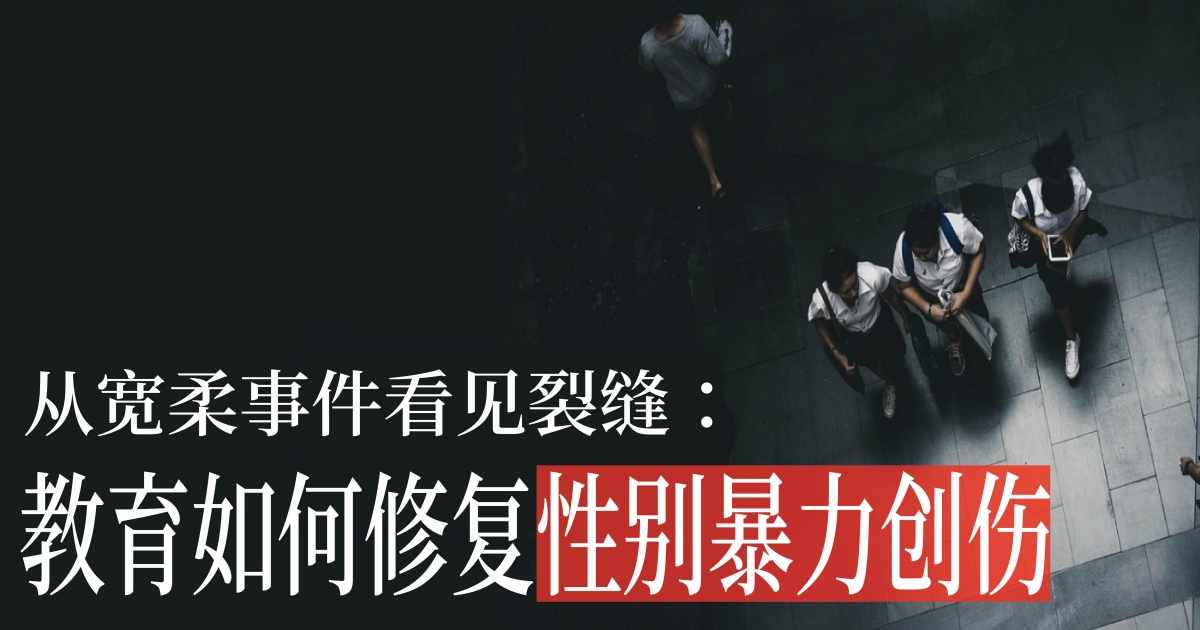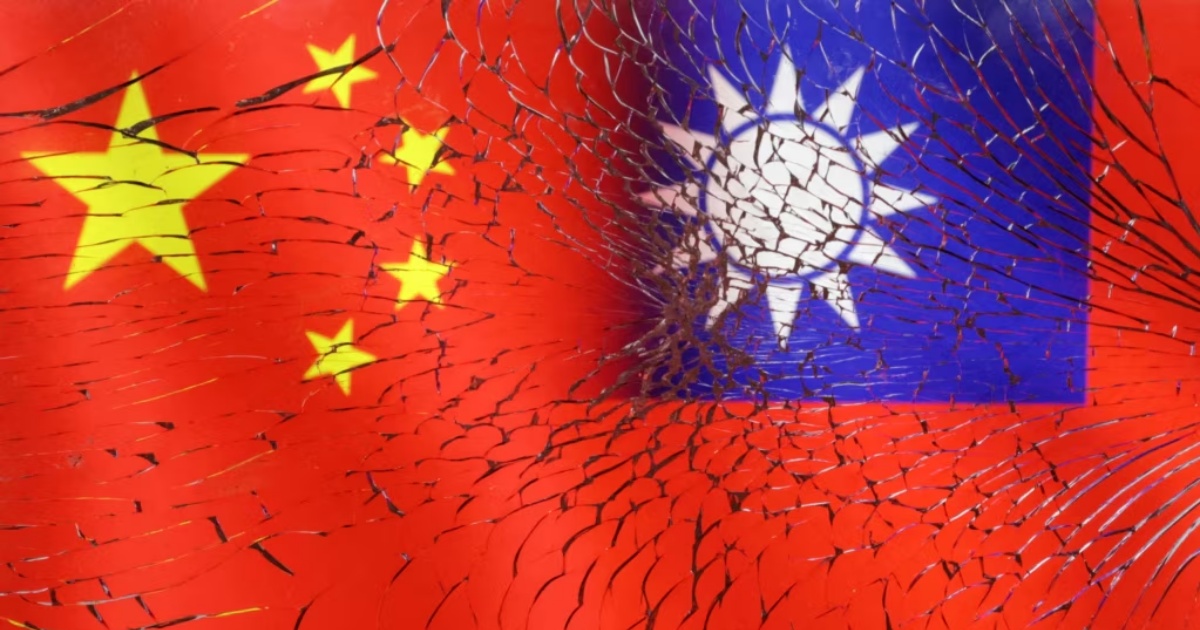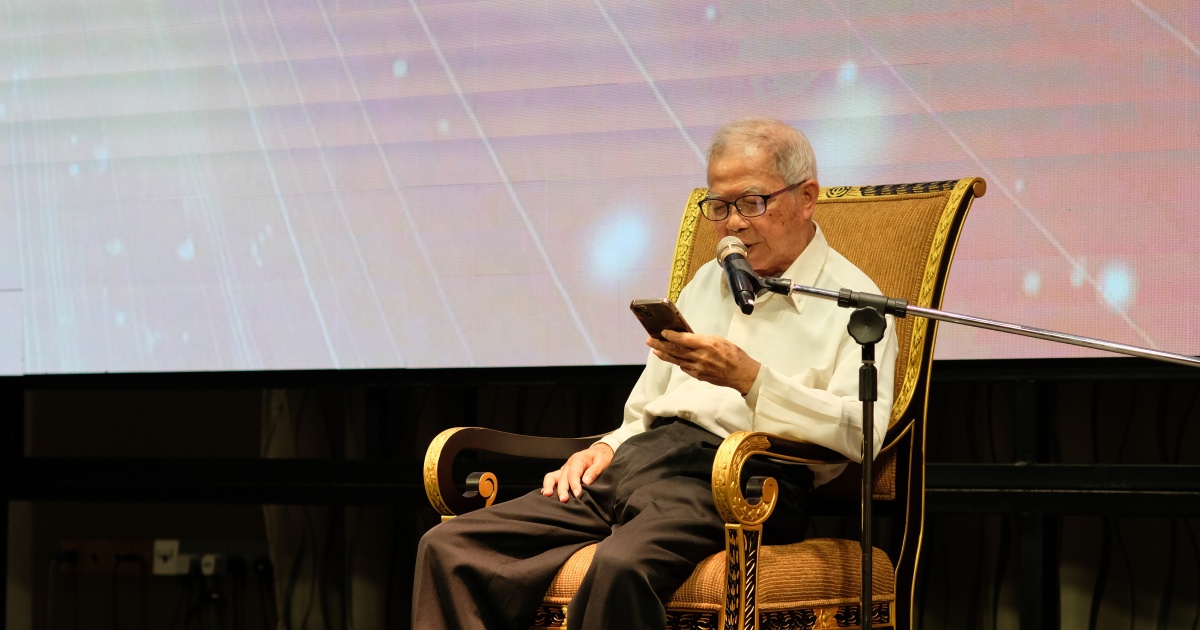前文《马来西亚可能出现特朗普吗?》 说过,“制度”比“经济”重要,因为制度决定诱因。
所谓诱因,指成本利益的计算。我们常常喜欢揣测别人为什么这样做或那样做,结论往往离不开“因为利益大过成本,所以他那样做”。
如果一切都用这句话来解释,那我们什么都没解释到。
关键是制度。所谓制度,其实就是指什么是成本、什么是利益;如何计算轻重、如何排列次序。
制度决定诱因,所以解释现象一定要从制度下手。
一般的经济学课本并不重视制度——他们喜欢在一个平面图上画一条向下弧的线,叫需求曲线;再画一条向上弧的线,叫供应曲线。需求与供应曲线相交的那一点,就叫市价。
俗话说,“有钱赚,就有人做”,背后是这套逻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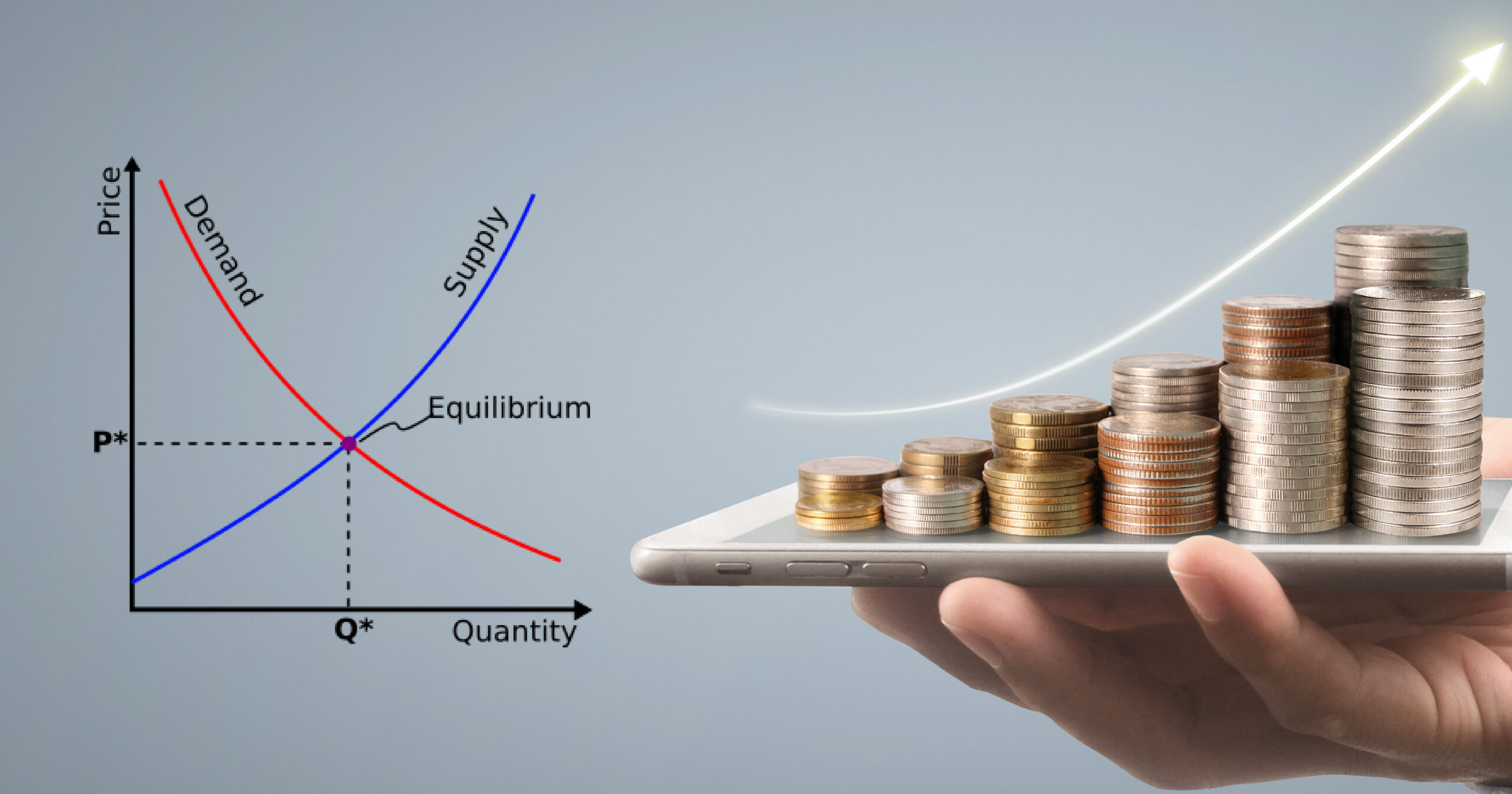
问题是,千千万万的制度当中,市价只是其中之一种。如果经济学只关注由供应和需求所决定的市价,那我们是把经济学想得太狭隘了,无法解释社会上大多数现象。
又或者,一种问题有几项解答,而市价只是其中之一项。如果我们只研究市价就断然下结论,得到的只是经济学的一偏之见,而非科学真理。
经济学是科学,用以解释社会现象。要成功这么做,就要对制度有充分了解。
有关制度的学问,应该是读经济学之前就要有的修养。这不能单靠读课本,必须到真实世界去参与和观察(这个过程或可称作“玩”,就看你用什么心态过活)。可惜今天的学生,从小学到大学,甚至硕士博士,都没有离开过家园和校园,极少踏足过社会半步。
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是关于制度的研究。
如果我们能把注意力从“诱因”转向“制度”,我们将能解释很多看似“不理性”的行为。

马来西亚的社会,有很多东西,是用钱也买不到的、是成绩再好也得不到的、是符合了全部标准也被判不达标的;也有一些东西,明明不需要用钱,现在却必须用钱来买到。例子大家心知肚明,不用我说了。
既然这样,你还相信“问题在经济,笨蛋”?
判断制度好坏的方法
只注重“诱因”的经济学,不能判断价值观上的好跟坏。换言之,没有所谓好诱因坏诱因。诱因是客观的。
是注重“制度”的经济学,为经济科学披上一件艺术外衣,让我们可以判断何谓好制度、坏制度。制度是好是坏,要从结果判断。
要判断结果,就要知道我们原先追求的是什么。经济学不是靠花言巧语,而是用理论和事实来检验好坏。
比如,经济制度的目标是带来繁荣富足。我们检验经济,不是听政府把政策吹得多好多高尚,而是看它能不能实实在在地促进经济发展,带给人民富裕、幸福的生活。
又有一种经济制度,打着消除贫穷为目标,由政府实施扶贫政策。贫穷,人之所恶也,任何有良心的人都不忍见人穷困。然而,扶贫政策却未必能真正帮助穷人脱贫,甚至可能让聪明的有心人从中图利,变成巨富。问题的关键不在“贫”,而在怎么“扶”。

解释制度选择的方法
被人选择的制度,未必是“好”制度,但一定是成本最低或利益最高的制度。
从这个角度分析制度选择,乃至于制度演变,我们即可用上需求定律——随着选择一种新制度的费用降低,它被选取的可能性越大;或者,随着放弃一种旧制度的成本降低,它被放弃的可能性越大。
制度费用(institution cost),是解释制度演变的关键。
让我举例说明。一家商店本来采取自由市场的制度,规定顾客只要肯付10元,就能买到5颗特殊的水果。但是,因为有某种文化含义,某族人愿意付15元来买。由于是自由竞争的市场,商店不容许价格歧视。随着该族人越来越多,或政府想促进该文化发展,推出了特殊水果认证标签。申请标签将加重1元成本,但一旦申请成功,不管对谁,商店都可贩卖15元。不申请标签的只能卖10元,也会失去整个族群的光顾。所以,为了符合文化而申请标签的利益净增加了4元。或者反过来说,转换去新制度的成本降低了。于是,会有更多商店为了符合文化需求,而去申请认证标签。
文化有价。买贵货不一定是笨蛋。认为经济问题跟文化完全无关,才是笨蛋。

制度经济学可解释政治
从实际操作来看,“制度”指的是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这个定义和法律及文化几乎一致——它们都规范了人类的社会行为,三者如一。
然而,三者的成因却有很大差别——法律是民选议员在议会堂争辩的结果;文化是社会风气和教育潜移默化产生的结果;制度,是人类选择的结果。
经济学不能解释法律和文化,但可以解释制度。
在解释制度的时候,我们需要先掌握相关的法律和文化。
偏偏,法律和文化都牵涉到政治。一如马哈迪和阿克马所说:政治是民族、国家和宗教的事(参见前文《华人应该如何回应阿克马》 )。民族和文化对应;国家和法律对应,而伊斯兰教的理念是政教合一。
我一再重复:华人追求的是政治平等,马来人追求的是文化统一。
一个人的好制度,可以是另一人的坏制度。
因此,好的政客必定很忙——他们不是忙着搞经济,那是商人做的事——好的政客一边要忙着说服自己所代表的人群,作出适当的让步妥协,另一边要忙着找对方的代表坐下来,摊开筹码磋商谈判。
可见政治是一门谈判的艺术(dealmaking)。今天,我们的政客不止没有谈判,他们甚至和所代表的人群沟通都没有。当冲突发生时,他们选择静静,逼不得已时才作出仓促笨拙的回应。当官的一味拼经济。这到底是为谁赚钱?

从现行“制度”的结果来看,华人的平等权利没有得到丝毫改进,甚至倒退了;马来人则随着绿潮,进一步巩固了他们的单元种族、单一宗教、单一语言的统一大计。
身为华人,我们虽然讨厌阿克马,恨阿克马的诉求极端;但也不得不承认,他真的是为了增进他所代表的马来人的福祉而战斗。
我们可以批评:从长远来看马来人的利益会受损。但无论如何,那是马来人自由的权利——或许他们甘愿牺牲一点经济利益,来换取建立他们的理想国。
我们应该恨的是,没有人能够掷地有声地为华人权益发声。这包括华人和开明的马来领袖。
还有一点必须强调:华人所追求的政治平等,和马来人追求的文化统一,本来并不冲突,端看政客怎么用智慧斡旋不同利益团体的诉求。

保障自由的制度
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密不可分。密不可分,又实有分别。
一般人在讨论经济的时候,都是在算钱、算利益。偶尔有人搬出“自由市场”的口号,说政府不应该干预经济;又有人会说,无论政府怎样干预经济,最重要是对我派钱、给我补贴。这就是一般人所谓的“经济”。
一般人在讨论政治的时候,则是在谈平等权利、民主、自由等抽象理念。在2018年改朝换代前,希盟的政治人物和公民团体,都是以这些那些“政治改革”的口号来赚取选票。在执政后,却沦为计较现实的机器,妄想靠拼经济、派钱和利益输送的方式巩固政权。
要怎样把政治和经济整合起来研究呢?

经济学大师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有一本通俗的经典,叫《资本主义与自由》。开宗明义,将自由分成两类: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
西方尤其是美国,历来把民主、自由看得比命还重要,这是属于“政治自由”。在二战以后,随着国家越来越“先进”,靠资本主义发家的美国人却开始喜欢上政府管控,提出很多新奇的关于自由的理论,限制“经济自由”。这在70年代把美国弄成犹如实行社会主义的共产国家。
弗里德曼力斥其非。本来一名象牙塔学者,开始著书立说,到处演讲,甚至制作电视纪录片。他的关键论点是,一个国家若失去经济自由,人民必将失去政治自由(economic freedom is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political freedom)。
经济自由,不是指放任商人垄断市场、工厂污染环境、政府毫无管制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是人人在平等的约束下,各自为战,争取自己的福利。经济自由,专指一种情况——政府不干预市价作为竞争制度。
经济自由如何保障政治自由?
弗里德曼举例,如果社会上有人觉得自己政治不自由,又或者觉得社会不公义,那他将需要资金来帮助他宣扬他的思想理念。在一个经济自由的社会,有闲钱的人会比经济不自由的社会多。再者,如果政治钳制了经济,使得社会上的有钱人都有政治瓜葛,那这些有钱人就更加不可能公开支持政治不正确的理念。
美国自由主义传统的复兴
这不是很像最近特朗普胜选前美国的情况吗?一众的科技及商界巨头、教授及知识分子、好莱坞明星,对特朗普及马斯克诸般辱骂叫嚣;而马斯克身体力行,出钱出力出声音,几乎赌上了一切,最后促成了今天的局面。

弗里德曼所提醒的,是70年代的美国。他所宣扬的,无非是一种既保障经济自由、又保障政治自由的制度,而这套制度是美国在经济大萧条前行之有效的。这制度就叫“有竞争的资本主义(competitive capitalism)”,也就是“先进”知识分子是不是都乱骂一通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
美国虽然标榜是自由的捍卫者,她的“不自由”问题在2008年金融危机、奥巴马上台后,一步一步恶化,以致于病入膏肓,导致特朗普两次被选上台(2017-2021;2025-)。这一次,他联同马斯克,准备大刀阔斧整顿美国。
特朗普和马斯克并没有开创什么新的政治理念,他们只是高高扬起前人插下的自由旗帜罢了。
美国的伟大,在于知识与传统。尊重知识,使人及早反省;尊重传统,使人拨乱反正。
经济自由,不一定有政治自由。例子是回归中国前的香港。
经济不自由,就一定没有真正的政治自由。例子就在眼下。
自由,人之所欲也。与其标签和争论不知所谓的“主义”,不如多花时间,好好学习,深入研究一种真正保障自由的制度,然后老老实实拼经济,给自己、家人和国家带来财富和幸福。
▌延伸阅读:张恒学专栏《学而时习》其他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