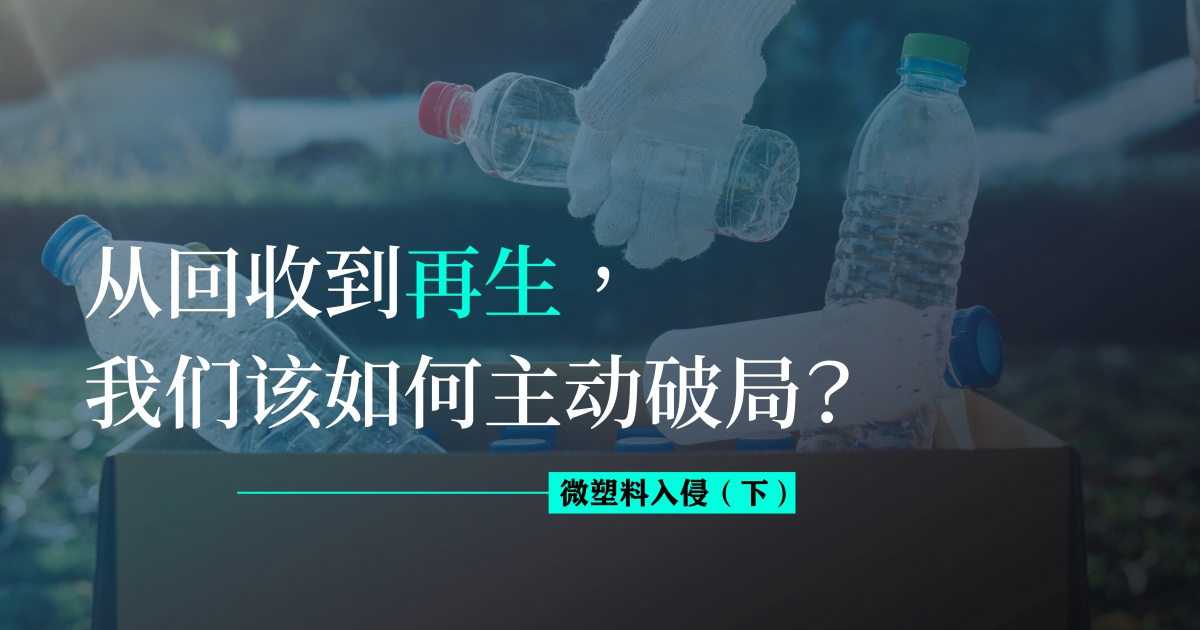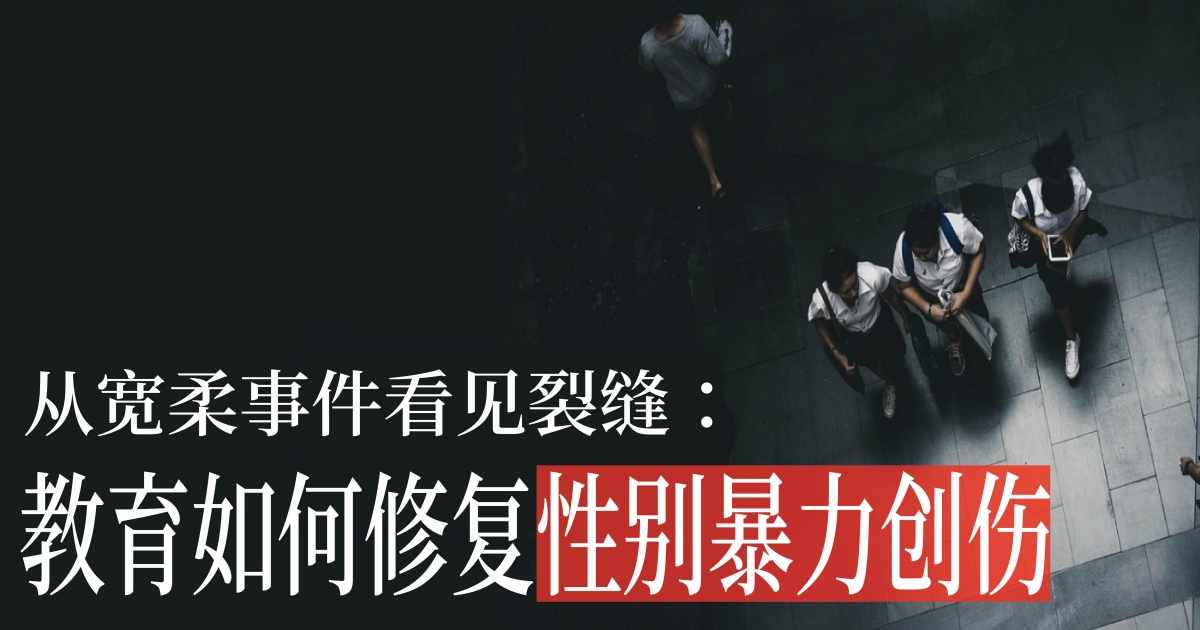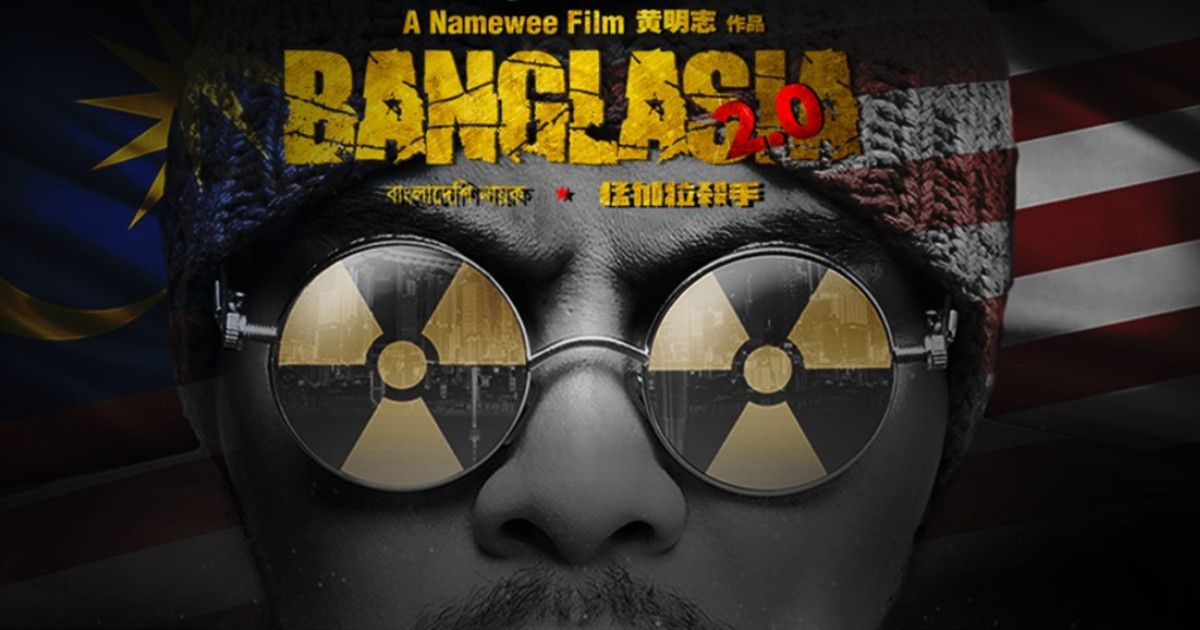2018年2月14日,这是个毕生难忘的情人节。
难忘的并非花束和烛光晚餐,而是这一晚我抱着女儿蜗躺在那4尺乘2尺的儿童病床上。这一夜,特别漫长。
情人节前夕被救护车送入医院后,女儿的血红蛋白只有6.4。入院后,医生立即再次抽血,需确定是血癌还是地贫,同时也要拿她的血样本到血库配血。
医生说,由于她的血红蛋白太低,无论是血癌或地贫也好,都肯定需要输血,而且分几次输血来小量输血,担心她的身体会出现排斥或发烧。
原本倒数着农历新年的心情,直接就往下掉,因为就连农历新年前能否出院也是个未知数。从卫生诊所到入院,从早上8时许到晚上7时许,从先后两度抽血到配血,情人节前夕的晚上7时许开始她人生中的第一次输血。
在输血前,除了核对身份资料和血型外,也要需要签署治疗同意书。这主要是因为每一次的输血都需要承担一定的医疗风险(这在往后会更详细说明)。
整个输血过程要四小时,我在整个过程中要不时注意她的身体有否出现红点、发烧等敏感或排斥的症状,并会在输血前和输血中途分别两次帮她输入一种排尿药物frusemide(呋塞米)。

当护士从她小手背的插管注入药物时,她就不停地哭。当血流入插管时,她直接嚎啕大哭喊着“很痛、很痛”。直至后来在一位医生的解说下,才明白年纪越小会越痛,因为他们的血管很细小,所以当血流入体内时会特别的痛。
那一刻,相信大部分的父母都宁愿痛的是自己。就这样哭着、哭着,哭累了,她就睡着了。
不过,我却无法入睡。除了要仔细观察她的身体状况,护士也会在输血时持续检查体温和血压,确保没有发烧,血压也没有飙高。由于输血机器非常敏感,只要稍微移动就会响铃并停止泵血,所以中途还停了几次操作,需要护士来帮忙重置机器。
那四个多小时,实在漫长。女儿睡后,我急忙搜寻地贫和血癌的治疗方法,虽说这是两种不同的疾病,但它们最终都有同一个治疗方案:骨髓移植。
记得我当记者时也曾报道过血癌和地贫病人募款进行骨髓移植的新闻,邻座同事还曾采访跨国捐赠干细胞的新闻,所以这些资讯对我并不至于完全陌生,但万万想不到我女儿有一天也可能需要这种治疗。
正因为曾经采访过有关血液疾病和地贫的医学讲座,所以知道家族有地贫基因的我,才会在婚前和孕前多次和丈夫确认他并没有地贫基因。奈何,他的血液报告一直以来都一切正常,而他也有每三个月捐血一次的固定习惯。
到了午夜12时许,踏入了情人节,一包80cc的血终于输完了。抱着女儿躺在儿童病床上,脚也伸不直,但这一刻却更深刻感受到拥抱着她的幸福。

“不好意思,妈妈,请问你睡着了吗?”
张开双眼,看见忙了整天的儿科专科医生Dr. Lam站在床脚。
“医生,还没,报告还没出炉,怎么睡得着?”
接着,医生说报告出炉了,有一个好消息,也有一个坏消息。这情节不就像电影一样吗?但这次,主角是女儿,但相信她也不想成为这主角。
医生说,经过检验后,确定不是血癌。我问医生,那是地贫吗?她说,是的。虽然地贫是一种需要长期输血的慢性疾病(chronic disease),但至少没有即时性的生命危险(life threatening)。
我随即问了医生很多问题,包括我和丈夫都在婚前验血检验,为何女儿还会有地贫呢?接下来有何治疗?能否进行骨髓移植呢?诸如此类的相关问题,问了近一个小时,Dr. Lam也很有耐心的、尽她所能一一回复,并拿了更详细的家庭资料。
她提到了几个重点,包括Vanishing twin(双胞胎消失症候群)有可能是因为两个胚胎都有地贫基因、女儿的头颅变大乃地贫症状之一、腹部肿胀是因肝肿大,而我们一家三口需要抽血送往吉隆坡进行基因分析(DNA analysis),以作更详细的诊断(包括地贫种类)。
当医生提及我女儿的头颅变大是地贫症状之一时,当下我告诉医生,有些家人的前额更加突出或头颅更大,甚至被朋友同学取了“金龙鱼”的花名。医生当下建议这些家人去做地贫建议。

此外,医生也建议我们接下来准备一本大本的书,然后将所有的输血记录、血液检验报告和医药报告等,都一并黏在这本书里。日后,我们若要在任何部门或医院求诊,那这本书的记录就非常完整且重要。
尽管地贫并非致命疾病,而输血也能减少地贫症状,还能延长患者生命,但每一次输血和长期输血都需承担一定的风险,而日后所服用的药物也有一定的副作用。
也因此,从一开始确诊地贫的那一天开始,我就一直祈愿希望女儿有一天不再仰赖输血,而骨髓移植是当时已知的唯一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