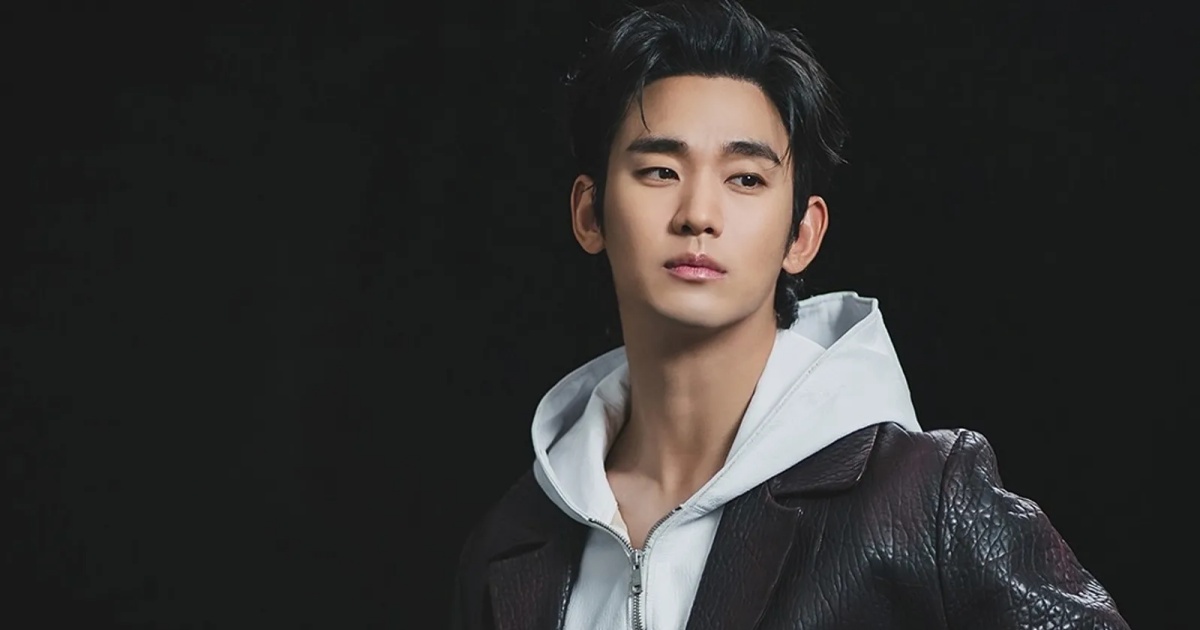最近常关注香港的政治问题,尤其是港版国安法从天而降,让港人诚惶诚恐,觉得真正意义上的繁华而自由的香港其实已经随着“香港制造”的货品标签被特朗普逼除下而灭亡。有能力、有耐力和有些经济能力的香港居民都在寻找移民外国的出路,让人不胜唏嘘。我想借此向香港人和香港精神致敬,谈谈我喜欢的夫家香港桌上的家常菜。
前夫是已入了加拿大籍的香港人;虽然我从未长期在香港居住过,可是去过香港无数次,每一回逗留数天至数个星期。多数是会在他们家西环坚尼地城的西施大厦公寓暂住,也常在他们老家附近租酒店,或者索性住老家一两个晚上探访家人过后,其余时间就搬往酒店。 (因为其实我也是个酒店控,旅游时尤其喜欢尝试换租不同的酒店。)

已故的前婆婆(我叫她奶奶,香港是这么叫的)是山东人,从小却在北方的天津长大,至少女时期才随家人移居香港。公公倒是地道的北方人,在天津出生长大,后来也移居了香港,可是他长年和那个年代的父辈一样在大海上航行(退休前是前香港特首董建华家族航运公司的一名货柜船船长),始终也没有学好字正腔圆的广东话。他们在家里和子女孙辈说的还是北方话。
不说不知,香港的西环和上环一带原来是早期北方人落脚集聚的社区,老爷子和老奶奶都可以在公园及菜市场里和邻里说着家乡话,借以疗慰乡愁。
来温哥华住在我家时,婆婆会把家乡的玉米馒头、葱油大饼和牛肉烙饼搬上我们的早午晚餐桌上。中国南方吃米饭,北方因盛产小麦,所以北方人非常热爱他们的面条、馒头、大饼和饺子。她搓面团的功夫很了得,做的粗粮馒头又有嚼劲又有绵密弹性的口感,令当时只会做面包的我十分佩服。

大年除夕有一年我在香港和他们家人度过,饺子是一早已经包好了的,有白菜猪肉和猪肉韭菜两种。单大儿子一个人一个晚上就可以吃下五十个饺子——可见那有多么好吃!他们煮饺子最要紧是皮薄馅厚,而且要点两次水——水煮沸了下饺子,煮滚一次再加入四分之一杯水,然后再煮沸了水又添一次室温的水,这叫“点水”。可确保厚厚的内馅可以煮得熟透,还可增加饺子皮的弹Q度。

虽然家里有五个兄弟姐妹,其中一个弟弟和弟妇跟他家里是不怎么往来的,只是过年或红白事上会出现。他们小时候很穷,父亲不在身边,全家租住所谓的板间房,与一大群房客共用厨房和厕浴,这是从小家境小康的我们所无法想象的。
我听前小姑和二叔谈话时说起,小时候学校老师带他们外出野餐,其他小朋友都带着(他们眼中认为)好好吃的零食和水果,他们只能带着别人三文治切下的面包边。以前的面包店会把做完三文治后切下的面包外层较硬的皮以便宜的价钱一包包卖出,而低收入的人家就会把这些面包皮买回去当作小孩的零食,连牛油都省下哦。
数年前前小叔嫁女,盛大的婚礼在海边私人会所的花园草地上举行;小叔已贵为香港垄断市场的煤气公司高层,全家人也早已入了加拿大籍。他们离开小时候的寒酸背景已经很远很远了,足见八十年代的香港经济奇迹造就了那一代人可以努力力争上游(upward social mobility)。反观如今的香港年轻人,想要安居乐业谈何容易。
炸酱面又是另一道我的前婆婆拿手的好菜。

北方人煮面照例要烫煮后过冷水保持面的弹性口感。配料也很讲究,绝不是简简单单切一些青瓜和红萝卜丝就完毕,还要有煮过的毛豆、大黄豆芽、生的蒜头、大葱的葱白等等很澎湃地摆满了碗,就像一座小山那样。
婆婆用的是七分瘦三分肥的五花肉切成肉丁,用黄豆酱豆瓣酱和甜面酱去先炒,后加入料酒再熬;过程十分的耗时兼且讲究切工和调味功夫,但是味道非常的香浓好吃。连我来自东岸小镇的加拿大好友Ken吃了也是一碗接一碗,竖起大拇指。
我想起的香港不是我儿子最喜欢的茶餐厅美食如沙爹牛肉公仔面,也不是老式西餐如太平馆的瑞士鸡翼,也不是添好运的酥皮菠萝焗叉烧包,而是香港少数北方人家里吃了三代人的小吃和面点。你一定看了一定摇头抓破头皮,但是这里面却装载了闻家人的满满回忆。
延伸阅读:小尔专栏《饮食男女》其他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