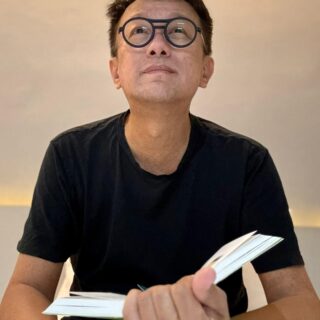站在伦敦老牌餐厅M.Manze前,看到穿着绿色制服的店员端出一盘盘“派和土豆泥”(Pie and Mash)。店内只有几张桌子,即便是拘谨害羞的英国人,此刻也不介意与其他食客搭台。棕红色的木头椅子很长,有点像教堂的长椅。墙壁上贴着的小花砖让人联想到潮湿的南洋。

白瓷盘中的土豆泥盖了一层又一层,热乎乎的牛肉派浸泡在绿色的粘稠酱汁里,说到这里也许有人要皱起眉头。但相比店里的黑暗料理之王——鳗鱼冻,这应该算较为温和的食物了。
坊间一度流传英国盛产黑暗料理,黑布丁、肉馅羊肚(Haggis)、朱古力油炸鬼,听起来令人闻风丧胆,但其实都尚可接受。阔别多年,竟有些怀念这些所谓的黑暗料理。
想起汪曾祺先生说过,“有些东西,自己尽可不吃,但不要反对旁人吃。不要以为自己不吃的东西,谁吃,就是岂有此理。他们爱吃,你管得着吗?”
满足口舌之欲,更多是关注自身的感受,也就无需在意旁人的眼光。直起腰板,用汤匙舀起一块鳗鱼冻。入口的一刻极微妙,果冻般的质感,锁住了整片大海的味道。

鳗鱼冻(Jellied Eels)大约兴起于英国工业革命时期,是用泰晤士河里的康吉鳗(Conger Eel)制作而成,在相对贫穷的东伦敦地区较为常见。这种高蛋白、高热量且低廉的鱼肉制品深受当时工人阶级的欢迎。鳗鱼冻通常与“派和土豆泥”一同售卖,在二战后,伦敦售卖鳗鱼冻的餐厅曾一度高达100间。
如今,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早已远去,想尝试鳗鱼冻,只能去伦敦仅存的几间老店。而食客更愿意去日式料理店享用蒲烧鳗鱼,这种冰凉、粗糙,且带着海水咸腥味的鳗鱼冻,已跟不上时代的步伐。

这道让人直皱眉头的英国黑暗料理之王,到了中国,又变身为“剩菜之王”。鳗鱼冻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在宋朝时人们便把鱼做成凝冻,并取了一个风雅的名字:水晶鲙。因常被文人墨客当作冷盘,拿来醒酒,故又称“醒酒冰”。后人依此做法,用白鸡、猪肉皮或猪脚等,慢火熬制,直至汤汁变得黏稠,再冷冻成半透明块状的各种水晶鲙。这道美食在宴席上常常以冷盘的形式出现,算是开胃菜之一。
在中国,鱼冻也是少数横跨南方与北方的食物,是家里的味道。不过那又是属于主妇的另一种智慧了。吃剩的红烧鱼拿去冷藏,第二天汤汁便凝结成晶莹剔透的鱼冻。冰凉的鱼冻融化在温热的米粥里,一口接着一口,那浓缩的鲜味是专属于家里的味道。“剩菜之王”的名号,绝不是在夸张。在外的游子,谁不惦念母亲做的鱼冻呢?
鱼要趁冷吃,绝不是谬论。除了隔夜残羹变成的家常鱼冻,更为考究的做法当属潮州鱼饭,那鱼皮之下凝结的鱼冻,琥珀一般,一口难忘。

鱼饭,又称熟鱼。与老婆饼、油炸鬼一样,鱼饭也是“名不符实”的食物,实质上里面一粒米都没有。所谓鱼饭,是指新鲜的海鱼不经打鳞、劏肚、去腮,先用盐腌制,一层盐,一层鱼,铺在小竹篓里。再放入盐水中煮熟,最后晾凉即可食用。
昔日潮汕渔民因没有保鲜冷冻的条件,对海产品有一套自己的制作方法:一鲜二熟三干四咸五腌。其中的“熟”便是制成“鱼饭”。在穷苦年代,熟鱼成为潮汕渔家人用来充饥的食物。以鱼当饭,这种看似屈服于命运的妥协之举,是潮汕人以退为进的生存智慧。
如今在潮州粥铺都可看到鱼饭的身影。鱼经盐水浸泡后释放出加倍的鲜甜,鱼皮内外若隐若现的鱼冻,更是鱼饭的精华。忍不住吮吸一口鱼冻,鱼肉也变得紧实有弹性,配上普宁豆酱,碗里的白粥很快见底。即便是富贵之家,餐餐都是鲍参翅肚也会生厌。反倒是这些不起眼的冷盘,才是餐桌上最温情的陪伴。

无论是令人闻风丧胆的英国鳗鱼冻,还是潮州粥铺泛着冷光的鱼饭,这些诞生于劳苦大众之间的食物,在果腹之余,都隐藏着独到的智慧。
鱼要趁冷吃,不是谬论,反而更像是一种人生哲学。在沧海横流中,坦然接受命运的安排,似乎比汲汲以求更难得。
不急,鱼要趁冷吃。
延伸阅读:王茜专栏《马来茜亚》其他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