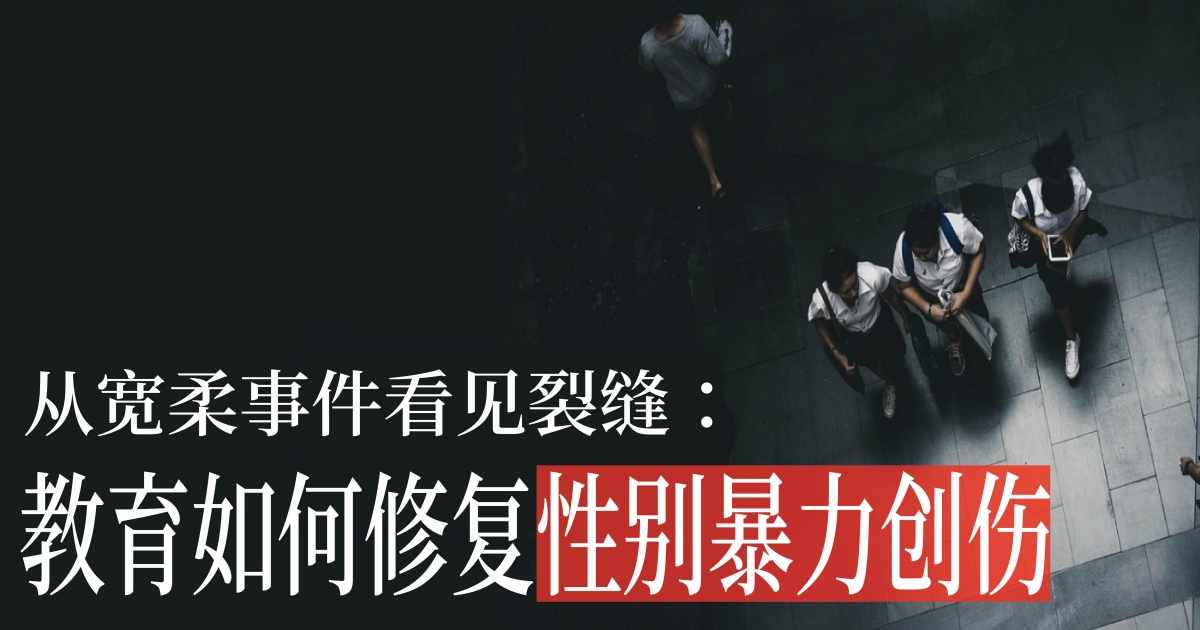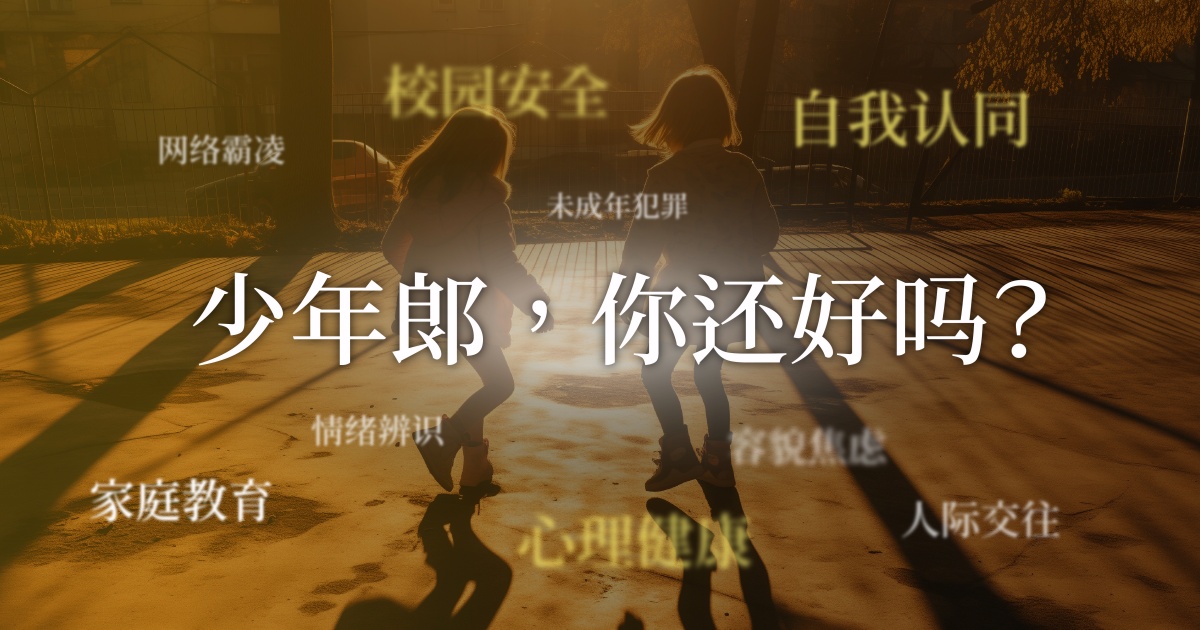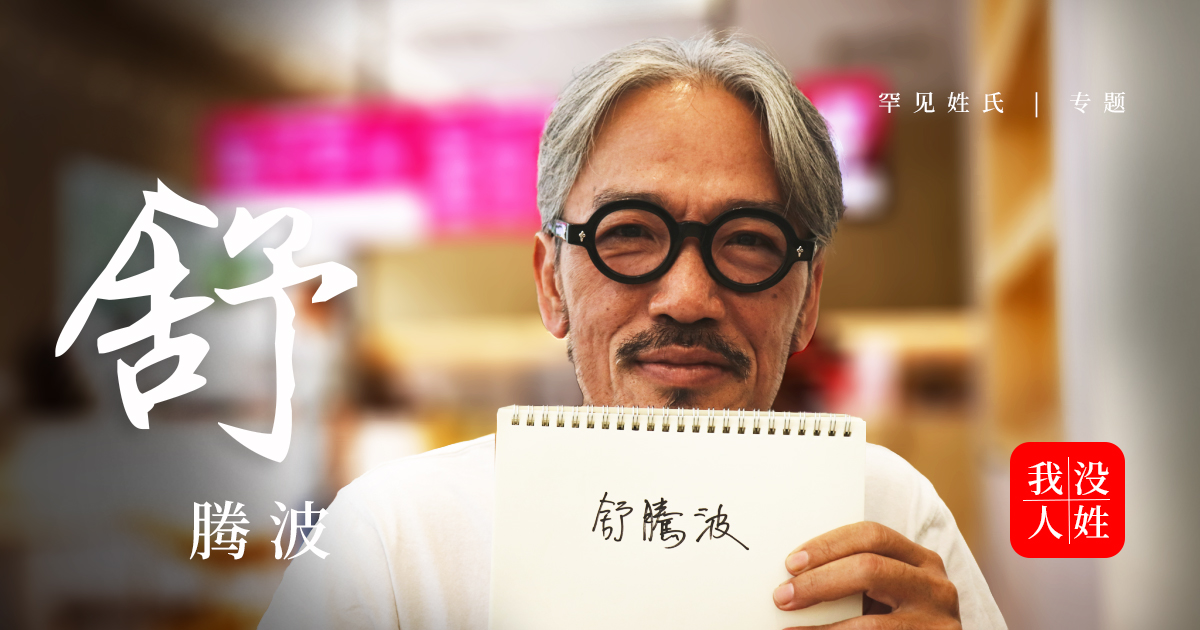清明前后,最惦记的便是带着草木香气的糕团。往年吃的是青团,糯米制成的糕团,艾草中带着一丝丝中药味,一口下去,像抱着修仙的香炉,直达天庭。
味觉的记忆一遍遍被唤醒,味蕾也跟着蠢蠢欲动。想到同样带着草木香气的鼠壳粿,在夜色中直奔半山芭的老二潮州餐馆,进门便看到长桌上摆满粿品,或咸或甜,形状分为“桃粿”和“圆粿”两类。甜口的元宝龟粿每次都最快卖完,这次发现新添了芝麻花生馅料的艾草粿,“时粿适时气”,想必是应时令。清明时节,将艾草或鼠麴草糕混合糯米粉制成糕团,是传统的时令美食。

乌黑的鼠壳粿,像一块油亮的墨砚,下面垫着蕉叶。店员拿去厨房按照十字形划开,再端回来时,已露出里面金灿灿的菜圃和虾米。鼠壳粿皮薄,馅料多,用筷子托住,要快速放进口中,不然馅料会洒落出来。与中国江浙地区的青团不同,鼠壳粿的皮更薄、更软,在口中像棉花糖一样化掉。鼠壳粿的馅料可咸可甜,也可咸甜两掺。不咬下去,你永远不知道里面是绿豆蓉,还是菜圃虾米。

鼠壳粿,其实与“鼠”无关,因由鼠麴草熬汁制成粿皮,便被称为鼠壳粿。关于鼠壳粿的传说,要追溯至南宋末年,据说当时元兵入侵潮州,流离失所、饥肠辘辘的百姓无意中发现了鼠麴草,以此充饥。后来便把这种野草熬成汁,掺入糯米粉,制成粿。

这里的鼠壳粿多由艾草制成,可能在本地较难寻到鼠麴草。艾草香气浓烈,纤维感明显;而鼠麴草韧,制成的粿皮更有弹性。周作人在《故乡的野菜》中也有提到鼠麴草,“黄花麦果通称鼠曲草,系菊科植物,叶小微圆互生,表面有白毛,花黄色,簇生梢头。春天采嫩叶,捣烂去汁,和粉作糕,称黄花麦果糕。”
潮州的粿,蒸,或煎至两面金黄,都别有一番风味。油煎,咸口的红桃粿最合适。外面的粿皮在平底锅中被烙出金黄的印记,包裹着香菇虾米、半肥瘦猪肉丁和炒香的花生碎,随着油温上升,馅料快撑破粿皮。出锅后淋上酱油或卤水汁,焦脆的粿皮散发出米香,满口油润。

红桃粿、水粿、韭菜粿、沙葛菜粿,吃不完的粿,拜不完的神,是潮州人的日常。印象中最美味的水粿来自SS2一位华人阿姨经营的移动糖水餐车,疫情时,打包一份绿豆糖水,外加咸水粿。厚实软糯的水粿,像一个小碟子,中间盛放着脆爽的菜脯粒。每次隔着口罩交谈,最后都不忘提醒我加辣椒酱。摘下口罩之后的日子,再也没见过这个移动糖水餐车,念念不忘那雪白的水粿。
人真是脆弱的动物,也许只是寻常的某种气味、某种味道,便成为牵绊一生的精神依赖。

传统节日早已被冲淡,时令美食也不再限定。如果你愿意,餐桌上可以同时出现来自五湖四海的食物,北京的绿豆糕、嘉兴的鲜肉粽、上海杏花楼的青团,还有云南的鲜花饼。
记忆中太多回不去的味道,也不愿自寻烦恼。在这个四月天,咬一口乌黑发亮的鼠壳粿,咀嚼间尽是艾草的香气,也不算辜负吧。
延伸阅读:王茜专栏《马来茜亚》其他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