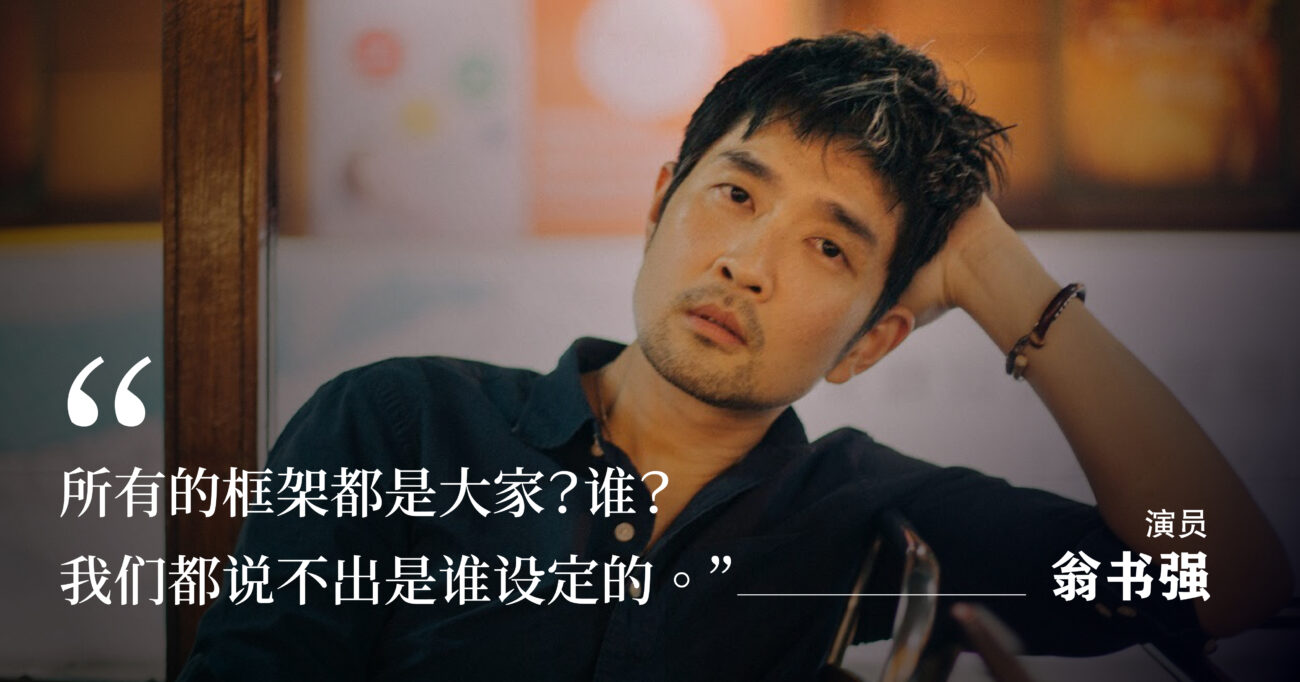台湾瀚草影视制作的迷你悬疑剧《谁是被害者》(The Victim’s Game),无疑是2020年最备受瞩目与讨论的台剧,由张孝全、许玮甯、林心如、王识贤等实力派演员主演。短短8集的叙事长度,已在Netflix上稳占台剧第一名,还在网络上掀起热烈讨论。与其他Netflix原创台剧不一样的是,《谁是被害者》的故事主导权掌握在瀚草影视的手中,一直到后制阶段,才公开竞标,由Netflix购下独家播映权。剧本改编自天地无限的悬疑小说《第四名被害者》,由《人面鱼:红衣小女孩外传》的庄绚维导演,与《红衣小女孩》陈冠仲副导演两人合作执导,精准地把控悬疑题材作品的节奏与呈现方式。该片也由瀚草影视总经理汤升荣担任制作人之一,而他在这之前制作的作品,就是另一部口碑爆棚的高分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访问》这一次约访三人,探讨作品中各式议题的呈现,尤其是作品中多次提到的矛盾——是死比较需要勇气,还是活着需要勇气?
“我们有权利结束自己的生命吗?”
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自杀者都是负罪的,在死后也不得安宁。如天主教深信自杀死去的信徒会下地狱,在华人的民间信仰中也认为自杀死的人,在死后也会在同样的地方,重复地进行自杀的举动,在无间地狱内一而再地重复自杀的痛苦。
这些信仰无论真假,都有一个很明确的指向——教育大家不要轻易地自杀。
《谁是被害者》稳占Netflix台剧第一 以自杀案剖析社会底层的痛苦
自杀课题是《谁是被害者》的剧情轴心,故事从一起溶尸命案开始说起,张孝全饰演患有亚斯伯格症(Asperger Syndrome)的鉴识官方毅任发现这起命案竟然和自己失联多年的女儿有关。于是他为了私下找出真相而隐瞒证据,和许玮甯饰演的记者徐海茵联手。方毅任的目的是要保护女儿,而徐海茵则是为了独家新闻流量。但随着案件的发展,拉扯出多名生前徘徊在社会边缘的弱势,看着他们死后与生前的经历,俩人的观念也慢慢有了转变。


“我觉得它有一个比较创新的想法,传统的悬疑推理剧都在找凶手是谁,但是这一次的确反过来,我们要找到被害者到底是谁。”庄绚维导演这么形容这一次的剧本。确实,《谁是被害者》的剧本原型取自悬疑小说《第四名受害者》的优秀架构,但编剧梁舒婷与徐瑞良两人决定放弃原有的叙事方式,另外撰写了不一样的故事发展。
在调查过程中,方毅任和徐海茵发现他们正在面对的,不是一宗连环凶杀案,而是一宗连环自杀案。由七个死意已决的大活人聚集在一起筹谋缜密的集体自杀计划。
故事若只是一起命案,尤其当它是一起并没有涉及第三者的自杀案时,也许是一部120分钟的电影就能说完。但这部影集总长480分钟,从筹备、拍摄、后制总共花了五年的时间,做足有关心理学知识、鉴识科与警察调查工作、媒体工作生态等等的田野调查,才搬上了台面。


痛苦的人有权利选择自杀吗? 导演庄绚维:有权利,但自杀不是唯一选择
编剧在这剧本中注入了多项有关精神障碍、性别议题、劳工权益、艺术伦理、老年照顾与官商勾结等等议题,引起大众的讨论。他们发出一个核心问题:如果死能够让人从现况中的痛苦解脱开来,那么人有权利选择自杀吗?
“我觉得生为人都应该对自己的生命和选择负责任,我认为剧本中的他们都有资格想要自杀,他们都是在巨大压抑下才会作出这样的选择。”庄绚维导演这么说。
《谁是被害者》阐述了七个社会边缘人的故事,他们分别有饱受歧视与霸凌的第三性、过气的女歌手、受资方压迫的员工、不被正名的艺术家、更生人等等,他们都是不被接纳、不被认同也不被理解的边缘人物,他们的人生没有希望,反而把“死”这回事看成是一个崭新的希望,看作是发声方式,希望借此获得社会的关注,能成为他们控诉痛苦的管道。
这一点十分讽刺,死竟成为了他们赋予生存意义最立体的选择。

庄绚维认为,人当然有权利去决定自己的生命要怎么终结,大众不应该一味地谴责受害者,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别人正在经历什么。但自杀同时也不应该是唯一的选择。
因为除了死之外,我们还可以选择交给时间。
庄绚维:“有个比喻说,你把手放在蚂蚁面前,它是走不到对面的。但是身为人,我们知道你绕过去的话那个关卡就过了。我觉得这个就是,你给自己多一点时间,给自己多一点成长的时间或者是给这个世界多一点成长的时间,它其实会带来改变。”

活着和死亡,哪一个更需要勇气?
在报章上我们常常可以读到自杀新闻,不管是学业压力、为情所困还是财务问题,人们看了总会感慨:“都有勇气死了,为什么没有勇气活下去呢?”这句话带着惋惜,同时也带一点责备的意味,让自杀者看起来只是个临阵脱逃的懦夫,不敢面对问题。那么到底是死亡比较需要勇气,还是活着比较需要勇气呢?
陈冠仲导演:“当然结束生命是一个选择,但我们想跟大家说的是,活下去其实是需要更大的勇气。”
《谁是被害者》传递正能量的方式,并不是简单直接地把正能量交到观众手里,让观众认可“活下去才会有希望”这样的一剂良药。因为这样的正能量并不奏效,只要我们一天不是站在自杀者的角度看待这问题,这些正能量也不过是另一种强加的负能量,于事无补。
在一般人看来自杀是自残的行为,伤害自己也伤害他人。但在自杀者眼里,自杀是解决痛苦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是他在重重困难中唯一能掌控的事情。陈冠仲看来,我们也许应该更关注,是什么让他们选择走上自杀这条路?我们作为旁观者,可以做些什么去阻止它发生呢?
陈冠仲:“其实我们这个故事就是在向这些想要放手的人说,我们要如何去抓住他们。我们也希望可以透过这部戏,也许看起来像是悬疑推理的剧情,但其实更像要开启的是一种对话。就是我们把议题都变成一个故事让观众都可以看到,也许也会让正处在同样遭遇的人能有他们不是孤单的感觉。”

自杀不只是选择生与死,而是选择痛苦地活着还是寻死求解脱
活下去还是寻死来解脱,并不是一个单纯二元对立的辩论。剧组用剧情向大众揭露,当人在面对痛苦时,他面对的不仅此是一个是非对错的难题。他正在面对的是生活中所有的选择都被捆成一个个死结,他无法解开,也求助无门。正因如此他才会游移在活着受苦,还是选择死去解脱的极端选择中。
《谁是被害者》要传递的是,即便生而为人让你觉得很痛苦,你也要试着活下去,因为只有这样才会有改变的希望,他们告诉观众“活下去才会有希望”确实是一剂良药,只是它是苦口的。
庄绚维:“如果你当下选择了死亡,那其实你原来在意的问题是不会被改善的,只是与你无关而已。但是活下去,你还是会遇到新的问题,即便如此,因为你活下去了,你有了很多时间。
时间就可以改变很多人的观念,很多人的想法,像是以前不被接受的事情,现在也被接受了。你只有活下去,你才会看得到事情有改变,价值观、观念的改变。

“其实我们现在的社会,很多价值观都在改变。我觉得要仔细说这面向,可以讲得很大,毕竟世界上那么多人。但这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怎么去接纳每一个人,怎么去包容每一个人的问题。”

但是,我们怎么会知道活下来就一定会变好呢?
毕竟能选择走上死路,就意味着生命中所有的部分都是黑暗的。在这样的境况中,该要凭借什么去相信,只要活下去就能看见曙光呢?为此两位导演认为,能辅助我们坚持下去的,是希望,是身边的人给予的支持。而制作人汤升荣也认为个人信念很重要。谁也无法保证好的事情会发生,但我们要相信,成事在人。
明天与无常,是谁先到? 汤升荣:常常是无常先来
“生活有太多烦人的事情,我觉得我们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排除这些难以预料的事情。谁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是无常先来,还是明天先到?常常是无常先来。”制作人汤升荣,汤哥笑着说。
汤哥表示这是个很讽刺的世界,有的人因为走不过生活的难而选择去自杀,有的人却费尽全力想活下去,最终还是逃不过命运的安排。“台湾有个很重要的演员叫吴朋奉刚去世了,我们所有朋友都一阵哀嚎,这么好的人怎么就这么走了?他如果活下来我们会有更棒的演员在这里。我的朋友前两天过世了,他得了大肠癌,奋斗了五年。他多想活下去,就是这些事情都在告诉我们,很多人都在努力活下去。”

汤哥也理解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人生,不能说把一个普世价值观放到某个人身上,我们决定不了命运会怎么安排,但我们能够决定自己能够怎么活。
“我们永远都没办法抛开命运的安排,可是成事在人。”
台剧加大写实力度以影视探讨议题 汤升荣:展开对话很重要
在《谁是被害者》播出后,大众对剧中有关正义、道德与人权课题进行讨论,无论是有关“人有权利选择自杀吗?”,或者是“作为旁观者,我们可以如何阻止自杀的发生?”,也或者是“用谎言来维持的正义还算是正义吗?”,这些讨论从剧中到剧外,彼此相互影响、延伸,成就了公共所需要的讨论空间,而这早已经是台湾剧本近年来司空见惯的现象。
当部分人对台剧还停留在长篇幅的乡土剧或是聚集帅哥美女的浪漫偶像剧时,实际上近年来的台剧作品不断加强写实力度,透过剧情反映社会问题,让观众能更清楚地认识议题,并展开对话讨论。作品如《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他们在毕业之前的一天爆炸》唤醒大众对青少年议题的关注,还有不得不提及去年年初引起广泛讨论的高分台剧作品《我们与恶的距离》。
《我们与恶的距离》剧情改编自真实事件,从一起随机杀人案件,剖析加害者与他的家属、被害者与他的家属、司法人员与媒体的反应,尤其挑起对死刑存废的巨大争议。此外剧情还针对精神障碍与媒体生态、传媒伦理进行多方面的讨论。

从《我们与恶的距离》到《谁是受害者》,他们的共同点即是透过影视化时事议题,引起了社会大众的热烈讨论。作为这两部作品的制作人,汤哥看来一个戏剧最重要的前期工作就是剧本的故事铺排,只要有了一个基本方向,剧组要做的就是紧紧地抓住核心。到最后作品呈现出来的时候,要问问自己,这部作品可以给到观众除了娱乐之外,还有什么收获?
“《谁是被害者》和《我们与恶的距离》这两出戏,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会引起很多对话。它都是把社会上面发生很多不同人的样子,放在剧中探讨。我觉得看过的人都会想要去探讨,到底什么原因导致这个结果?我觉得这个探讨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每次站在一个大众媒体的工作上面,我们让这个社会去对话,互相认识,我想这是我做这两部作品以来很重要的心情状态。”
在影视作品中注入现实议题有助于扩大议题本身的讨论范围,并且透过戏剧张力让议题本身能在“虚构”的环境下呈现,让观众有了全能的上帝视角,透过各种假设与预设,去看待议题的各个面向,并且放到现实面来讨论。
尤其来到这个网络无处不在的时代,观影习惯的主动权从从前传统媒体的手上,转到了观众的手上。观众能决定自己要看什么,而不是一味地守在电视前,电视播放什么他们便看什么。如今窜流媒体从Netflix到Apple TV再到Disney+,让观众无时无刻都可以选择自己想看的内容,可以选择储存、重看或者快进剧情。这是影视作品创作人要面对的问题,除了和彼此间竞争,还要适应不同的观众有不同的观影原则。
汤哥认为和戏剧本身有不同的类型与功能一样,观众也有不同的观影原则,有些人看了会感同身受,也会有人看完就只当作是娱乐消遣。要真正让一个社会议题在戏剧中发挥作用,让观众获得一些资讯而不是沦为创作题材的消费对象,就看作品有没有促成对话或者影响大家的看法。
“如果你不去做的话那么这个社会就不会有这个对话、运作,那你说它是不是一个消费呢?也许你可以从这个角度看,也许是,但是消费就是不好的吗?我们并没有硬是要导向一个要你们去接受的事情,但它必须透过一个行为、模式或者过程得到大家的探讨,我觉得有对话就可以继续往下走。
影视化社会议题可实际带来改变 以《寄生上流》、《熔炉》为例
就像《我们与恶的距离》,那时候在探讨杀人犯事件的时候,台湾内部就起了很多探讨,甚至对于媒体是不是可以在报道的时候,有一些界限或者范围?我记得那时做《与恶》的时候,我们的立法委员就在咨询这件事情,希望可以去落法,透过法律去限制媒体的一些界限,让他们不可以越过这个界限,必须要保有一些新闻媒体的功能,那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例子。”
影视作品的现实性到底是引起社会关注还是沦为消费议题,最重要就是这作品本身有没有为现实社会带来一些对话的空间,有讨论,有批评,才能有反思,才能有改变、进步的可能。去年奥斯卡大热电影《寄生上流》就因揭露了韩国阶级与贫富悬殊问题,让韩国政府拨款改善居住在半地下室家庭的生活环境。而在2011年上映的韩国电影《熔炉》也因翻拍自现实案件,讲述聋哑学院爆发的虐待与性侵案而获得韩国法院关注,重新调查案件,并且间接协助通过了《性侵害防止修正案》,又名《熔炉法》,其中包括让性侵身障者或13岁以下的幼童,最高刑罚可判处无期徒刑,并且废除案件的公诉时效期等等。
一部承载着现实意义的影视作品,若是能做到改善现实问题自然是最好。但并不是事事都能顺遂或者合适,汤哥认为要求透过每一部影视作品去改变现实实在是有点苛求,但如果观众因此而感受到多一点价值观或者鼓励,就算是成功了。
“我们也收到一些很好的回响,我提两个例子。一个他分享自己的经历,说起爸爸是自杀的,他们曾经很痛苦,现在他也终于走过来了。另一个是他本身有忧郁症的倾向,他说他看完戏以后,觉得自己也没有那么糟了。
我自觉得说每个人都可以表达,这是自由社会很重要的一块。那每个人表达的内容都不同,透过戏剧我们想要传达的就是这样,如果你们从中间获得一些好的价值观,你们可以尽量去表达;如果你们不喜欢也没有关系,毕竟这就是戏,这就是提供我们多元社会的一个可能性。”

汤哥:“我们是一群人的时候,一定会有不同的问题,或者是自己的问题。现代社会有很多的问题、不公,或者是对生命的否定。我觉得在这个疫情影响之下,各个国家都在面对这样的问题。不管是哪个国家、地区,他们都在面临这种事情的探讨。比如说美国这段时间发生黑人权益的事情,我觉得我们社会上常常会有在彼此不够认识不够了解的状况下,做的一些互相伤害。后来也有让我们非常感动是美国的一个地区白人警察为黑人下跪,或者是他们互相牵手,那是非常感人的画面。我觉得互相谅解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
拥抱多元是《谁是被害者》想要呈现的价值观,它需要多方相互了解、谅解,提供资讯,接受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个体,有不一样实践生活的方式。我们需要明白的是这是一个各司其职的社会,唯有保证平等的状况下,让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方施展不同的功能,这个社会才能共同、平衡地运作起来。所以自杀不是对的,也并不一定是错的。像导演说的,这个世界一直在改变,价值观也一直在改变。
若说性别是流动的,那真理应该也是如此,会顺应时代与人们拥抱多元的需求而改变。不管你是第三性、更生人或者是任何想要获得关怀与关注的人,我们都只是在社会中寻求最合适的生活方式。大众能够多一点包容,多一点同理,这个社会也许就能少一份伤害。
否则在庞大且失衡的社会中,我们迟早只会成为彼此的受害者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