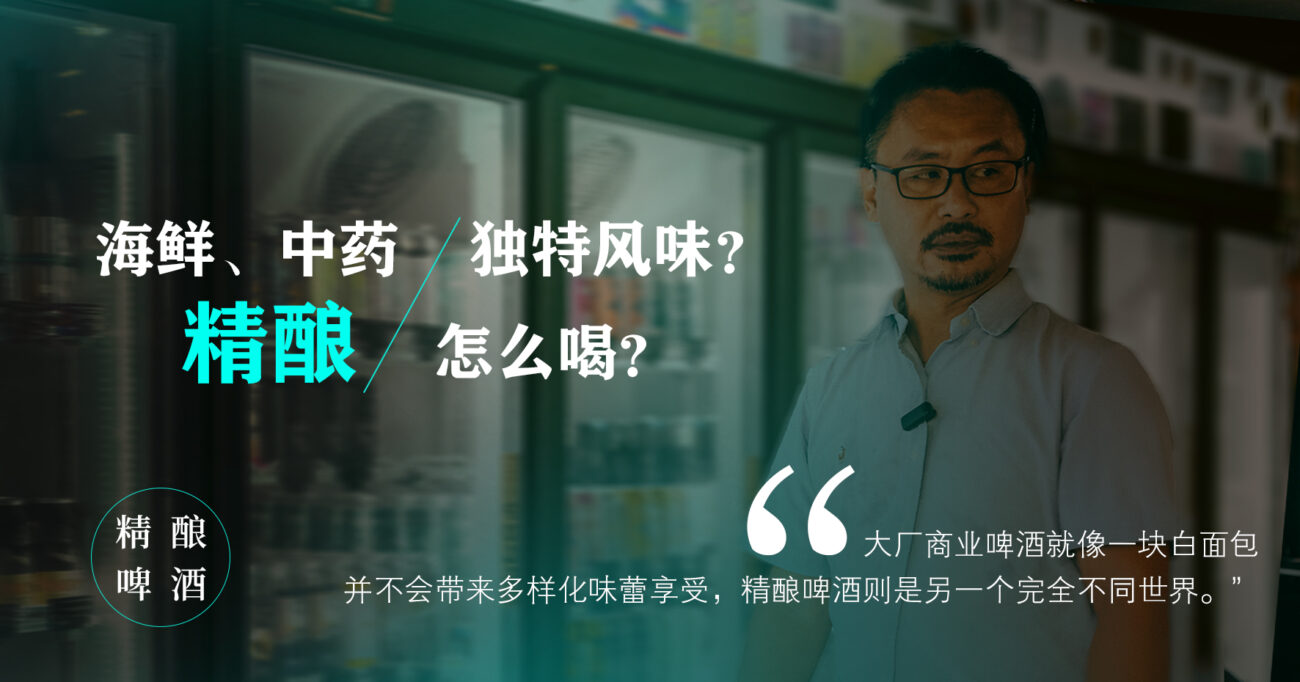1969年发生的“五一三事件”,至今仍然是国家禁忌的话题,过去纵使有马华文学书写“五一三”事件,但也大多是轻描淡写带过。马来西亚作家贺淑芳首部长篇小说《蜕》的出版,恰好落在“五一三”事件55年周年前几个月,是第一本直面“五一三”事件的马华文学小说。为了这部小说,曾经是一名记者的贺淑芳,走访了无数当年“五一三”事件的受害者与后人,这部小说从写成到出版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为它完成了什么,而是它撬开了什么,这也让《蜕》这部虚构的长篇小说,看起来,更像是一部口述历史。
“有一段时间,很多人觉得书写政治就会让文学消失不见。这是一种冷战时期的思维,但过度到现在,我觉得也并非绝对如此。如果书写政治文学就会消失,所以在文学创作中不应该书写政治,那是很奇怪的。”
“因为政治很大程度地影响我们的生活,而当我们被这么巨大的事情笼罩的时候,为何不允许我们抒发出来?我觉得文学应该要是可以书写政治的,因为我们意识到政治会如何笼罩我们的生活、制约我们的身体,我们更加需要这样的自由去书写。”
“要说这几年有什么改变,我想我们应该更深刻地体会到政治对人的控制,还有它对个体、性别、性还有各种事情所带来的影响,都是连在一起的。”
接受《访问》专访时,贺淑芳语速缓慢,娓娓道来她创作《蜕》之后的心情。
2023年,贺淑芳完成了她首部长篇小说《蜕》,这也是马华文学迄今第一本直面“五一三“事件的小说。比起过去贺淑芳在小说中的魔幻书写,《蜕》的故事相对平铺直叙,她书写主角们经历”五一三“事件前后的生活和变动,包括暴动本身,所有的冲突、躲藏、逃匿,都不断重现在每一个篇章中。
但它仍然是一部不容易阅读的小说。即使是对马来西亚历史、政治多少有认知的读者,也或许会在阅读过程中混淆身份,分不清现实和梦境,分不清今夕是何年。
可是,若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蜕》的故事也并没有想像中难以理解,因为“五一三”是绝大多数马来西亚人心知肚明的一组数字。
-1.jpg)
文学的“五一三”
1969年5月,马来西亚经历独立后第三次大选,向来十拿九稳的执政党联盟(如今国阵的前身)首次在大选中丢失三分之二议席的优势,而反对党则成功动摇好几个州政权,这成绩让反对党的成员和支持者们都感到大为雀跃。
他们于是上街游行大肆庆祝,却在路上与执政党支持者狭路相逢。双方爆发口角,反对党支持者态度嚣张,最终导致双方在街头爆发激烈冲突。
以上是”五一三“事件的官方说法,官方认为冲突的根源是族群之间存续已久的贫富差距问题,所以国会通过了《新经济政策》,强调土著的身份和地位,透过种族扶贫政策分配土著和非土著在经济和教育上的固打份额,奠定了马来西亚种族政治的地位。
”五一三“扭转了大马的政治结构,如此重要的事件却成为了国家敏感的禁语,只有坊间不断流传的众多说法。如果”五一三“不是一场偶然呢?学者普遍认为”五一三“其实是一场政治阴谋,目的不只是以民族情绪稳住执政党的权力,另一个目标是要把当时候担任首相的国父敦姑阿都拉曼拉下台。
种种说法孰真孰假,距离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我们仍然未有解答。在一切尚未明朗,扑索迷离之际正是小说家发挥力量的地方。

《蜕》讲述了主角陈桂英和她的家人、朋友,在1969年5月经历种族冲突前后的故事。故事的开端从马来西亚劳动人民的生活开始说起,华人移民为了填补劳动空缺而来到南洋,洗琉琅、割胶、摘黄梨⋯⋯
如小说描写的,“洗琉琅洗到屎忽向天,钱还是左手来右手去。”劳动人民的生活就是手停口停,生活永远不够,像是永无止尽地轮回在湿热的南洋,总在洗衣煮饭的母亲,还有那位缺席、抽烟又沉默寡言的父亲。
马来西亚人不多不少都能在这小城故事中找到自己家庭的原型,原本只是埋首劳作度日的小人物,却经历一场突如其来的暴动,强行扭转所有人的生活和命运。面对如此巨大的转折,他们却不得轻易抒发悲伤、愤怒,或是哀悼的情绪。
贺淑芳说,人是一种理性的动物,当我们生活在一个倾向于鼓励乐观、积极向上的集体社会中,对于无法诉说、解释的情绪,人们会选择逃避或排斥。更何况公权力不轻易允许大众提及,仅以“这是一场民间自发的暴乱”作为结案陈词,要大家尽快愈合伤口,别再提起。
“但若你不去看它,你就不会知道它抵达的是什么。”
这些被压抑的情绪仿佛辐射蔓延,已经渗透到好几代人的生命。如此庞大的悲伤、愤怒该怎么说起?”五一三“从不能谈到应该怎么谈,对贺淑芳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她从2017年开始构思,想要用魔幻书写来回应”五一三“,如同过去她在《迷宫毯子》、《湖面入境》以魔幻主义侧写各种大马政治和社会议题。故事原本是想说一群经历过”五一三“的幸存者或受难者家属,他们一同去旅行、散心,却遇上了一连串魔幻的事情。
可是后来贺淑芳发现,坐在房间内的写作无法让她满意,她一时担心这样会离”五一三“太远,一时又害怕离”五一三“太近。
“我还会顾虑作为一个小说家,我会不会因为太接近事件本身,反而导致我不太懂得用文学或者创作的语言去表达了。我竟然有这样的想法。”那段时间里贺淑芳的书写方式和动机不断来回变更,就在她犹豫该怎么进行的时候,2018年让她遇到了一个契机。
她有机会接触到马大社会科学学者傅向红带领的“五一三事件口述历史小组”,他们与贺淑芳分享了当时搜集到的田野调查和历史资料,而历史学者陈亚才也给贺淑芳推荐了几位愿意接受访问的“五一三”受难者家属。
贺淑芳说,她知道要完成这部小说,她必须要亲自去一趟。
进入个体记忆的入口
“我跟家属约访过几次,他们一开始都很愿意谈,讲了非常多当年的事情。我问的都是关于他们当时在现场的观察,像是当时候他们是怎么逃跑的?当时街上那么乱都是人,他们是怎么避开众人眼线的?沟渠那么小又是怎么藏得住人的?”
“他们在回答中提供了很多细节,还有很多重叠的地方,你会知道那是真实的,不是随便捏造的。那些细节非常深入,像是你只要去看当时候屋子的构造,你就知道原来以前的屋子建造得很靠近,所以可以从一间屋子逃到另一间屋子去都不会被发现。又或者是以前沟渠的大小,怎样才能够藏得住人。”
但随着采访次数增加,贺淑芳开始往更深入、更仔细的地方探问时,受访者们不约而同地退怯。他们开始回避,甚至是不再回覆。贺淑芳说她也不责怪受访者,毕竟这道伤口太难以处理,有很多未知、恐惧等等复杂的心情,让人不想一提再提。
再者,访问的过程中也让贺淑芳体会到人和记忆的不稳定。她说她曾经访问过两个受访者,俩人生活在同一个家庭,但对于“五一三”所发生的事情,俩人的说词有些微的出入,难以判断究竟谁的记忆更加准确。
“所有人的记忆你都没有办法完全保证,这是口述历史可能会遇到的困境。”官方的记忆、个体的记忆或许会有所限制,但小说没有,因为小说拥有虚构的力量。
“虚构本身是很有威力的,它可以去深入国家档案没有的资料,或者去处理一些被遮蔽、隐瞒的地方。而且小说家都是比较厚脸皮的,别人不提的,我们都会尝试介入。”贺淑芳笑着说。

采访贺淑芳那天,正值2023年916马来西亚日。热闹的苏丹街上人满为患,附近的音乐节快要开始了,在夕阳西下的时分,远远可以看见许多年轻男女在舞台附近席地而坐。
现代化的捷运一趟一趟载送人潮,送入这陈旧又进步的老社区中。捷运轰隆作响犹如时代巨轮的滚动,新的世代已然来临,半个世纪过去了,一切都在向前发展,而人们都站在在历史翻页之际。
但事实是我们能够轻易地翻过去吗?贺淑芳和我坐在鬼仔巷一间雅致的独立书店中,谈论超过五十年前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一道国殇。
过去马华文学从未有过一部小说像《蜕》一样直面“五一三”,贺淑芳解释,原因并不是因为过去的作家不想写、不敢写,而是没有资料,无法写。
“在这之前除了官方资料,还有柯嘉逊博士的《五一三事件解密》,再多的就没有了。国家档案局的照片也是少之又少,多数是一些救济中心大家互相帮忙、互相照顾的照片。又或者是暴动发生的一个月之后,国家恢复运作,学校开学了,学生排队去上课的照片。”
“几乎都是一些比较乐观的场面,所有负面的像是冲突、创伤、死亡等等恐怖的照片都不会出现。所以如果说要用完全纪实的角度去书写“五一三”小说,是非常困难的。当国家资料不足、口述资料也有限,这个时候虚构就必须要进来了。”
虽然后来家属们一一回避贺淑芳的约访,但前几次的访问下来,贺淑芳找到了她在房间内书写缺乏的元素,这是再深入的新闻报道、论文都无法勘查到的面向,那就是这些受访者们的“人性”。不只是在于他们说了什么,也在于他们没有说的到底是什么。
虚构的威力
小说以陈桂英,和母亲叶金英、阿姨叶阿清、还有桂英在暴动发生之后生下的女儿萝的个人生活贯穿了这道国殇带来的影响。从故事的开端,我们得知陈桂英在暴动中失去了年仅9岁的弟弟,阿姨叶阿清失去了同时是挚友又是情敌的同伴。
面对如此巨大的伤口她们缄默不语,尝试恢复如常生活,但生活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身为母亲叶金英与丈夫感情生变,无法面对幸存下来的家人。她放弃家庭,另寻伴侣过上新的生活;而叶阿清则深受内疚和妒忌所煎熬,扭转成为一个无法再爱的人。故事的主角陈桂英也因为这场暴动之后迷茫、无助,试图透过寻找爱欲解惑,却在早岁的感情中意外未婚先孕,诞生了女儿萝。
而这明明没有经历暴动的年轻生命,萝也深受“五一三”的余波荡漾影响,她深感欠缺,即便作为家庭中的独生女,她依然感到欠缺、不公,满腹忧愁、疑惑和妒忌充斥着她成长的岁月。
.jpg)
这些女性的爱欲和孤独看似与政治无关,却都在呈现“五一三”这巨大的历史事件如何影响个体与他人相处的关系。五一三暴动之后到底改变了什么?唯有将个人的情绪和感受分解到最幽微的单位,我们才能知道“五一三”的伤口究竟抵达了什么?
“小说本身就应该是从‘小’的地方去进入,这样它才会跟你平时看到的新闻、论文有不一样的东西。尤其是国家、个人都不愿意去提及的部分,像是性和欲望,或者是一些很幽微的情绪包括妒忌和恐惧,到底从何而来。”
虽说如此,贺淑芳在执行过程中还是有所顾虑,这样书写是否会不符合大众对“五一三”的期待?在这场种族冲突面前,描写个人的小情小爱,描写个体的情欲,会否矮化了“五一三”国殇的地位,这样的讨论是不是不政治正确的?
虚构的书写本来就伴随许多伦理问题,但贺淑芳认为正正是因为有了虚构的角色,还有他们所面对的种种人性与挣扎,才能为事件的讨论带来更复杂的面向。所以在国家档案局缺席的,都会在小说中一一浮现,无处藏匿。
“我在讲述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不只是在说华人这个主体,它们是女性、母亲、丈夫、男性、父亲,甚至是从我们眼前被藏起来的加害者。这些主体有各种的困惑是漆黑不明的,因为无法舒展所以我们无法理解它到底是什么。”
“小说拥有冲破这些框架的能力,唯有虚构你才能抵达这些个体的内在,去提出控诉或者是介入。”
“所以后来我觉得小说最大的伦理其实是‘你要竭尽所能去表达彻底‘,小说家需要竭尽所能表达深入。它唯一失职的地方就是你把事情写得太简单了,小说必须保留事物复杂的、所有的元素在其中,这个就是小说最大的伦理。”
这种复杂性可以赋予“五一三”更多面向的讨论,它不是官方的一种补充说法,而是为“五一三”事件提供更多的反思角度。
同一张脸,同一种恐惧
“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这里是受伤的国度。人们携带伤口,像蛾脸那样背着。除了自己,每个人都看得见。不要胡说八道别人背后的那张脸噢,母亲这么复述祖母说过的话 。那是很鲁莽很不礼貌的。我知道她为何那么说,因为他们背着的那张脸,我们也有。”——〈第一幕剧:蛾眼睛〉
小说中有这样一张相当玩味的“脸”,作为意象它不时出现,像擅自闯入万家灯火的飞蛾。小说是这样写的,“他们背着的那张脸,我们也有。”究竟是一张什么样的脸会同时存在于受害者和加害者身前与身后呢?
于是我问贺淑芳,这张脸到底是什么?她反问我说:“你觉得呢?”我深思后揣测,这张“脸”或许是一种复仇和愤怒,同时也是一种恐惧和脆弱,它原生自不同民族之间共有的国族焦虑。无论是马来人、华人或者印度人,我们都在担心自己的民族某天会被同化、消失。
她点点头,说:“我们其实都在害怕同样的事情。”
小说后半部分来到了贺淑芳最擅长的魔幻书写领域,若说虚构是为了填补史料的欠缺,容许作家探身到更深入的所在;而魔幻书写对贺淑芳来说,是一种可以跨越种族、语言的隔阂,抵达大同之地的方法。
“我曾经读过这样的一句话,’连结不同种族的文学语言一定是梦的语言。‘在马来西亚我们经常谈论要怎么连结、跨越不同族群的人,大家都觉得要用一个共同的语言,像是马来文、英文,但其实都不是。我相信大家通用的是梦的语言、诗的语言”
“透过魔幻、诗意、想像进入到更深层的意识去探索‘五一三’,这个资料有限又年代久远的复杂议题,你的心自然会打开,释放掉一些我们处理不了的复杂情感,才会写出跟社会主流不一样或者不赞同的说法。”

这些不一样的声音,在文学中到底可以为历史的“五一三”做一些什么呢?整个书写过程中,贺淑芳如此反问自己。
“我想文学的书写也许是可以带着历史的记忆,让一些沉默的声音甦醒过来。我觉得能够甦醒,就是重生,也唯有重生,我们才能思考我们有没有办法修复伤口。因为‘五一三’还没有结束,无论我们现在科技多进步,有多少人工智能可以取代人类,它仍旧像是一个恶梦那样缠绕着我们族群之间,产生对立、在政治上成为话题。”
于是我们蜕变
“总得解开过往,解除那使自己瘫痪的封印。一个人必须要拥有权力,走进那过往的记忆与情感,才能理解,何以如此。要去回忆,要捍卫感觉与记忆的权力。无论如何,都要获得这样的礼物,好让自己有一天,可以在时间里走回一圈。真相大白。” ——〈蜕皮〉
《蜕》这部小说在成为“蜕”以前,它的名字叫做《繁华盛开的森林》。“繁花”的意象固然比“蜕变”来得更美好。“蜕变”用以形容节肢动物、无脊椎动物变形的过程。它们脱胎换骨,过程漫长且充满不确定性。一旦不成功便会卡在旧壳中窒息而死。
“‘蜕’是一个充满可能的意象,你可能成功蜕变,也有可能会失败,一切充满未知。我们能做的就是好好地注视这个过程,关照它、保留所有的过程。”
昆虫蜕变的过程如此险峻,但它同时也是无法接受外力介入的。借由外力干扰的蜕变会对昆虫造成伤害,使它失去蜕变过程中所学习到的求生能力,最终也会无法长久的独立生存。
如同这道英殖民残留在马来西亚的种族问题,这些年它演化成为偏见、歧视、所伴随的焦虑恐惧,都必须由马来西亚人自己去经过、蜕变。我们已经知道禁止谈论无法修复,只会让它变得更模糊、不明。
如文章最初提到的,“五一三”是一组绝大多数马来西亚人都心知肚明的数字。可是当我们在说“绝大多数”的时候,这组对“五一三”事件有所认知的人,也正在一代复一代地减少。
它或许某天会成为一组极其普通的数字,再也没有过去它被禁谈时候所拥有的威力。但国家的伤口依然存在。
而这也许是《蜕》这部小说诞生的意义,它的写成解决了什么、撬开了什么、提问了什么都极其重要。因为我们看见一本马华文学能够如此直面“五一三”,往后也许能够期待更多的整理,透过文学、电影去提问或者谈论“五一三”,为这道陈旧的国殇,赋予一个全新世代的意义。
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