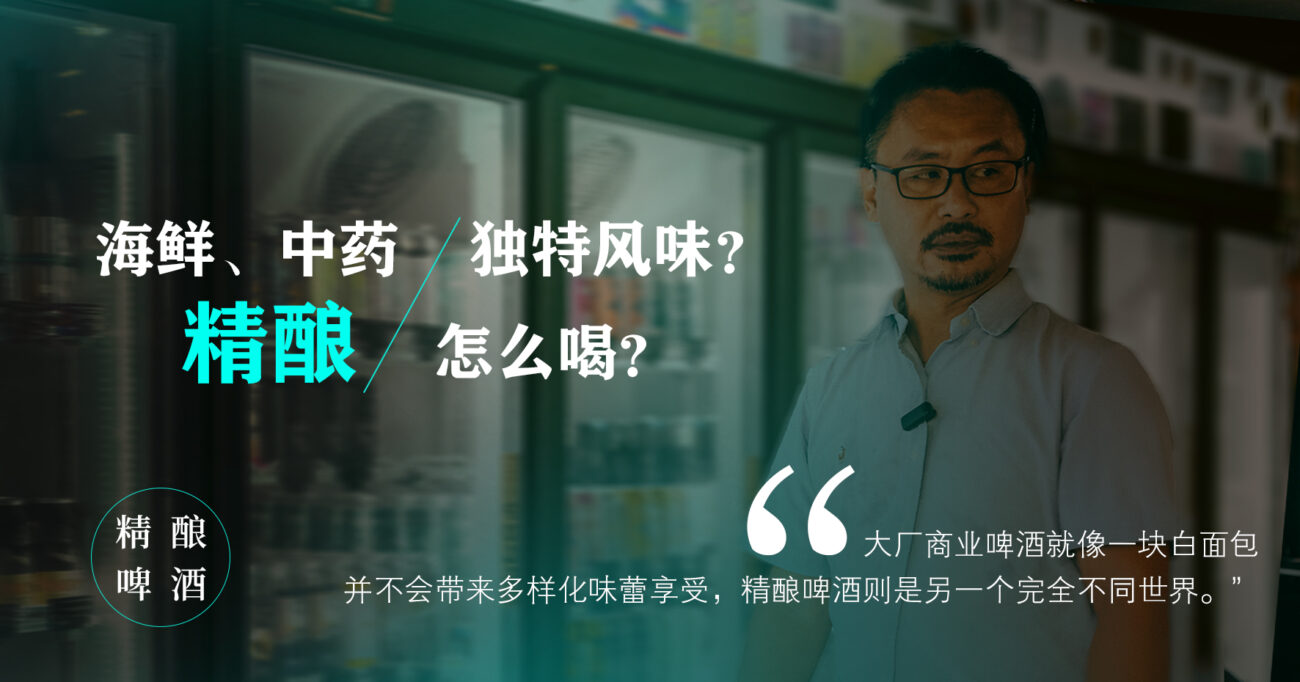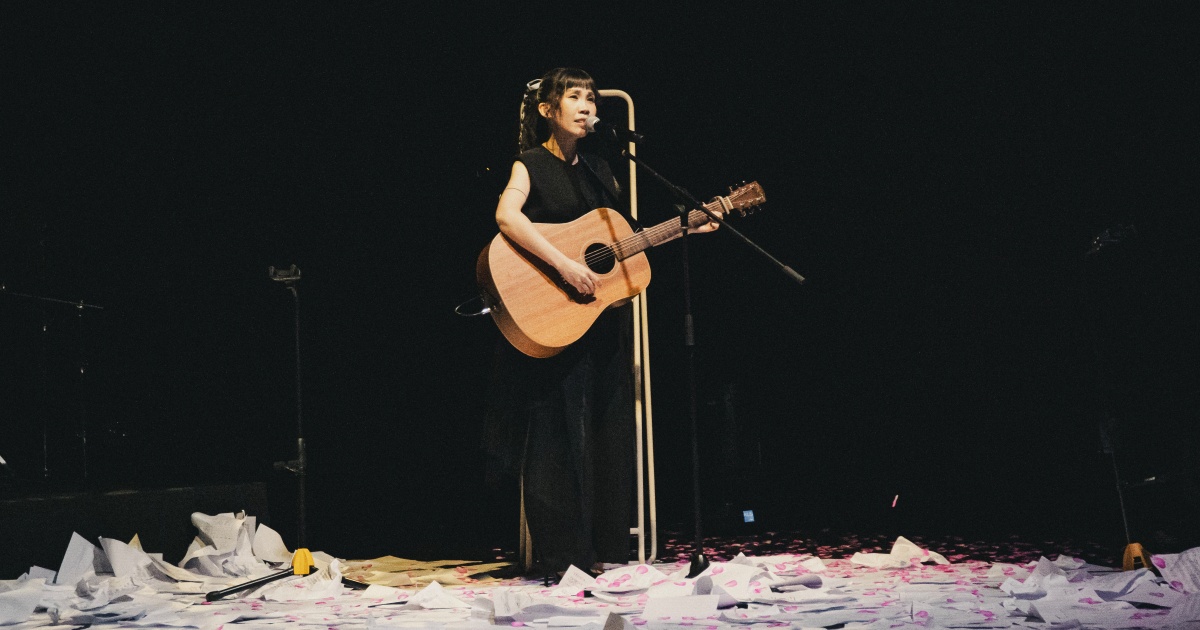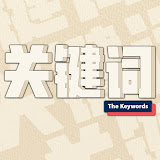马华作家贺淑芳的短篇小说集《湖面如镜》,透过书写9个不同女人的故事,剥开不同身份的女性在社会中面对性别、年龄、宗教与政治困境的形态。她写出女性的欲望与胆怯,写尽女性那些不宜诉说的部分。但她却从未抱着自己是女性作家的身份来写作。对她而言,书写女性,书写马来西亚,或者说书写本身只是作家与心灵最自然的链接。即便是虚构如小说,但最重要的是作品是否有真诚地呈现作家所看见的世界。
“我在罗兰巴特的书里面读到一句话,我觉得很妙。他说,当我们在使一件事情发生,或者当你要完成一件事情,你必须要有完成一件事情的欲望。如果你要写一本书,你就必须要有写一本书的欲望。有很多人可能一直想要写小说但一直没写完,我想是因为在众多的欲望中,完成小说这个欲望对他来说不是最重要的。”
大部分人认识马华作家贺淑芳,都是从她的〈别再提起〉开始的。2002年贺淑芳以短篇小说〈别再提起〉获得第25届中国时报文学奖而名声大噪。〈别再提起〉叙述了一个马来西亚华人在隐瞒家人的情况下,改为信奉伊斯兰教,最后在葬礼发生逝者的遗体被家属和宗教局争夺的故事。
贺淑芳透过书写马来西亚华人改教的故事,还原当时种族与政治氛围,更进一步地触及种族与宗教之间的差异。

1970年生于马来西亚吉打,贺淑芳先是在马来西亚理科大学修读物理应用系学士,尔后到台湾政治大学中文所修读硕士,2017年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获得中文系博士学位。在这段时间她还曾经担任过工程师、报馆专题记者与大学讲师等等工作,穿梭学术与职场的生活带给她的真实体验,都成为她创作小说的养分。
“我写〈别再提起〉的时候,还在南洋商报工作,我当时就进入报社的资料室翻阅资料。我就看到其实是60年代的时候谈论这些课题比较多。那跨越90年代到00年代,报纸就只能刊登,有新闻他们就刊登,大家会看到,但是再多的讨论就没有了。”
她把日常所见所闻全部都化作小说,以尖锐的笔触刺破人们装作若无其事的假象,即便是难堪的,应该说尤其是难堪的。
〈别再提起〉故事的最后,是家属与宗教局人员在葬礼上演抢尸体的闹剧,最终尸体内残余的排泄物因双方大力撕扯、摇晃而四处溅开来,顿时排泄物洒落满地,场面相当难看,也相当荒诞。
“如果我要书写一些负面的东西,我就不会想要安慰读者。因为假的安慰还是不要安慰比较好,不如还是如实地写。我觉得所有的一切都衔接政治,但是我写的是政治那边遗留下来的,可是这些剩余的东西正正对我们透显出,不能谈的政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虚构的威力
但再怎么如实地写,小说本就是虚构的文体。当真实的世界就在眼前,荒诞与戏剧程度还不输给虚构故事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还需要一个虚构的世界呢?
贺淑芳认为:“纪实告诉我什么是已经发生的。虚构则告诉我什么是可能会发生的。”
“我自己是一个写小说的人,我倾向于在写故事的时候,去看很多资料。然后去做田调、采访,把所有的东西组织起来。这些东西可以给我一个角度,我尽可能去获得一个多面的角度。”
透过这些多面的角度,她擅长虚构出一个世界来,透过铺陈、部署,让不同背景、文化层次的人或议题都能在小说里面相遇和互动,以此回应那些日日夜夜发生在我们身边,既熟悉却也无解的社会议题。“小说的故事是假的,可是它透露出真实的部分,可能还不好说。”

“小说的真实可能是另外一种,它的真实也许是以不直说的方式去体现出来,它是我们真实体验到的东西。因为这世界上有很多东西不是你可以直说的。小说就是穷尽可能,通过故事、设计情景,去把那些不能直说的,或者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话语被回避掉的,都表现出来。”
不管是无法在报章上讨论的课题,或是人们觉得难以启齿的欲望与性的课题,也或者是其他人们拘泥于“人情世故”不轻易开口说的,虚构都能让人们可以正视那些这些袒露或隐藏在日光之下的事情。
这就是虚构的威力,它使我们在看到事物底下更饱满的情感。这种有情感的介入不只是像是新闻中陈述的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会被导带去到另一个地方,一个感性的,充满感觉、感受的过程。
如果没有虚构的存在,贺淑芳觉得对小说家来说,将会是很大的困难。当所有人都只能受限书写自己眼前的生活,那么我们将无法刺探到事情更深层的,除却逻辑之外,更接近本质的地方。
虚构,它让我们去反思,我们可以从中经过一个漫长的书写,最后我们可以提出一个观点。
《湖面如镜》女作家书写女性的故事
经过了2012年的短篇小说集《迷宫毯子》,贺淑芳2014年出版了她第二部短篇小说集《湖面如镜》。借用女人的身影,描绘出9个短篇小说,讲述女性在面对性别、宗教、政治等等社会议题中的困境。

其中创作时间最早的是〈墙〉,讲述了妇女与丈夫感情疏离,她终日在厨房忙活,甚至在厨房睡觉,最后消失在外面的隔离墙中。以此讽刺“厨房是女人的天地”的观念,彰显出传统价值观中女性的边缘与孤独。
“她后来消失了,她老了,她会死去。但是这个结构还在,这个结构会一直凝视著我们,而我们也会凝视著这个结构。”
这部小说在2019年被译者Natascha Bruce翻译成英译本Lake Like Mirror,让海外书迷也能跨越语言障碍,一睹贺淑芳老师短篇小说的魅力。这部英译小说还入围了英国2020年度华威女性翻译奖(The Warwick Prize for Women in Translation),成为入围者中唯一的马华作家。

但贺淑芳说自己并没有特别意识到自己是女性作家的身份,“我其实也是在看到刘艺婉的书评之后,才意识到自己是女性作家(笑)。我没有特别去意识到这个身份,我只是很自然地写。”
“你很难会抱著‘我是女性作家’这个意图去写作,你就是很自然的。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女性的身体经验,这是我们最自然最熟悉的东西。比如女性上厕所的方式跟男生都不一样,女性对衣服的感觉,对事物的感觉,对自己内在心灵的感受都不一样。所以当女性写情欲小说,或者是当她写自己的身体的时候,会有很多细节是只有女人知道,女人能写。”
女性书写欲望:她成为自己所有感受的叙事者
然而在马华文学中,她觉得很多时候大家可以书写历史,也可以包容情欲,但是女性书写情欲的部分,却是常常缺席的。“大家可能觉得女性的欲望是不好意思谈的,觉得它不是一个东西,不是一个值得谈的东西,它是一个败笔。可是我不这么认为。”
“如果是书写情欲的话,它还有一个特殊的现象。比如说,男性如果书写情欲故事,女性就是对男性作家他探寻自我成长的一面镜子,男性在这个世界冒险或者探索自我成长的体现。但如果女性如果去描写自己的情欲,无论她的感受是什么,无论它是不堪的、是快乐的、是幸福的、是失落的、悲伤的,她都是自己感受的叙事者。
也就是说在当女性书写女性的故事的时候,她成为了自己全部感受的叙事者,成为自己叙述的主人。”这对女人,或对人来说都很重要,因为认识自己的欲望,是重新定义自己的方式之一。
“你可以去认识自己的欲望,‘哦原来我是想要这个东西’,如果你把这个欲望施展出来,有没有伤害到什么人吗?如果没有的话,那么你为什么要去压抑这个欲望呢?那你就要问自己,如果这么一个欲望没有伤害到人,但你却要去压抑它,这表示什么呢?这表示你正在顺应社会对你的期待。”

“文学中对欲望的探索,使得那书写特质必然是阴性的,只有接受阴性,书写才可能深刻,而不只流于表面。这过程就像是走进意识底层,或走到月亮背面的阴影,去摸索那些埋藏在阴影里的秘密。当然,某些感受被写出来之后,被语词照亮以后,定义重塑以后,一些暧昧不明的魔魅彷彿就消失了。”
“但在我们漫长的生命里,甚至历史长河里,还有很多处境、感受与经验是不可能说尽的。写了,说了,又会发现还有东西没有说完。就像宇宙一样,黑暗总是更浩瀚大于发光星体。因此,残余的,不曾说清楚的,又会再度回到艺术里,就像轮回一样,故事又会再继续。”
贺淑芳认为欲望是很深刻的事情,它体现的了人许多可以诉说与无法诉说的部分。“爱情如果你写得很干净,那就会变得像琼瑶的小说,很纯情,但是其实是摸不著边际的。你不写性的话,其实你写爱情是写不到氛围。因为围绕著性这个主题而来的就有包括到欲望,欲望被压抑的样子,欲望没有被压抑的样子,还有诠释其中的人性。”
“倘若一个人不接受自身的内在面,他或她是不可能成为一个创作者的,因为不够诚实。要去感觉情感、自己或别人的,而不只是硬梆梆的逻辑,文学跟读者的交流,需要从内在面打开,这几乎是先得有信任,才可能办到。”
她认为许多人对描写性这个主题感到胆怯,害怕它会让自己在作品中曝露很多,“可是如果不能写这样的事情,你创作来干嘛呢?你这样就是写作文而已吗?所以你要敢这么做,你才是在创作。”
何谓马华文学?
到底要怎么定义马华文学创作,是什么样的笔法、内容才是马华文学众说纷纭。马华文学究竟是马来西亚华文文学,还是马来西亚华人文学,而作品中“马华”的体现到底是以什么为标准?
类似这样的讨论历经不同的年代与价值观,充斥在学术与文学之间。有的会要求马华文学需要有马来西亚的体现,像是能代表马来西亚风味的食物,或是让读者能一秒代入马来西亚的风景,椰子树、油棕园。但在文本中书写这些就意味著它就是马华文学了吗?

换言之,也就是马华文学是否只是一盘盘的椰浆饭,七彩斑斓的蜡染(Batik)能象征的,只要不书写这些就不是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吗?
贺淑芳书写马来西亚跟书写女性,某种程度上有些相似之处。因为对她来说,写作都是从自己最自然的部分出发。“我觉得当人在马来西亚的时候,会有一种身体在场的感觉。你所见到的人,听到的声音,围绕你的氛围,邻居、街道统统都不一样。所有的滋味、食物、声音、语言气息,环绕你的生活。你在小说文字里浮现的意象,还有你会写出什么细节,这会跟当你人在国外的时候,是会有不同的。”
“所以当我离开马来西亚的时候,我会感觉到身体在场的感觉是被切断的。感觉很遥远很难受,你会感觉有一半的你还落在另一个地方。

我以前读到一个创作理论,它说当我们写作,我们都是在跟自己的心灵衔接。心灵就是我们最自然的东西,就跟我们的出生相连。我就是在这一团氛围中成长,所以如果我能够契合这股氛围,我就可以比较有信心,情感就可以奔放。这个就是触发你创作,最自然而然,最好的状态。
贺淑芳认为在国内和在国外的作者会用不一样的方式去体会马来西亚,所以对她来说,与其执著于文学作品中是否时时浮现各种“马来西亚性质”的符号,作家写作最重要的是要忠于自己的感情和感受;而读者在寻求的是这个作家的文本是能否接通自己的感受,契合他所认识的马来西亚。
一千个作家就有一千个马来西亚
因为有多少个人,就会有多少个版本的马来西亚。我们没有人可以说全然地理解自己的这片国土。有太多的生态,是我们无法理解的。
“譬如说,如果你做的考察时原住民的话,你就会呈现出跟另外一个写女性小贩故事的作家,不一样的马来西亚。这个时候我就看到,每个作者写出来的马来西亚,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马来西亚到底是什么,是回答不了的问题。那我觉得我们想要求的其实是,写作能不能够很真诚地展现作家看到的那个世界。当我们在谈作品有没有南洋的时候,我们其实在意的是作品有没有真诚地呈现你所书写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