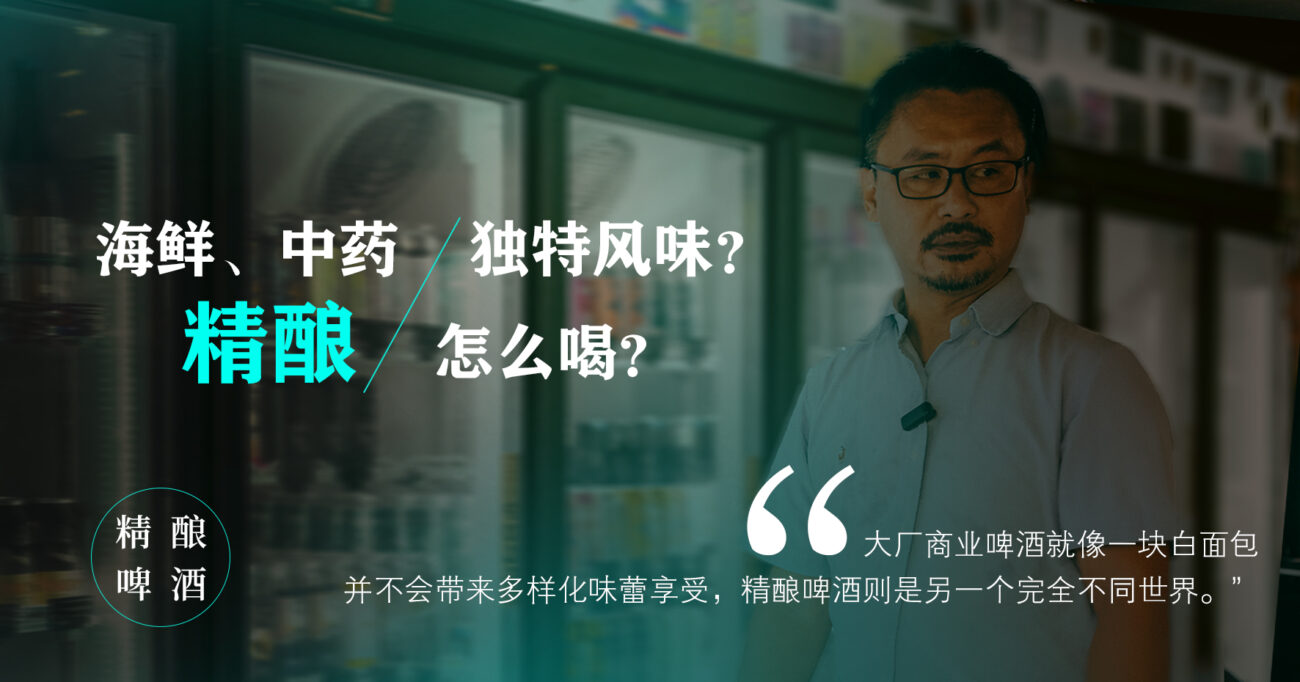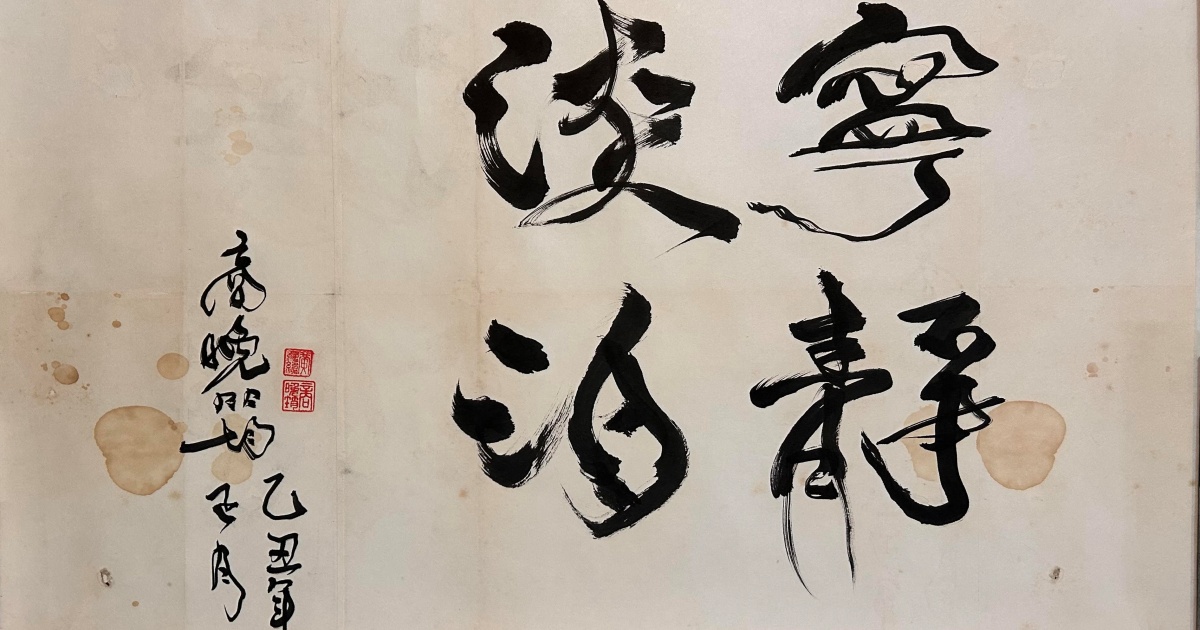生命礼仪师是家属处理丧事时的指明灯,他们站在生死之间,看生者也看死者。郭俊豪说,一般可从家属的身体语言观察得出往生者与家人的关系与融洽度,但相信这是经验累积而来的能力。从外行人的视角来看,这份职业有着满满的使命感,但他当初入行只不过是为了生计。一眨眼12年过去:“这一行,能做的人一做就能做很久……”,不是因为命硬,而是走着走着就会开始思考:还可以多做些什么?
好多年前的某一天,郭俊豪接到案子要南下接送遗体,车程逾四小时,他熟练地拎起黑色外套,坐上接体车后座,然后倒头就睡在担架上,一路补眠到目的地。有的人对此感到很忌讳:“那是死人睡的,怎么可以随便躺上去……”。
踏入殡葬业担任生命礼仪师12年的郭俊豪说:“我只想到接了遗体后还有很多事情要忙,最重要是补充睡眠,抵达目的地后才有精神及体力为往生者办理身后事。办一场圆满的丧礼才是至关紧要的事,哪里还想到忌讳。”
失去至亲的痛苦无论经历多少次都无法真正释怀,也许,让往生者死得有尊严,是家属在痛不欲生之际最大的安慰。
“有的地方因为空间问题,无法使用担架运送遗体,两个人帮忙抬又无法转身,我唯有直接把遗体抱上接体车。”

“其实不会有太多的杂念,这么想吧:如果今天是自己的亲人衣衫不整倒地不起,我该怎么做?当然是想办法让他有尊严地离开,总不能像拉猪肉那样把遗体拉出来。”
眼前滔滔不绝分享着职场见闻与体会的郭俊豪,很难让人联想到二十年前,他也不过是个正在面对父亲倒下、手足无措的儿子。至今回想起心里过不去的坎,他依然感慨:为什么当年没有这样一个“我”出现在年轻的自己身边?

大约22岁那年,有一个晚上妈妈非常慌张地敲他房门,他走出来发现父亲已经躺在地上。父亲如同大部分的男人一样,在家裸着上半身,只穿了一件短裤。当他试图想要进行急救时却不知从何下手,连移动父亲倒下的身体也显得吃力。
好不容易赶到邻近诊所,诊所医生只是问了句:“还有没有呼吸?”,知悉父亲似乎没有呼吸就连忙挥手说不收,让他把父亲送到医院。
他说那是自己人生中开车最快的一次,连红绿灯无暇顾及;也是他年少无知向父亲抛下狠话“不要再载你了!”之后,载父亲的最后一程。
内心无法释怀的痛 “做了很多,但就是过不去”
“以前刚考到驾照,正值叛逆期,父亲一坐上车就唠唠叨叨,我一时忍不住抛下狠话:我以后都不要载你了!不久后去了新加坡半工读,结果还真的从此没机会载他。”
说起父亲,郭俊豪几度泛起泪光,在餐馆暖黄灯光照耀下特别明显。他最大的遗憾是自懂事以来,从未跟父亲好好坐下谈心、饮早茶,或是吃一顿好吃的。直到自己有了孩子、升为人父,内心的遗憾亦未随着时间冲淡。
“我无法释怀,即使很久很久以后……那种感觉是即使做得再多,也过不去,我不懂怎么形容……”他哽咽,思索着怎么表达这份感受。
父亲受教育程度不高,但离开前还是留下了两句话给他们三兄弟——“做兄弟,有今生,没来世”和“世事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于心”。
“我后来才发现,父亲其实很爱我们,只是他不擅于表达,而我们当时也不会,有些事情就是过了你才学会。”
当年父亲离世,他经历了一段很糟糕的丧礼体验。交由传统寿板店处理的丧礼,因为母亲没有类似经验,主家没有主动权而被牵着鼻子走,最终结账时账单远超于原本谈妥的配套价格。
“将近三万令吉的丧礼费用,对当时我们的家庭经济状况而言是很大的负担。母亲原本只是一名家庭主妇,突然要扛起生计把我们三兄弟拉拔长大,加上这笔债务,可谓生活艰难,也受尽了委屈。”
这样的体验或多或少在他生命中留下印记,冥冥之中造就了今天的他对家属所抱持的同理心。这一点,可能他自己并未察觉。
丧礼的主角是棺材里的往生者 而非所谓“应该”的传统仪式
身为生命礼仪师,郭俊豪是家属在亲人被证实死亡时,除了医务人员之外第一个接触的人,并且从丧礼协商、遗体护理、入殓、报丧、奔丧、停灵、守灵、封棺、出殡、土葬或羽化,再到往后的祭拜仪式,全程给予陪伴和建议。
“根据以前的观念,丧礼必须跟着既有流程、固定模式进行,要跪要哭膜拜等等……可是对我而言,我的责任是打破所谓‘应该’的东西,丧礼应该怎么进行,选择权在家属身上,而我就扮演提供选项的角色。”
“很多人搞错了丧礼的主角,大家都被宗教牵着走,只要宗教师父或是领导人说要做什么,大家就不敢违背,因为自己不会,唯有照做。如果一个角色掌有绝对权力,当中就免不了涉及利益关系。”
他想表达的是,丧礼的主角是躺在棺材里的人,丧礼最重要的是家属想要为往生者做些什么:“不是让别人主导,而是你自己想为他做什么?你想留下些什么在自己心里面?”

对他而言,丧礼最关键的两个部分在于开始和结束。如今,丧礼不再局限于固定模式,不少礼仪师都会提供家属客制化选项,力求做到圆满。
“以前的丧礼结束前会由司仪代表家属宣读答谢词,但司仪照稿念的答谢词没有情感,我通常会鼓励家属站出来说出心里话,参与告别式。”
“对不起,我爱你”是他参与无数场告别式中最常听见的一句话。可能在人生最后一程,除了及时表达爱意与抱歉之情,其他一切已不再重要。
“入行那么久,若是遇到主家身边的三姑六婆指指点点怎么办?”他笑言:收服他们。
主家在办理丧事期间,身边难免会出现一些亲戚对于丧礼提出看法,甚至以传统观念提出质疑,他曾经认为这样的“三姑六婆”很难搞,但随着专业知识提升以及经验累积,这一切对他而言都不是难题。
“前提是礼仪师的专业知识扎实,可以解释传统观念的由来,不只是为了让事情处理起来更容易,而同时也在教育民众。”
“比方说,大家总有听过‘白头人不能送黑头人’,这是为什么呢?其实这是一个保护机制,假设丈夫突然离世,妻子的情绪一定几近崩溃、哭得撕心裂肺,因为担心身体无法承受出现状况,所以老前辈们才会设下这个机制。我不会用太强硬态度强迫家属应该做些什么,而是先告知他们这些说法背后的意义,再交由家属自行判断与决定。”
悲伤不一定是丧礼的主调 :“那一年,我见证了最浪漫的丧礼”
当年郭俊豪入行并不是因为什么崇高的理想或使命感,纯粹因为觉得生命礼仪师这份职业比较冷门,似乎可以获得不错的薪资,才跃跃一试。
“为什么入行?因为穷啊!”他不假思索马上回答,后来想想,再续称:“这一行,能做的人一做就能做很久……”
按照传统流程客制化丧礼,在出殡日前一晚进行告别式,让家属述说往生者生平追悼,是郭俊豪从一场最浪漫的丧礼中得到的启发。

那位往生者是一名太太,也是一名母亲,因肠癌病逝。早在十年前,她就发现患癌,身为丈夫的一家之主顿时失去方向,面对三名年幼的孩子也不知生活该如何继续。他向上天祈求十年:“我不贪心,请你再给我太太十年,让我们一起陪伴孩子长大。“而太太离世的那一年,正好十年。
丈夫在出殡日前一晚,主动要求郭俊豪设置麦克风,让他说几句话。他心平气和地述说与太太相识相知相爱的点滴、抗癌过程,当他说起自己向上天祈祷时,来奔丧的亲友全都感动落泪。没有华丽词藻,也没有卖弄悲情,只有平凡的感动。
在那一瞬间,他深知面对亲人离世,家属不应仅当丧礼中的旁观者,而是参与其中,这也是他提及的“生死两相安”,让逝者安息,活者善生。
如果丧礼可以提前规划,你希望人生最后一程怎么走?
你也可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