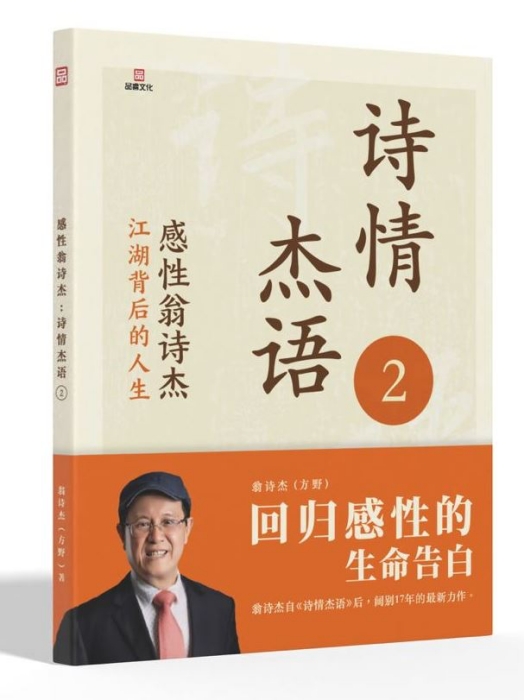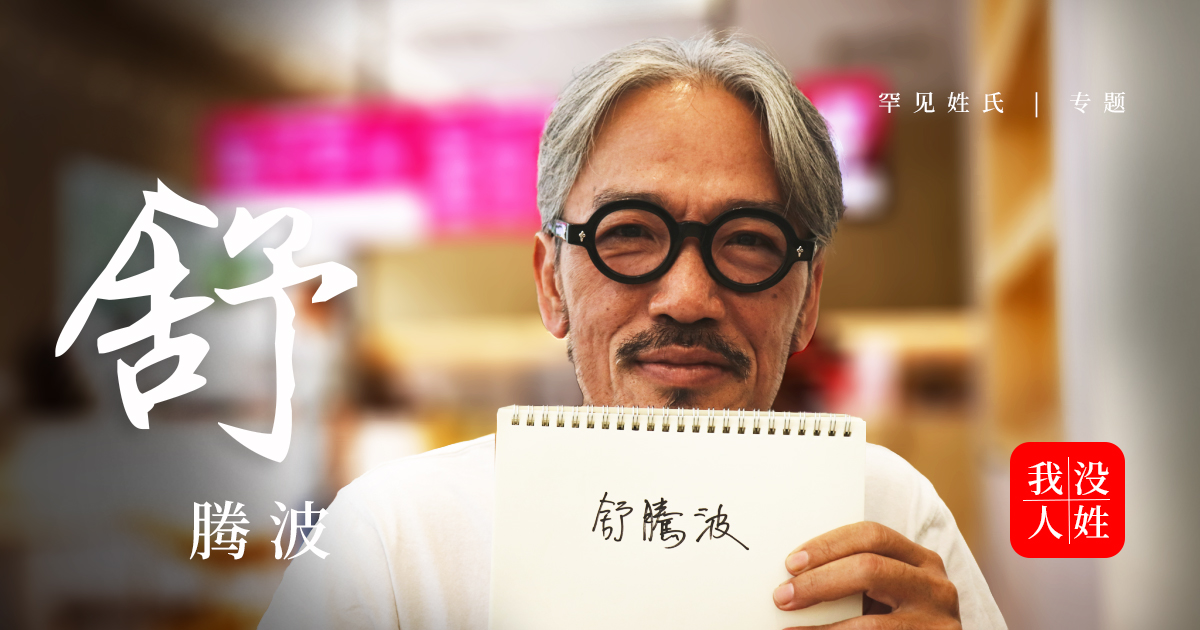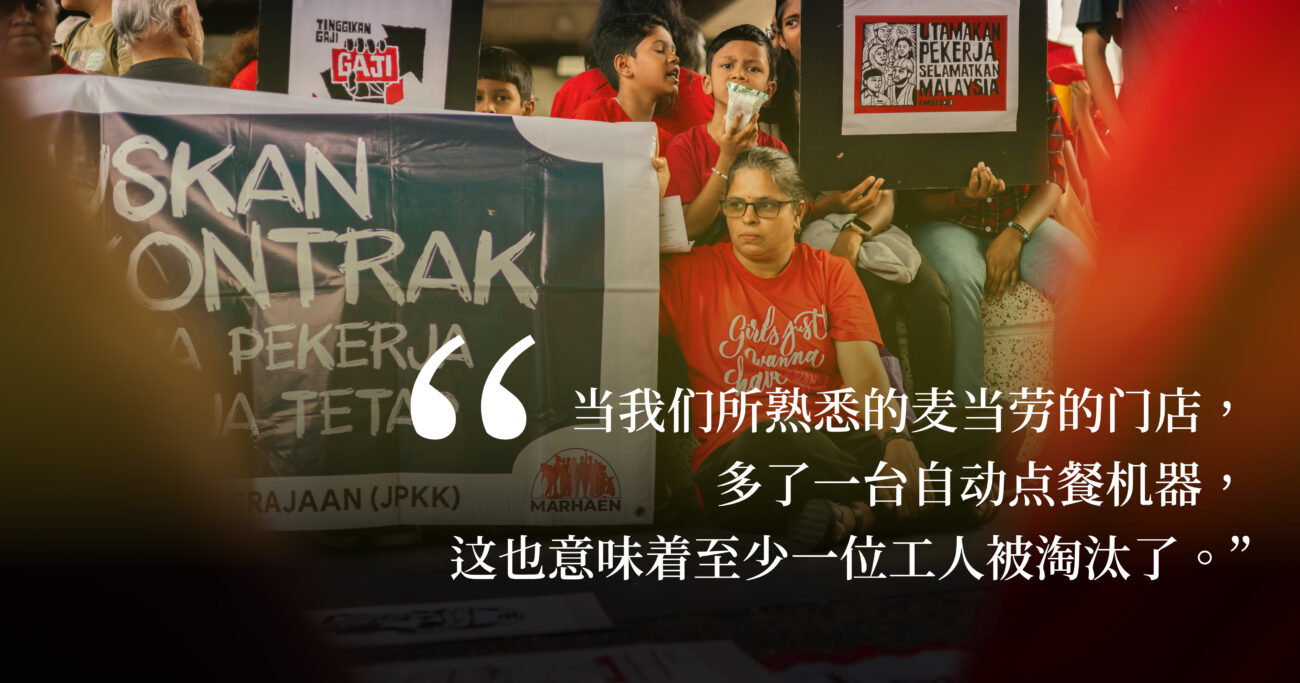印象中儿时的母亲是个闲不下来的家庭主妇。当时家在大杂院式的旧式店屋。我一家四口窝居在不到十平米的板隔斗室里,摆放了卧床,再添置了小书桌,就只能勉强容纳得了一台脚踏式的“针车”(缝纫机)了。可这却正好是母亲的命根子。

当时的斗室,即是我起居饮食暨活动天地的全部。大杂院里住了廿户人家,孩子多,品流杂,母亲怕我学坏,除了上学,就只能靠她手里挥舞的一根细长藤条,把我拴困在这小天地里。
当时,我只感到那台缝纫机的笨拙与厌烦。笨拙只因它粗重且占空间,厌烦则往往是它操作时停不下的噪音。母亲出身海南农村,节俭成性。她的唐式女装衫裤,概由自己买布剪裁缝纫,从不假手于人。
在我记忆匣子深处,伴随她脚踩“针车”踏板的,永远是那节奏性的机声夹杂着她絮絮叨叨的家乡往事。可孩提时代的我,走不进成年人的世界,更何况是那个陌生且遥远的祖籍地!

印象中,我始终记得母亲念念不忘的那句口头禅:“说我有命去,没命回,可真要给他们说中了!”我直感觉到她语气中的余愠未消,但又耿耿于怀自己回不了老家的无奈。
从她断断续续长年累月的叙述,她纵然嘴巴再硬,说自己早已断了落叶归根的念头,老家也没啥好惦念的,可三头两天跟父亲的谈话,她的话题还不是依旧绕着家乡转。先是怕乡下家里粮荒吃不饱(注:指1960至1962年间中国面临的三年自然灾害),几年后则又见怪家里的儿孙们音讯全无,生死未卜(注:指1966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凡有海外关系的中国家庭为怕有里通外国之嫌,备受牵连,而被迫选择与海外家属划清界线,断绝联系)。
儿时的我对这些话题向来一点也不感兴趣。我只留意母亲积存了许多花布碎屑,形状不一,杂锦缤纷。只见她一有闲暇,即埋头埋脑的把这些花布碎屑缝接起来。没多久,一件接一件的成品,都先后悄然地堆积起来了。先是长形的被子,后是圆方不一的座垫、足垫。说也奇怪,平日毫不起眼的布屑碎块,经她巧手处理,竟也缝制成三角形并成的花被子。我只知她管它叫“百家被”,说是给儿孙们做的。

回心一想,母亲的儿孙们都在海南。在那意识形态抬头的年代,她内心何尝不知自己回不了老家,可她口中的儿孙,在当时的现实里却离我们甚远。比我年长八岁的二哥还小,未到适婚年龄。只有我才是现行可能的受惠者。可我对这斑驳杂锦式的“百家被”不感兴趣。记忆中,与这相似的倒是我懂事后已弃之不用的襁褓。那想必也是出自母亲的手笔,由她以花布屑块缝制的。
而今,母亲已离世多年。这类襁褓老早已从我的记忆褪失,直至年前我在路上偶见外劳女佣以这杂锦式的襁褓背孩子上街。那惊鸿一瞥立马唤回了我尘封的记忆。
我想起不久前回到祖籍地省亲时,大哥不经意的说起母亲年轻时喜好女红的往事。那是没有缝纫机的年代,靠的就只有她手中的针线了。念及此,我才蓦然省悟,斗室里的那台缝纫机可是母亲的奢侈品!经她费心耗力缝制的被子、座垫,有哪件不是她乡愁的寄托?

我赶紧从她的故物堆里,好容易找到了当年她缝制的素色布屑座垫。这已历时半世纪之久的母亲遗作,果然还保存如新。然而,那张杂锦式的“百家被”却早已不知去向。我内心五味杂陈,一股浓郁的歉疚油然而生。
过后,我托人打听并订制了几张罕得一见的“百家被”,分赠几位外孙,权充替母亲了遂她可能也已淡忘的遗愿。可我心里明白:她不会淡忘的是她始终回不了原乡的毕生遗憾。
编按:本文摘自翁诗杰新作《诗情杰语2:感性翁诗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