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早晨的吉隆坡茨厂街上还徒留昨夜的热闹。清道夫低头打扫,街道还未苏醒。但早早就有一群民众穿戴好步行穿搭,到集合地点,等著参与这一次聆听老街的导览活动。而导览人正是大家熟悉的乡音采集工作者——张吉安。 有别于一般上带游客逛吉隆坡的导览活动,这一次的导览除了去看老建筑物之外,更重要的是去寻找那些曾经在这座老城生活过,却已经遗失了的声音。
每天睁开眼睛,你最先会听到什么声音?
会是闹钟的声音,还是亲爱的人在旁边叫醒你的声音?
窗外的鸟叫声,咖啡机烹调咖啡的声音,呼噜呼噜的流水声……这些鲜明的声音象征著生活的真实感。有声音,那是因为有人在这里生活。但如果有一天,这些人都走了的话,那么这些声音也会跟著消失。
吉隆坡老街,现在正在面临这样的命运。
周末早晨的吉隆坡茨厂街上还徒留昨夜的热闹。清道夫低头打扫,街道还未苏醒。但早早就有一群民众穿戴好步行穿搭,到集合地点,等著参与这一次聆听老街的导览活动。而导览人正是大家熟悉的采音人——张吉安。
有别于一般上带游客逛吉隆坡的导览活动,这一次的导览除了去看老建筑物之外,更重要的是去寻找那些曾经在这座老城生活过,却已经遗失了的声音。

最容易流失的文献——声音
在文献工作中,声音往往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般上大家都在做搜集文字、文物或者是照片的工作,但却鲜少注意到声音的保存。这一来是因为搜集声音的工作相对繁琐,必须找到本尊才能够采集到。再来声音流失的速度也非常快,一旦人走了,声音也就跟著完全消失了。
“所以过去我就是觉得趁着这个人还在,然后包括他留下来的录音,包括黑胶唱片、历史拷贝的录音,因为对我来说,那才是真正还原一个时代。因为照片你找到就是一张黑白照片,充其量你可能只能凭空想像,那个时候的人的样子长什么样。可是声音你听他说话的时候,你不仅仅是听到他的语言,你还听到他的语言习惯,还有他的用词习惯,他讲述的过程中他会讲出一些字的发音,跟我们现在的发音是不一样的。”
消失的妈姐 消失的“好姊妹”
导览行列中的人们走在逐渐苏醒的老城里,吉安带著大家走到了双英斋的小巷子内,给大家介绍了曾经在这里生活的妈姐。妈姐的生活很低调,下班之后她们会回到这个窄巷内,她们和自己的好姊妹住在一起,有著自己的七姐庙。


50到70年代间,多数妈姐都居住在这一带,后来妈姐纷纷凋零离世,人去楼空,房子也随后面临拆除,徒留下一片空地。如今,妈姐存在的证据就只剩下这一块空地了。

正是因为妈姐生活低调,有关她们的故事能记载到的并不多。大部分的她们早已经断了和中国那头家人的联系,所以她们在这里的生活就是和其他妈姐们相依为命。这样的生活方式被她们的下一代诠释为,妈姐们都有同性恋的倾向。
是的,妈姐也会有“下一代”。
吉安说,这些妈姐中有些比较有能力的会选择领养孩子,并且一般上都会选择领养女孩子。这是因为她们长期跟女人一起生活,并不习惯生活中会有男人的出现,甚至还有点抗拒男人。
“她们会尽量低调领养孩子,因为她们早已立誓终身梳起不嫁,避免惹人闲话。甚至坊间都会谣传她们部分是同志身份。不过,根据后来我所接触过有聘请妈姐的街坊提到的,绝不是我们想像中那样, 她们只是会选定姊妹同居,义结金兰,然后住在一起,而旁人则会诠释她们是同志,后来更添加她们彼此有越轨行为的说法。”
早期男尊女卑的社会,社会对妈姐存有一定的歧视,认为飘洋过海来到马来西亚打工的妈姐们终身不嫁,仿佛违背了社会女大当婚的传统 。而对她们来说,她们可能只知道自己勤奋工作赚钱寄回老家,并习惯跟姐妹相处,一起同甘共苦。也许无关爱与不爱,在那个年代,她们就是属于独立自主的女性社群。
后人认定她们是“同性恋” ,可是在妈姐的群体之中,也许比起我们认知中的爱情,更大程度是一种相濡以沫。毕竟飘洋过海来到陌生的国度,来到陌生的家庭中工作,难免有点不安。於是选择某个安全的对象,与她一起生活。
但无论实情是什么,我们都已经无从得知了。
我们不会知道妈姐们是知道自己的性取向之后,才选择成为妈姐的;亦或者是成为妈姐之后才感觉到自己只想要跟同性生活在一起。由于旧时代的观念,妈姐们绝口不提,这件事情已经随著妈姐的凋零以及那个时代一起远去了。
工业声响巨大如兽 淹没温柔老乡音
进步的城市伴随著的是工业化的规划,大同小异的大楼、车流涌入老城里,不只是加快了城里人们的步伐,轰隆作响的工业巨声也盖过了曾经聚居在这里的声音,那些生活中的声音正逐点逐点被淹没。
为了让大家能够感受到这座老城曾经的模样,吉安带领著大家,每经过一个老建筑就会打开一段老人家的录音,透过老人家的老乡音给大家叙述这里以前的面貌。
但无奈周边车水马龙的声音、建筑工地的声音如巨大的洪水,拍打在这温柔而孱弱的老乡音上。这似乎注定就是一场不公平的格斗,工业化的巨响无可避免地必定会战胜老乡音。于是任凭导览团队中的人们如何侧耳倾听,这些乡音只是零零落落地从吉安手中的扬声器传出来,能听得见的会走进人的心里,而没听见的都只是徒留在原地,成为了落单的、意义不明的声音,被这个进步的城市所摒弃。

“工业化的声音,它其实就是一个猛兽,它跟我们听到比较温柔的声音,这些声音很温柔、很纯净,但它敌不过工业化的声音,这些温柔的声音会消失。除了是环境造成它消失,也造就了这些声音无法跟现在的都市化生存在一起。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听的过程中,我们都会听到很多遗憾。
所以为什么我会用这种方式导览。我们现在看一栋建筑物,它虽然是活着的,但它里面的人已经消失了,它连带的文化已经消失了。你要如何让一栋建筑物可以发出声音,唯有通过语言,通过当年的录音,去让我们感受这栋建筑物。”
我们听不清楚一个完整的句子,只能听见一个旧时代的叹息。
这趟导览老城,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吉安一共给大家播放了十段录音。或长或短的老乡音从吉安的扬声器里一点一点地,筑成听者内心对这地方各自的想像。两个小时不长,十段录音也不多,但这却是吉安经历采音工作十年来的整理成果。
“像这样的导览其实很少人做,因为比较花时间,像今天你听到的可能短短两个小时的导览,听了十多段的声音,其实也不长。可是这十多段的声音是要用十多年来搜集的,可能你用两个小时可以听完。试问谁会用这种耐心去承担这种文化工程?今天大家只是付一个三十块,但其实这三十块根本不能就此换算我这十年来做的努力。”
做文化这件事情不是Touch n Go,不是举办几个活动提醒大家珍惜老街,也不是到一个地方去画几幅壁画,就可以让人们醒觉过来的。
“曾听过一个台湾古迹保存工作者形容我们这里的现象,他说要破坏一个社区的原生态,那么就到那个地方去画壁画吧!”
无论是在吉隆坡、马六甲、怡保还是槟城,这些地方的老社区或者古迹区都会发现有壁画的“打卡胜地”出现。为了吸引游客,而大肆改建、改造当地的建筑和生活方式,不只是没能保护老社区,更多的是在进行破坏。
吉安认为,近来许多文创活动在茨厂街开花,看似是让这座老城再次鲜活起来,有了年轻的人潮,但这对吉安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这些看起来翻新老社区,将新生命注入老社区的活动,其实就是不少业者将原居民和老行业赶走,将外来的元素东拼西凑,将老社区改造成“主题乐园”,对于守护历史老城就是一种破坏。因为这些文创跟老社区本身缺乏联系,宛如殖民者与原住民之间的对立,殖民的新流行文化无论将在地发展得多么合适人们居住,对原本就生活在这个社区的老人家而言,始终是不适的。
消失的老城 消失的老人
“说得比较难听一点,这些老社区或者是居住在这里的老街坊基本上其实已经尾声了,意思就是他们大部分都走了,剩下的可能是已经很老了,甚至可能已经记忆力衰退,说不出东西来了。所以基本上这几年我都已经慢慢停下来,原因是因为很难找到原声了,反而是将过去十年来不断采集回来的声音文献。我现在就是一个一个去修复,一个个去把它记录下来变成文字,现在完全就是整理的工作。”
吉安从2005年开始从事采音工作,历时15年的时间,他也逐渐意识到采音工作真的来到了尾声。他虽然早就意识到这结局的到来,但面对采集的对象,这些在老社区生活的老人家们一个一个离去、消失,还是让他感到相当惆怅。
我们能看到经常有老人聚集在一起喝茶聊天的茶室被取代了,大家喜欢围在附近看戏、听“古仔”(故事)的中华戏院被改建成停车场了,原本在这里生活的老人家都跟随孩子到其他地方去生活去了……
老城和老人不知道是谁先开始消失的,老社区依然是人们日常的中心,但已然变成中途转车站的地方,上班的地方,不再是生活的地方。

“我觉得以前的人比较有共享的概念,因为我们知道以前资源不多,以前的人是群居社会,现在的人连邻居是谁都不知道。所以我觉得以前的群居社会造就了 我们很多东西是共享的,共享资源、共享娱乐,在那个时候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好。反而到现在已经没有了群居社会的概念之后,人跟人之间的疏离越来越大了。”
进步的科技与社会让我们常常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时间一长,现代人甚至都有点享受这样的孤独感。这仿佛是进步化社会的代价,人们不再需要公共空间,对共享资源也不再有概念,吉安甚至嘲笑说:“我们现在的公共空间充其量就是商场吧。”
老城和老人两者都是这急速进化的社会中的淘汰者,它们都需要彼此才能继续生存,一旦失去了对方,这关系就会开始坍塌。城里最原始的老乡音逐渐被索然无味的工业巨响盖过,老人们聚集的茶室不在了,老人们也不在了。没有了老人的老城只会沦为一栋栋无语的建筑物,外人经过看了,只看得见风化与沧桑,却不会知道建筑物曾经有过的人,有过的故事。
同样地,失去了老城的老人,也同样,会支撑不下去。
“其实很多时候,这些社区的老人,他们还住在社区的话,他们不舍得离开这个地方,是因为他们年华老去,他们也看到社区的凋零。然后你会发觉到很多这些老人家,茨厂街很多老人家,白天会在这里溜达,我们遇到蛮多。当然逐年比较少了,因为有些都已经去世了,近十年左右是蛮多的,因为他们搬走了,他们搬去跟孩子住。”
离开了老社区的老人家们还是会在白天回到这里。也许是为了挽住旧时代的尾巴,希望透过回到了这座老城,也就能回到那段他们视之为珍贵的岁月中,在里面和熟悉的人、熟悉的城相处,谁也没有离开过谁。这些挽留光阴的方式都只是一场容易被拆穿的镜花水月,但老人们愿意去相信,他们想要继续留在那段岁月中。
但工业化的巨响步步逼近,敲碎这个疲弱的梦,一条条老巷子被翻新,老店家被取代,让这些老人家失去他们原有的生活空间,那些与老街坊一起聊天的共享空间逐渐被取代,这让他们感到相当不适,似乎已经失去了容身之所,这是时代进步对老人家发出最直接也最残忍的呼喊,“你们已经不被时代需要了。”
失去话语权的老人家,失去了他们最原始的容身之处,只能够躲在远远地,也学起了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开始接触手机、接触电视,没有人跟他们说话,尤其谈谈那些他们还记得的往事,他们也很快会患上老人病,不久就会与世长辞。
流逝是时间给我们最无法反抗的宿命。但透过保存,透过记载,我们能在这强大的宿命中找寻一丝缝隙,让这些有温度的声音与故事,能有个归宿,而不是时代巨轮底下被碾压的孤魂。
而有人记得你,就是最好的保存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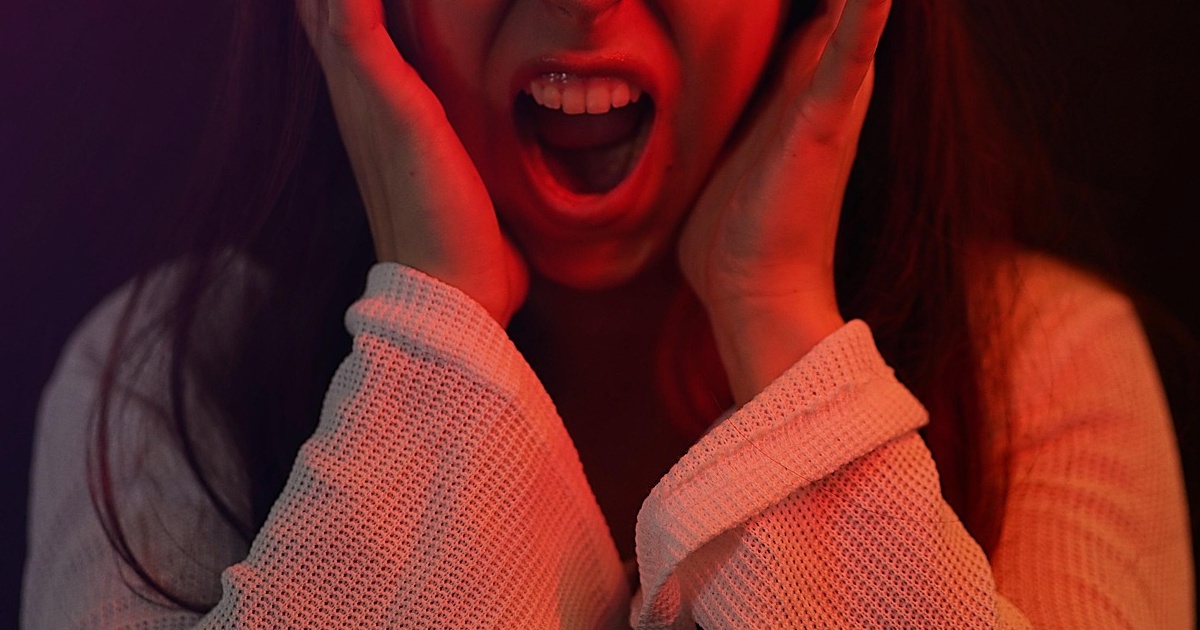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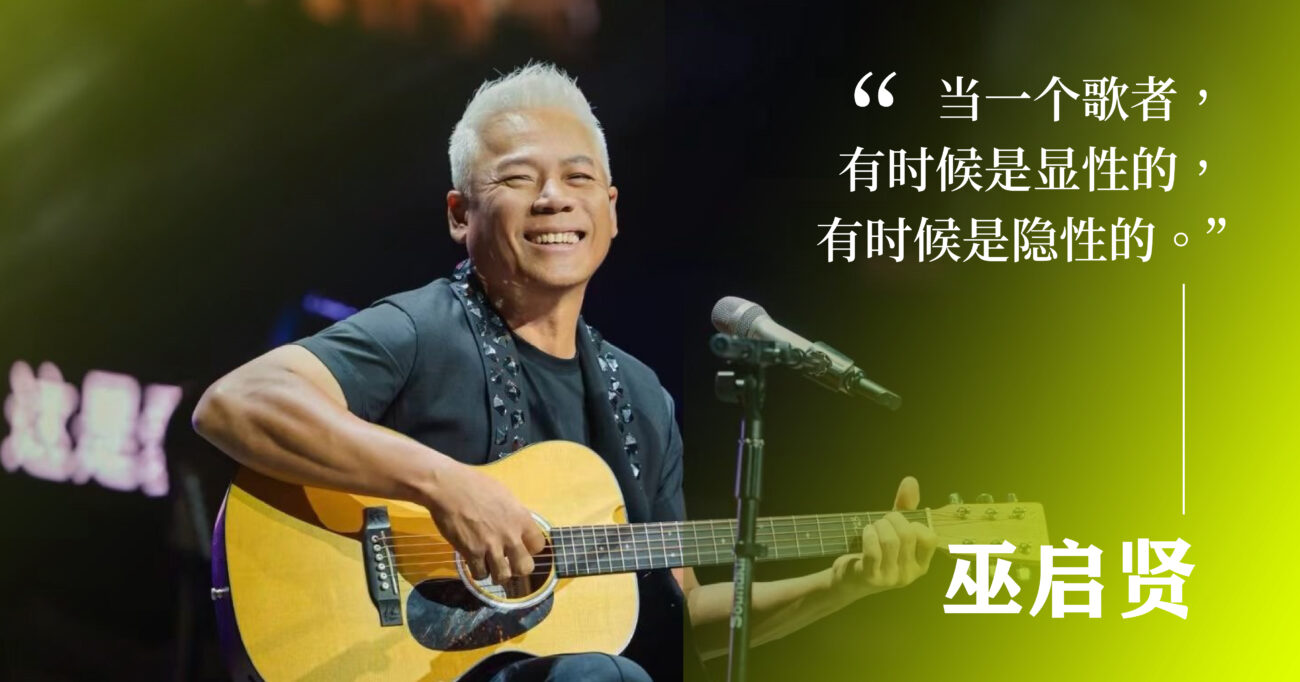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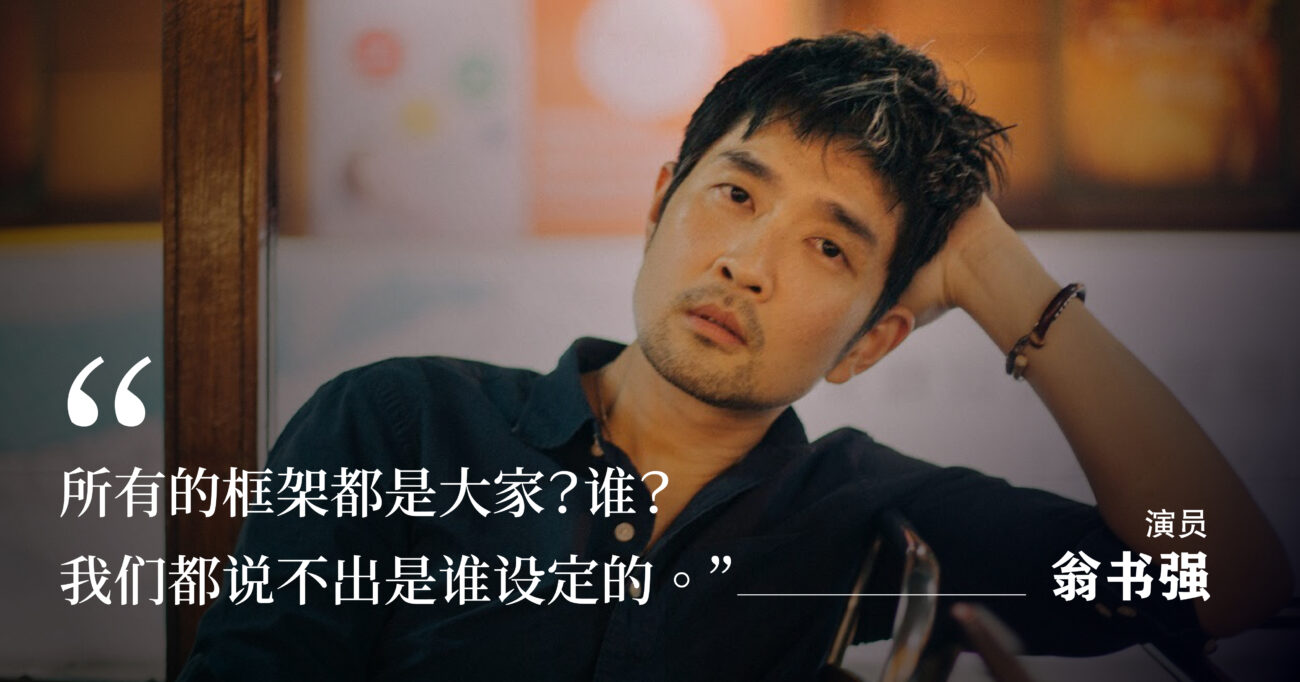






































內容紮實,有溫度,很喜歡你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