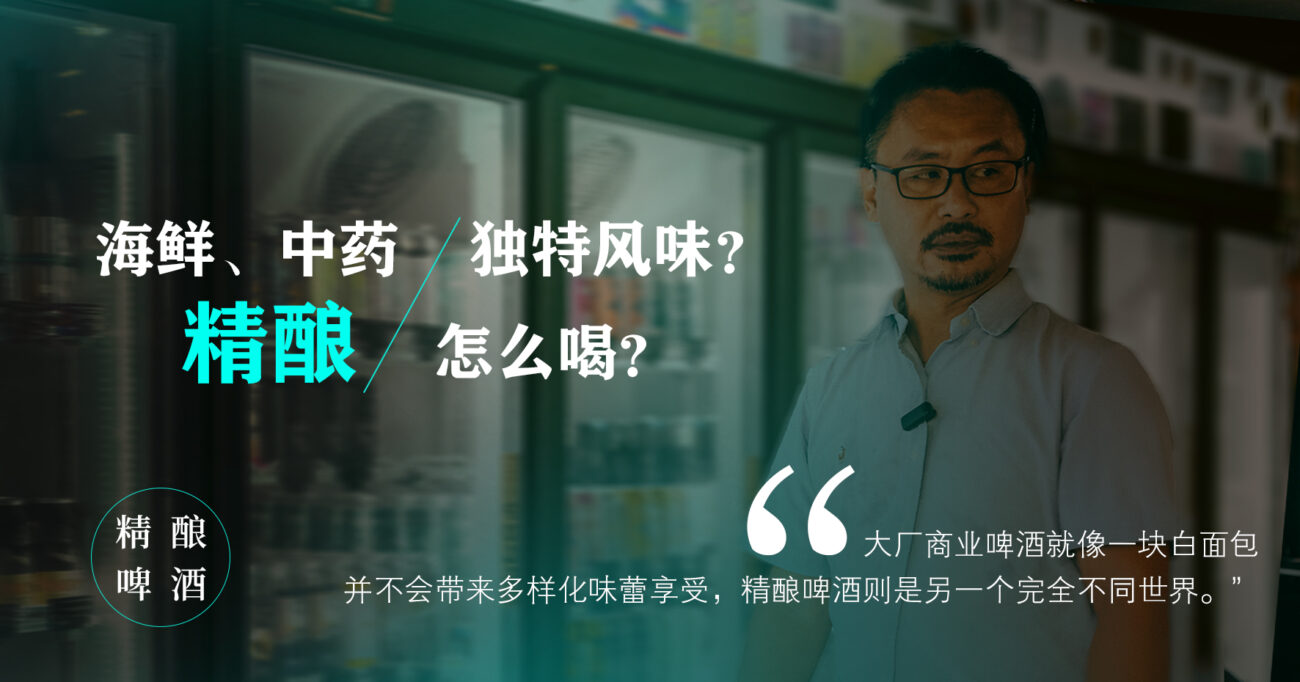当医生决定将新冠肺炎病患转到加护病房,就表示病患已属第四至五级肺炎,需要加强治疗及使用呼吸辅助器。每一通来自加护病房的视讯通话,也许只剩下微弱的呼吸声,每一次都可能是最后一次,家属每天皆面对接或不接电话的两难。踏入加护病房再也出不来的家人,真的就这样消失了吗?在疫情之下,接受死亡真相的难度,比一般常态下更难。也许悲伤会随着时间消化,生活终究会好起来,但那个消失于加护病房的家人从此只能活在心里,永远不会再出现于生活中。
根据马来西亚卫生部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6月9日,大马新冠肺炎累积死亡病例共3611宗,这意味着逾三千户家庭失去了至亲。本地电台DJ丘淑霖的父亲也在五月杪不敌冠病逝世。
“我们的生活很简单。早上,爸爸载我去上班;下班回来,我们一起吃午餐,聊聊当天发生的事;周末,陪爸爸妈妈到公园运动。天天如此,日日重复规律又平凡的生活。”
直到父亲逝世后,她才发现,其实这些再平凡不过的普通日子,让她一直感到很踏实。

我们是相当传统的华人家庭,不会把爱的语言挂在嘴边,从来都没有,甚至是爸爸躺在加护病房,医生帮忙连接视讯通话时,我都没怎么跟他表达。我们之间的爱,即便到了这样的时刻,依然是别扭的。可是,我的心里是踏实的,因为在他生前,我一直都陪着他。
她说家里并没有大肆庆祝节日的习惯,自己更是不太喜欢过节,总是希望节日那一天赶快过去。
“节日对我来说总是别扭,好像一定要有什么表示才对。很多人都在倡导生活要有仪式感,我到这一刻才知道,原来只要家人都在,平凡日子里天天都充满仪式感。”
自律执行严谨标准作业程序,保护自己免受感染
2021年4月22日,丘淑霖家中出现第一位新冠确诊患者。他们一家五口同住一屋檐下,一名家庭成员因为到学校上课染疫,随后其他家庭成员相继确诊,除了她以外。
“当家里出现第一位确诊患者时,我就针对每一名家庭成员日常生活所需列出一套非常仔细的标准作业程序,包括必需品、洗手间、使用空间分配。不过,也许是在那之前就已经开始传染,也可能是在这过程中还有一些疏忽的地方,所以就没办法避免。毕竟住在一块儿,风险是非常高的。即使我们拥有各自的空间,也无法掌握病毒除了在确诊者身上,还残留在什么物体上。”
在这段期间,她也收到不少网民私信询问,怎么在与确诊者同住的情况下,避免自己被感染。
“我很宅,除了上班时间之外,其他时间都在家。我猜想,自己其实并不是没有接触到病毒,而是我把病毒‘洗’掉了,或者执行严谨的标准作业程序避开了病毒。”
单单是洗手这回事,她甚至把手给洗破。她分享道,有一天在洗手时,好奇手上怎么有污垢,连搓两次“污垢”还在,直到抹干手掌才发现那不是污垢,而是手掌被搓得破皮了。即使是在家里,只要离开卧室,她即把口罩戴上,戴了之后不随意摘下,更不用手摸东摸西。
“我也当作戴过的口罩上会有病毒,所以不会用手托腮、触碰脸部等。因为家人相继确诊,我总共隔离了26天。重返工作岗位复工时,我还戴上手套,并且学着加护病房医护人员的做法,隔着手套也用搓手液洗手。”
下班回家之后,她有一套耗时30至45分钟的消毒流程,逐一物件消毒才进屋。有的人会认为:有必要吗?至于吗?
“在疫情严峻的当下,而我又跟数位确诊患者住在一起,我觉得,是有需要的。”
“是一则则慰问讯息在提醒我:爸爸真的走了……”
5月30日,也是报刊专栏作者的丘淑霖如往常一样,在个人脸书专页分享专栏文章,帖文随即引起强烈回应,这是她始料未及的事。她在文中写下父亲被送进加护病房之后所经历的心情写照,文末标注父亲在文章刊登时已经离世。
“爸爸过世的那天,我一滴眼泪也没有流。直到分享专栏文章、新闻刊登,排山倒海的慰问讯息涌进来,那个当下,我才从大家的慰问中不断地被提醒:爸爸走了,原来真的发生大件事,人死了……”

那一晚临睡前,她才终于潸然泪下。
当家中出现确诊患者,间中父亲被送进加护病房,自己又处于隔离期,要处理的家务事实在太多。
“那段期间,很多事情都是我在处理,包括四位确诊患者确诊之后需进行的报备程序、联系相关单位、跟医院接洽等等,我试过一天下来打了约50通电话。一整天下来只做一件事:打电话和接电话。我想,我冷静的原因有两个。一,我必须稳定家庭情绪与氛围;二,太多事情要处理,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让我停留在焦虑或悲伤。”
父亲躺在加护病房的日子,医院每天都会打一通电话向家属汇报病患的健康状况。对于这通电话,丘淑霖心里充满矛盾纠结。
“我每一天醒来就为了等这通电话,因为如果错过了,再回拨时很可能已联系不上。所以,我连上厕所、洗澡、睡觉,手机都必须贴身。但当这通电话响起时,我又害怕电话的另一头传来坏消息。”
来自加护病房的电话,就这样在一次次的犹豫、挣扎之后,被她鼓起勇气接起又放下。
不知道第几天,他们再次视讯。在加护病房多时的父亲很用力地表达,用微弱颤抖的声音说:“我……要……回……家……”。终于,他在进院接受治疗的21天后,获允出院回家。只不过,已瘦成另一个模样的父亲让她越发心疼。
“我甚至觉得他不像一个活着的人,长时间睡觉、进食困难、喝水会咽到,也没有力气说话。回家一天后,爸爸又开始发烧不退、背部刺痛、全身无力,我们只好再送他到医院。”

这一次,父亲就再也没有从加护病房走出来了。
“如果他活着,我希望他健康快乐,如果不是这样,我觉得上天已做了最好的安排。”
无法见面的死亡“不真实”,丧亲者的悲哀以倍数式增长
临终关怀工作者冯以量受访时这么形容:“只要家中出现一名新冠重症患者被送入加护病房,基本上就是一颗计时炸弹。”
他指出,当事情发生时,每一名家属都不会处在同一频率上,因此会产生混乱。加护病房里的这一颗计时炸弹会不会爆?何时爆?无人能预测。家属最煎熬的阶段,就是等待的过程。
在过往的临终关怀工作里,冯以量可以依据临终病人的个别情况,献出好多的建议和点子,让患者和家人达成善别,而这一次,这些方法全都使不上。

“这场疫情让我们最无助的是,连去见对方一面都没有办法。”
他打个比方说,一般常态下,人要么是患病逝世,要么就是意外丧生。
“假设一名家人是癌症三年后去世,其实在他罹患癌症开始,我就已经预知到家人随时离开,至少有三年时间去接受家人的死亡;另一个状况,突然接获电话说家人车祸去世,这非常突然,可是我依然还可以冲到太平间去看死者遗体、认领遗体、确认眼前的人是自己的挚爱,甚至可以要求在入殓时亲自帮死者清理身体。即便是在丧礼上,我还可以绕棺木、接受亲友慰问、请法师送上祝福……全部都可以参与。即便是突如其来的,家属还能够参与。”
这一次难在没有时间做心理准备,也没有参与最后送行的机会,难度加剧。这个悲伤不是一加一等于二,而是以倍数式增加,每一件无法完成的事都会成为遗憾。
他感概地表示:“我们这些普通人,不要以一般常态情况来叫家属放下,因为那真的很难,单单接受死亡真实感就已经充满挑战了。”
“如果没有打算在这个时候说再见,那就不要说再见。”
他说道,如果丧亲者对亡者已死这件事没有真实感,他不会引导丧亲者说再见这件事。毕竟,他们双方没有说要在今年里说再见。因此,他会鼓励丧亲者多想办法连结对方、思念对方。譬如:打电话给亡者,把语音留在他的手机里。或者,每次煮饭,都留一碗饭给他,放一双筷子在桌上。
“唯有继续连接,我们才能圆满那些不圆满的死亡事件。”

也许在陪伴冠病丧亲者的路上,他无法做太多实践性的事情,但他可以当丧亲者的“内心导游”,让家属大概知道接下来会发生的状况,至少让丧亲者在面对无助时不孤单。
世间生死是自然定律,但新冠肺炎蔓延的日子,节节上升的死亡病例像极了“集体死亡行为”。或许,一年多下来每天看着新闻里播报的各种数据,你已经感到麻木、无感。但请记得,数据背后是这场瘟疫被牺牲的人,是一张张家庭照中所缺失的一角。若干年后,这些人都将成为这个时代的经典故事。
你也可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