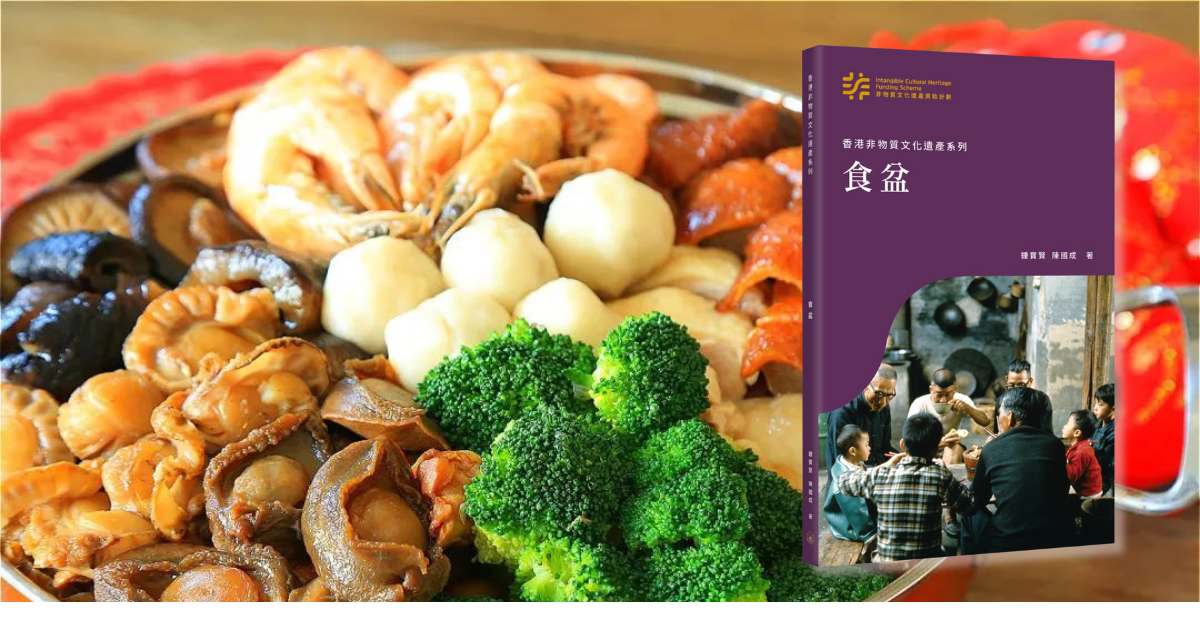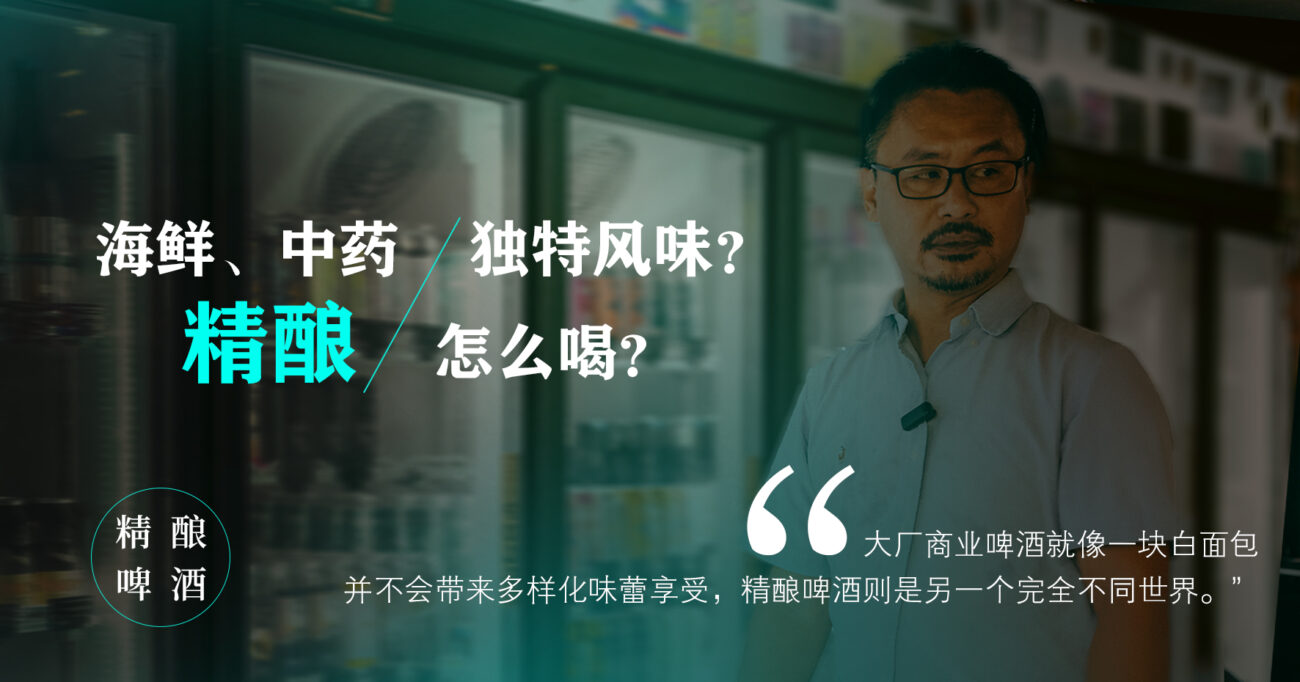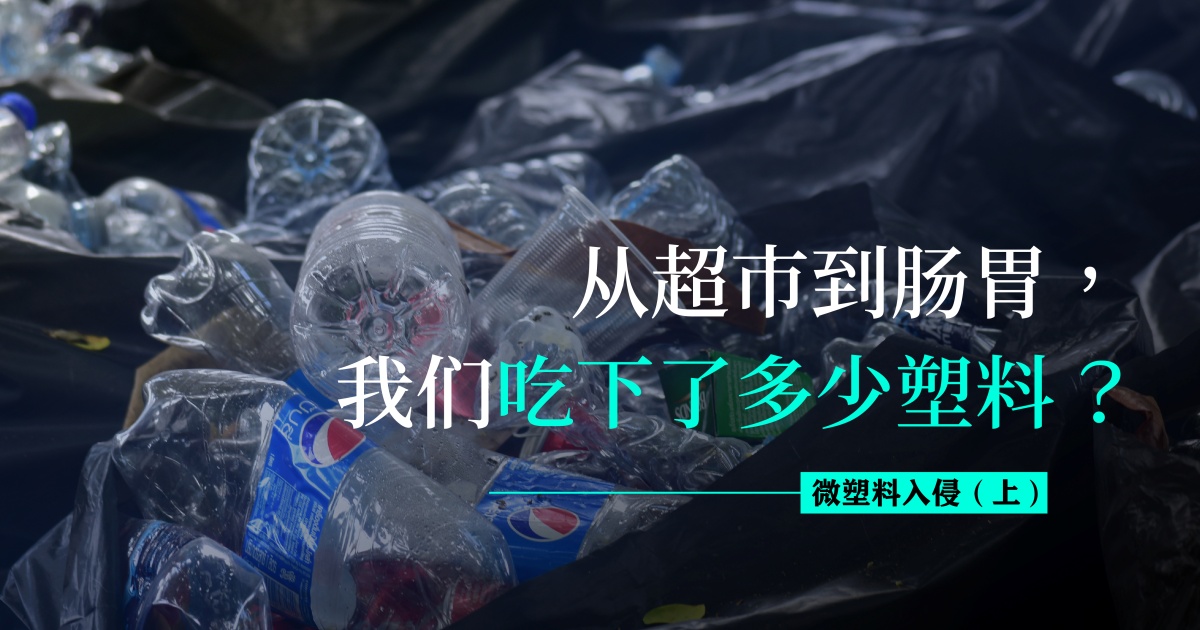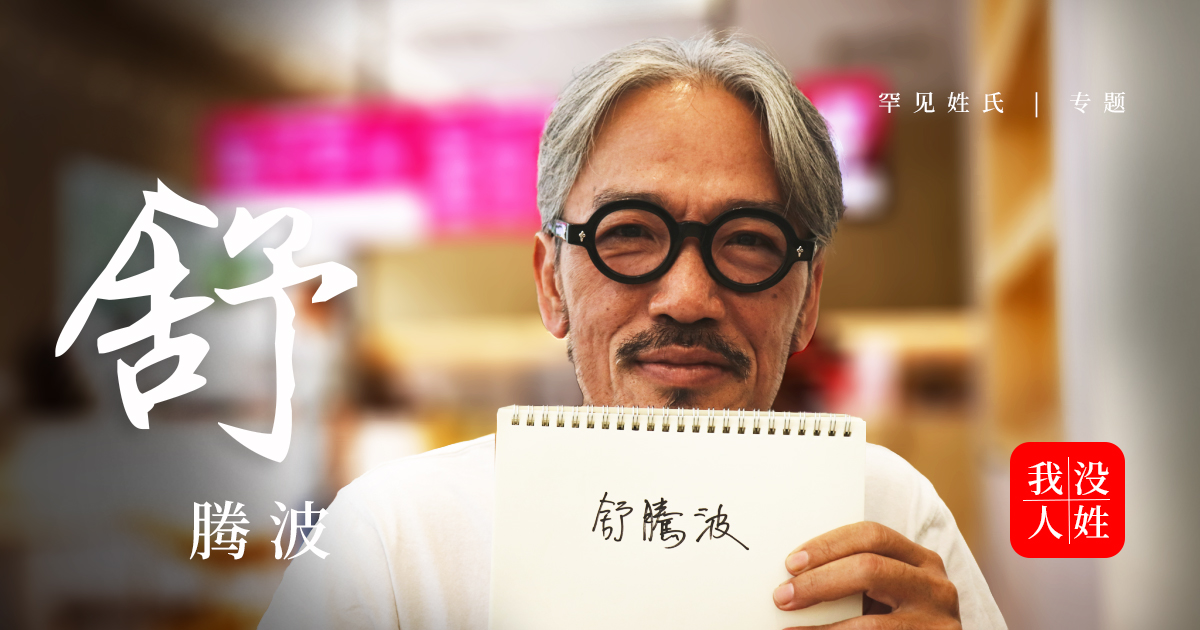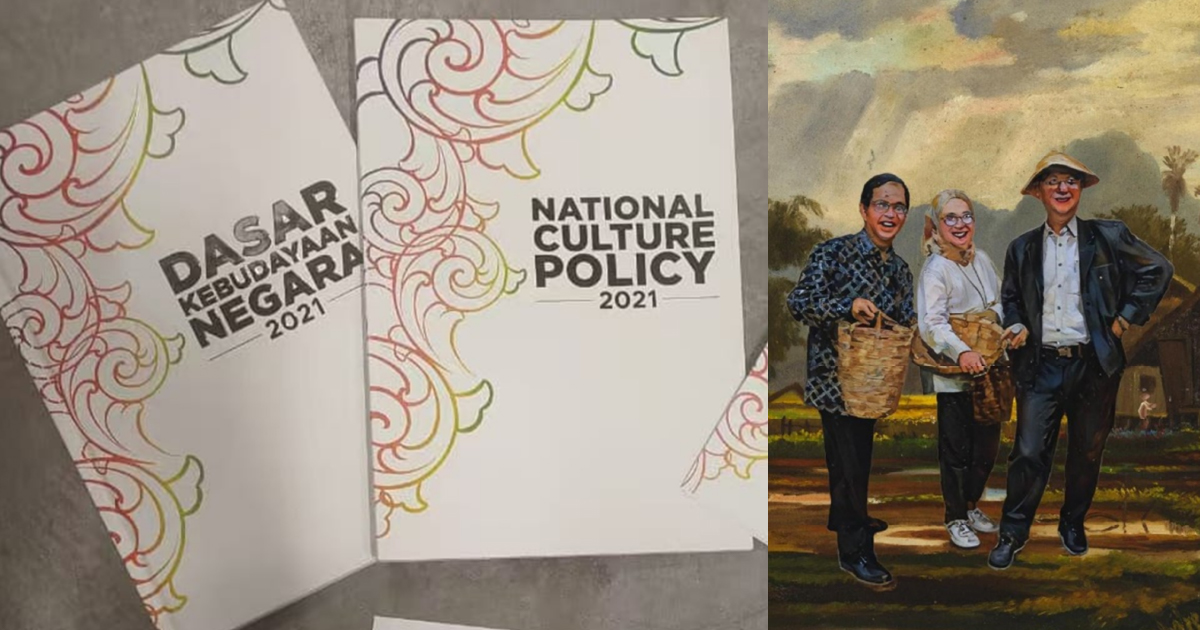在一场追求突破的艺术旅途中,《纸影人》不只是传统潮剧的一次延伸,更是一场关于身份、传承与革新的集体思考。由槟城潮艺馆出品、融合铁枝木偶、潮剧与现代视觉元素的演出,即将在8月6日首次登上PJPAC舞台,带来一段跨越五代、融合旧与新的文化演绎。演出背后的制作团队不仅有跨界的勇气,更展现出对本土文化深厚的敬意与重新定义的野心。
由槟城潮艺馆出品、融合铁枝木偶、潮剧与音乐元素的演出《纸影人》,将在8月6日首度登上PJPAC。8月3日,剧组展开了新的一轮大排练,准备将这部凝聚五代家族心血的潮剧带到吉隆坡的观众面前。
《纸影人》的制作人兼主演吴慧玲表示,这部作品早在2024年便于槟城首演,今年特别邀请马来西亚世纪华乐团、共响合唱团与吉隆玻在地的影像、音响等制作团队加入核心演出阵容。在正式演出前几个月,主演阵容都有持续来到吉隆坡一同进行练习与磨合。

《纸影人》延续了潮剧的传统,同时也大胆尝试走出原有圈子,与剧场导演爱美利亚合作。吴慧玲谈道:“一般这种传统剧目类大多会找传统领域的老师或前辈,而我们却选择了剧场导演。这次会邀请爱美利亚的主要原因是希望带来新的视角与元素,尝试一些变化。在排练的过程中,与导演产生不同想法时,我们会一起讨论,看哪些元素是非保留不可的,努力找到平衡点。互相包容才是最重要的。”
对合唱团成员而言,必须学习潮州方言,才能准确诠释歌词。乐手也需掌握潮州音乐特有的音准与韵味,这些皆是全新的大挑战。

关于《纸影人》的剧目含义,吴慧玲解释:“我们都称自己是纸影人。”
这部作品的灵感源自中国传统纸影戏,其在潮州落地后发展出独特的铁支木偶形式,即从平面走向立体。而今,导演艾美利亚把潮州文化与不同艺术元素融合,犹如马来西亚的多元社会。“可能你是广东人,但在槟城你会讲福建话。这就是马来西亚。”
《纸影人》以传统为本,却不拘泥过去的传统形式。透过剧场灯光、影像设计、服装与现代视觉美学包装,拉近与现代观众的距离。
吴慧玲笑说:“传统艺人多走向庙会、社区,偏地方性。年轻人比较多不会在庙口看戏,都选择到舒适且有冷气的地方。所以我们用他们熟悉的方式,让他们愿意走进剧场。”
用演出重新思考马来西亚华人身份
“我们自己做了那么多年,表演也好、生活也好,都是同一种模式,其实需要一个机会跳脱出来,去学习、适应另一种形式。”
吴慧玲补充,她希望把潮艺馆带出传统框架:“马来西亚这么大,我们也该尽量走出去,让更多人认识这种文化。”
她也提到,《纸影人》不是从头到尾“咚咚锵”的传统演出,而是具有结构与层次丰富的剧场体验。全场约两个小时,以其母亲杜爱花的真实故事为主轴,讲述家族如何将这门技艺传承下来,并穿插不同的表演形式与文化介绍。
“我们会用讲故事的方式带入内容,用串场的方式介绍什么是铁枝木偶、潮剧、潮州音乐、潮州锣鼓……不是说教,只是简单点到,勾起观众兴趣。”

尽管潮艺馆不断尝试创新,但潮剧的故事原型依然多改编自中国作品,还没有编写完全原创的新剧情。但吴慧玲指出,早在2018年开始,铁枝木偶戏部分已经尝试编写属于马来西亚的原创内容,将潮州技艺与本地文化融合。
《纸影人》也尝试原创,努力跳脱过去“前辈唱什么我们就唱什么”的延续模式,创作出真正属于马来西亚华人的潮州大锣鼓曲。这首由吴慧玲哥哥创作、由第五代传人她的侄女——吴欣洁担任指挥、领导整支打击乐队演奏的作品,象征着在地文化的新生。
“马来西亚没有像中国那样的戏曲艺术学校,我们都是私徒制,一点一滴传下来的。”但正因为如此,他们更需要思考:马来西亚华人和中国华人,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这是我们这一代要去面对、去扩写的身份课题。不是照搬,而是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化表达方式。”
代际传承的艺术厚度差异
“我们家从第一与第二代代演潮剧、到第三代我妈妈演铁枝木偶、第四代再结合两者,第五代继续传承。”这是一个跨越五代的艺术家庭,两种表演形式并存、延续。“铁枝木偶与潮剧,其实是潮州同一个文化背景下的两种形式。只是演员不同,一个是真人、一个是木偶,但锣鼓、唱腔、音乐,几乎一模一样。”
但在吴慧玲眼中,不同世代之间,最大的差异不是形式,而是艺术的厚度。

“现在最小的传承者,吴乙韩才19岁。虽然他们对潮剧从小耳濡目染,在这个环境中长大,但他们最终还是属于新时代的人。文化艺术这件事,是需要时间、生活去沉淀的。”
她借用美食来形容代际传承的差距:“以前的kuih又大块、又厚、便宜又好吃;现在的变小了,味道也差了。比如福建面,以前火候够,炒得香,现在的人虽然学了,但功夫就是不到位。”
吴慧玲并非在贬低新一代,而是指出环境变化带来的影响:“我妈妈那个年代,娱乐很少,唯一的娱乐就是听戏。现在网络、短视频太多,不可能叫我的侄女每天都听潮剧。”
“我们无法对抗时代洪流,只能顺着它前进。”
吴慧玲强调,关键在于如何用现代的方式,把观众带回来。“我们是非主流、小群体,不能去硬推。也不能抱怨别人不喜欢传统,他们只是有更多选择。”
她也提出另一种可能性:“有些人其实是喜欢传统文化的,只是因为没有尝试过,所以他还不知道。”
为此,她们不断地为传统文化进行推广,去打开观众的视野,引导他们去发现传统的魅力。
而这一路走来,并不容简单。吴慧玲分享道:“以前行业内的人会讲你,因为传统领域就是比较保守。做创新的人,很容易被批评‘不传统’,以前的我也会这么想。但因为我走出去了,我才明白,传统也需要改变。”
“所以我有两条路可以走。要我做传统,我可以很传统;要创新,我也可以走创新。这就是我特别的地方。我现在希望下一代能继续走出去,拓宽眼界,为传统文化带来新的生命力。
“不然,传统就只是一个‘死’的东西。”
《纸影人》的革新,并不是一夜之间
吴慧玲回忆起2013年,她第一次被剧场导演朋友Ling Tang邀请参加艺术交流计划(Art Exchange)。
“那时他看到我在Facebook上很努力宣传,但他告诉我要用新的方式,于是就邀请我去参与。进去以后才发现,天啊,我好像个古董,别人的艺术怎么都那么有创意、有深度。”

这场交流计划成为她艺术旅程的转折点。参与跨界合作、接触不同领域艺术家,一起做舞台剧的过程中,她慢慢意识到传统艺术也需要转变,必须进行革新。隔年,她便正式创办了潮艺馆。
“有时候视野不是说一定要马上转变,是慢慢被影响的。这11年,慢慢有一直有在“开”,但我觉得还不够大。我觉得我自己已经开了一些,但还不够大。”
她始终相信,创新必须建立在基础之上。“在你走出去之前,要先把自己的根扎稳。你没有底蕴,怎么创新?”传统与创新并不对立的,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吴慧玲也提到,很多人对传统其实有误解。“他们以为传统就是不能变,其实不是。几百年前的潮剧和今天完全不一样。像梅兰芳,他不断创新,才有今天的京剧。铁枝木偶戏也曾禁止女性上台,如今早已不同。
“很多人被传统这两个字框住了。其实真正传统的人一直都在改。只是讲的人忘了是谁改的,以为一切本来就是这样。当然,我们还是尊重,一些核心精神不能改。要看它背后的意义是什么。”
“我七岁开始就接触铁枝木偶戏,到今年45岁了。有时候我们为了前进,会不小心忽略了后面的传统。”
于是她开始记录吴家班的点滴,为母亲制作专场:“有些事情,一旦说了再见,就是永恒。”
“我希望马来西亚可以出现一个真正的革新者,她需要不畏惧他人的批评。我希望那个人可以是我。”
关于未来的计划,吴慧玲说《纸影人》的团队人数动员过于庞大,目前不太可能再做下一场。因此,本次许是《纸影人》的最后演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