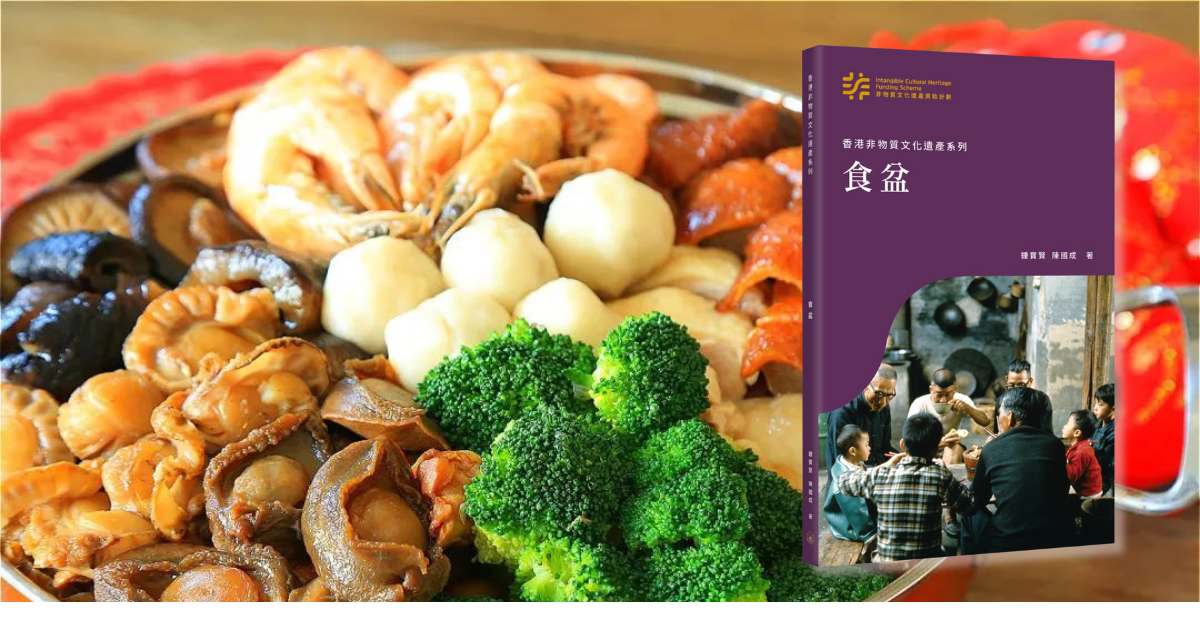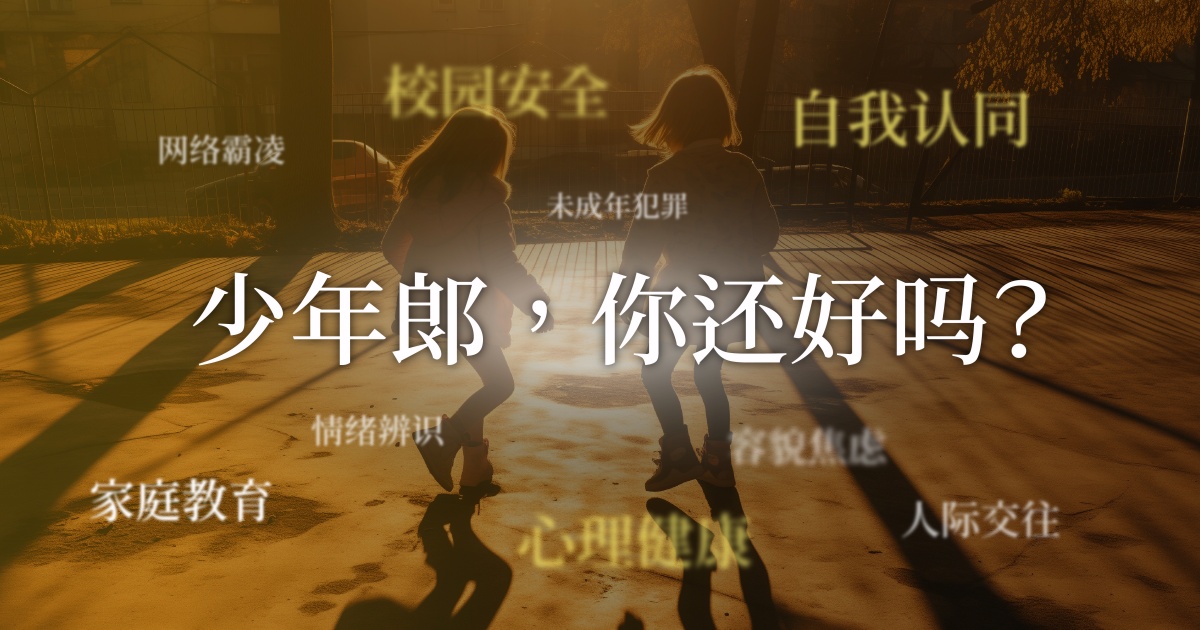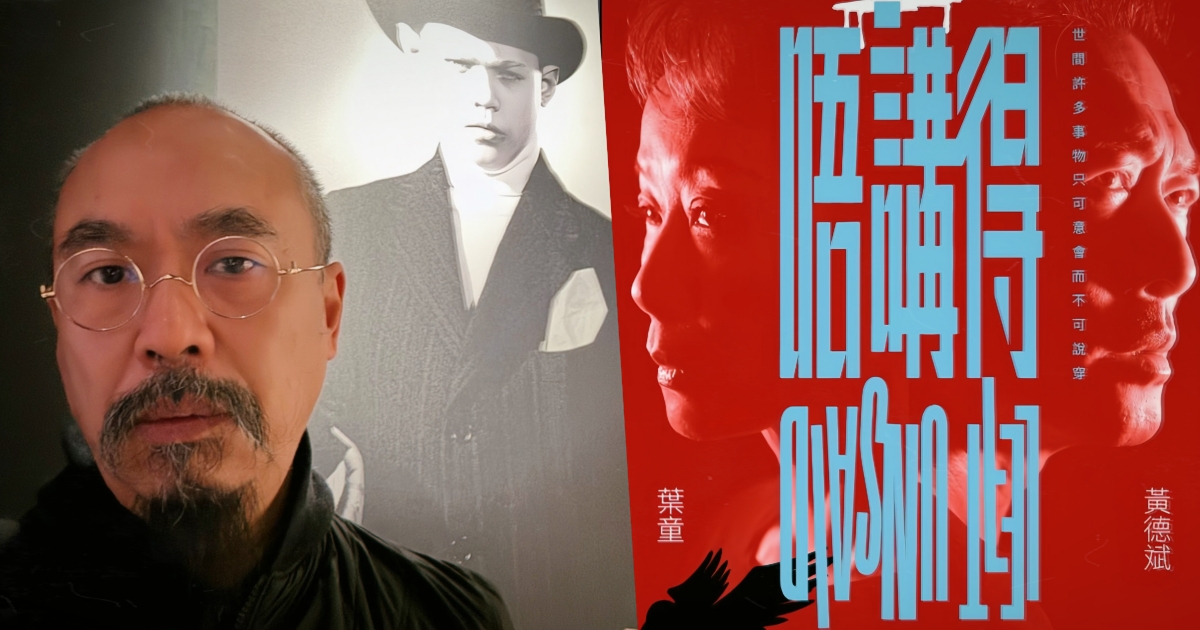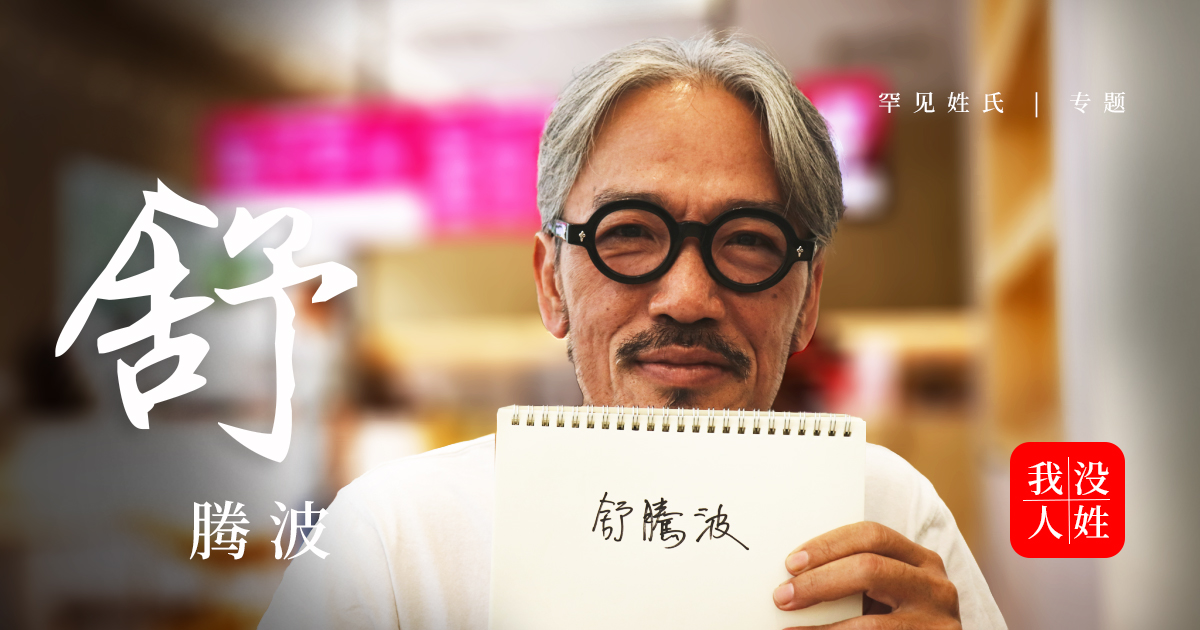在全球化与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马来西亚社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AI的崛起重塑产业格局,外籍劳工政策牵动经济与公平,环境治理则暴露出制度的脆弱。面对这些攸关未来的课题,华社研究中心主办的《政策改革与社会韧性:跨领域对话》论坛邀请学者与专家齐聚一堂,从不同视角切入,探讨如何在快速变动的时代中,为国家与社会建立更坚韧的支撑结构。
随着新时代风口的到来,国家与社会面临的新问题与担忧接踵而至。在全球局势与国内环境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下,国家和社会需要怎样的制度设计与改革步伐,才能在危机来临时更好地支撑彼此?从科技、政策到环境制度,各个领域的专家纷纷展开研究与对话,推动公众重新思考社会的治理与未来走向。
由华社研究中心主办的2025年马来西亚社会政策研究——《政策改革与社会韧性:跨领域对话》论坛的第二场于9月27日在隆雪华堂举行,主题分别是科技商业评论作家孙德俊主讲的《AI时代的机遇与挑战》、前国会政策研究员林慧琪主讲的《移工政策思考》及英国阿伯丁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博士陈慧思的《环境决策的制度缺陷》。
AI冲击下的机遇与风险
科技商业评论作家孙德俊以“AI时代”为主题,回顾了从1994年至今的互联网三个重点时期。他指出:1994年互联网商业化开启PC时代,1998年谷歌崛起统一了搜索引擎战国局面,2004年脸书与隔年的YouTube则带动了Web 2.0和社交媒体时代,社交媒体改变了人类沟通的习惯,也打破了传统媒体和大众的沟通,社交媒体也因此顺势成为新一代主流。而2007年iPhone的推出则揭开了移动互联网的序幕。如今的便利,如导航、银行应用程序、电子钱包、外卖订购,都是移动互联网所带来的变化。

说到这里,他把问题抛给在场的观众:“1994年的我们,能想象今天的生活吗?”
显然不能,正如我们当年无法预测社交媒体与智能手机的冲击,如今也无法完全预料AI带来的深远变化。
在他看来,AI将影响马来西亚的人才、教育、研发创新、行业应用、数据治理、法规制度与全球竞争力,而其中的人才、教育、企业与政府机构是国家最有可能抓住的机会。

一、人才:孙德俊分享了一位摄影师朋友的案例:“当外界担心生成式AI会冲击摄影行业时,这位摄影师却主动掌握ChatGPT与MidJourney,凭借专业背景提供‘摄影+AI图像生成’服务,开辟出全新市场。”
二、教育:将AI纳入课程,灌输学生使用AI工具的正确态度,开发“AI书僮”辅助学习,避免教育沦为机械化。他以南华独中引入人工智能教育为例,强调教育应在效率与人文素养之间取得平衡,确保科技不会使学习变得冰冷。
三、企业:AI转型的五大步骤——拥抱科技、识别痛点、连接数据、构建程序与持续改进。
四、政府:制定国家AI蓝图(NAIO),推出道德治理准则(AIGE),推动数据驱动的公共服务,并建立软硬兼顾的生态系统。
孙德俊在结尾引用了《双城记》的名言:“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
“如果你什么都不做,错过了这个时代,那就是最坏的时代。如果你掌握时代的脉动,在对的时候做对的事,这就是最好的时代。”
外籍劳工政策背后的政商共生
虽已经到了AI时代,但马来西亚仍作为发展中国家,其中劳动人口不容忽视。马来西亚高度依赖中小企业,而中小企业占比高达90%,贡献了40%的GDP,其劳动力极度依赖外籍劳工。但,我们是否关心外劳所面对的政策不公与处境?前国会政策研究员林慧琪指出,外劳政策长期受政商关系左右,导致制度缺陷与利益不均。
以外籍劳工的强制体检(FOMEMA)为例,雇主每年需为劳工支付约4.14亿令吉的费用,近年来收费不断增加,但政策合理性却备受质疑。非法劳工无需体检、医疗覆盖不足,使得体检制度难以真正保障公共健康。与此同时,FOMEMA公司在2022年的净利润上升近六成,凸显其垄断性。

外籍劳工在马来西亚主要有两种保障制度,其一是外籍劳工赔偿计划(Foreign Workers Compensation Scheme,以下简称FWCS),其二是职业灾害保险(SOCSO)。
FWCS是一项专门为外籍劳工设立的保险,用于补偿因工伤、职业疾病或死亡所造成的损失。该保险的保费相对低廉,每年仅需70令吉,一旦发生事故,最高可索赔2万3000令吉,并能在理赔时一次性全额支付。
相比之下,SOCSO的赔偿机制较为复杂,其赔偿金额会根据劳工的薪资水平、伤害程度以及家庭结构等条件来计算。以死亡赔偿为例,SOCSO最高可提供7500令吉的赔偿,其中4500令吉用于将遗体运返原籍国,另有3000令吉作为抚恤金给予家属。然而,虽然SOCSO的保费近年来不断上涨,其保障范围与赔偿额度却并未有显著提升。

总体来看,FWCS以低保费和一次性高额赔付为特点,而SOCSO则采用差异化的计算方式,但在实际保障上显得相对有限。与此同时,从2016年至2025年,外籍劳工的人力成本持续增加,令雇主在选择和承担保险时更需衡量成本与保障之间的平衡。
在政策执行上,“漂白计划”与外包公司MyEG成为争议焦点。尽管有70万人注册,最终仅2万人成功合法化,而资金流向不明。MyEG的财报显示,其收入与利润因该计划大幅增长,引发“政策被商业化”的质疑。另一家公司Bestinet自2013年起掌控FWCMS系统,更在2025年被强制指定为续签平台,形成高度垄断与潜在的利益冲突。
最后,她提出了七项建议,包括政商分离、开放体检市场、保险制度多元化、数据主权归政府、设立跨党派监督机制、外包透明化,以及重新定位外籍劳工政策目标,避免短期依赖与利益绑架。
我们的环境政策与制度究竟面对什么问题?
人文与自然总是紧密相连。自独立以来,马来西亚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常常忽略环境问题,而环境与制度之间本就唇齿相依。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全球第一波环境制度化浪潮出现在美国、瑞典与日本,马来西亚是最早迎接这波新浪潮的发展中国家之一。1972年,马来西亚签署《斯德哥尔摩宣言及行动计划》,并于1974年制定《环境素质法令》(Environmental Quality Act 1974),同时成立了专责机构,包括环境素质理事会(Environmental Quality Council)及环境局(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目前,《环境素质法令》下已衍生约二十项相关法规,为环境保护建立起初步制度基础。
随着国家发展规划的推进,环境政策逐渐纳入国家议程。1976年第三大马计划明确提出,将在各类发展方案的规划与落实过程中高度重视环境保护,以确保在发展目标与生态保育之间取得平衡。1996年第七大马计划首次提出国家环境政策,到了2002年,科学、科技及环境部正式推出《国家环境政策》,矢志通过“在保护环境永续性的前提下,推动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发展,并提升马来西亚人的生活质量”。

然而,英国阿伯丁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博士陈慧思指出,马来西亚环境政策的制度建设仍存在结构性问题。
她分析:“大马计划的拟定过程高度集中于首相署,缺乏透明度与制衡机制。”环境影响评估(EIA)也并未强制纳入发展蓝图阶段,导致许多大型工程在未完成环评的情况下就已动工,例如巴贡水坝与柔南经济走廊,最终带来严重的生态破坏。这些制度上的缺陷凸显了马来西亚在追求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仍有待解决的矛盾与挑战。

她批评联邦与州政府普遍延续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将公共资源调拨予政治盟友与官联公司。例如,巴贡水坝在财务危机后由官联公司接盘,最终动用公积金贷款填补亏空。州政府层面,砂拉越长期由首席部长一人掌控财政与资源事务,伐木特许权多颁予家族企业,导致严重森林流失。
她也点出:“王室与土地开发的利益纠葛日益严重,彭亨州苏丹及相关公司在榴莲园、油棕园与伐木业的获利规模庞大,反映宪政制度的制衡失效。”
在环评制度方面,法律仅要求发展商提呈环评报告,但最终决策权仍掌握在政府手中,环境局的专业意见常被忽视。例如:
一、森林城市计划:发展商将大规模填海工程拆分成小项目,企图规避详细环评。
二、罗京高原案例(1996年):环境局调查发现,当地14项发展计划中,仅有数项提交环评报告,但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仍在环评未通过前批准相关申请。

森林城市项目与罗京高原案例显示,发展商可通过拆分项目或违规操作绕过环评,暴露法律执行的软弱。
陈慧思指出,环评制度的“Missing link”在于缺乏强制遵从机制。环评的功能本是协助决策单位(如联邦、州或地方政府)做出判断,但在马来西亚,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决策单位必须遵从环境局的意见。结果,环评沦为形式,难以真正阻止资源掠夺与生态破坏。
马来西亚环境治理的最大挑战,在于制度上缺乏透明、制衡与强制执行的环节。只要环评缺乏法律约束力,政府与利益集团间的权力结构未受制衡,环境政策便难以发挥实质效用。

从AI到外劳政策,再到环境制度,这场跨领域论坛分享有几项共同点:马来西亚的制度在面对快速变化的全球局势时,常因透明度不足、制衡机制薄弱、政商关系紧密而陷入困境。
然而,如三位学者所强调,挑战亦是契机。无论是科技的应用、劳工政策的调整,还是环境治理的制度化,只要社会能建立更健全的制度框架,并在改革中注入透明、责任与公共利益的核心原则,马来西亚才能在未来的不确定性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