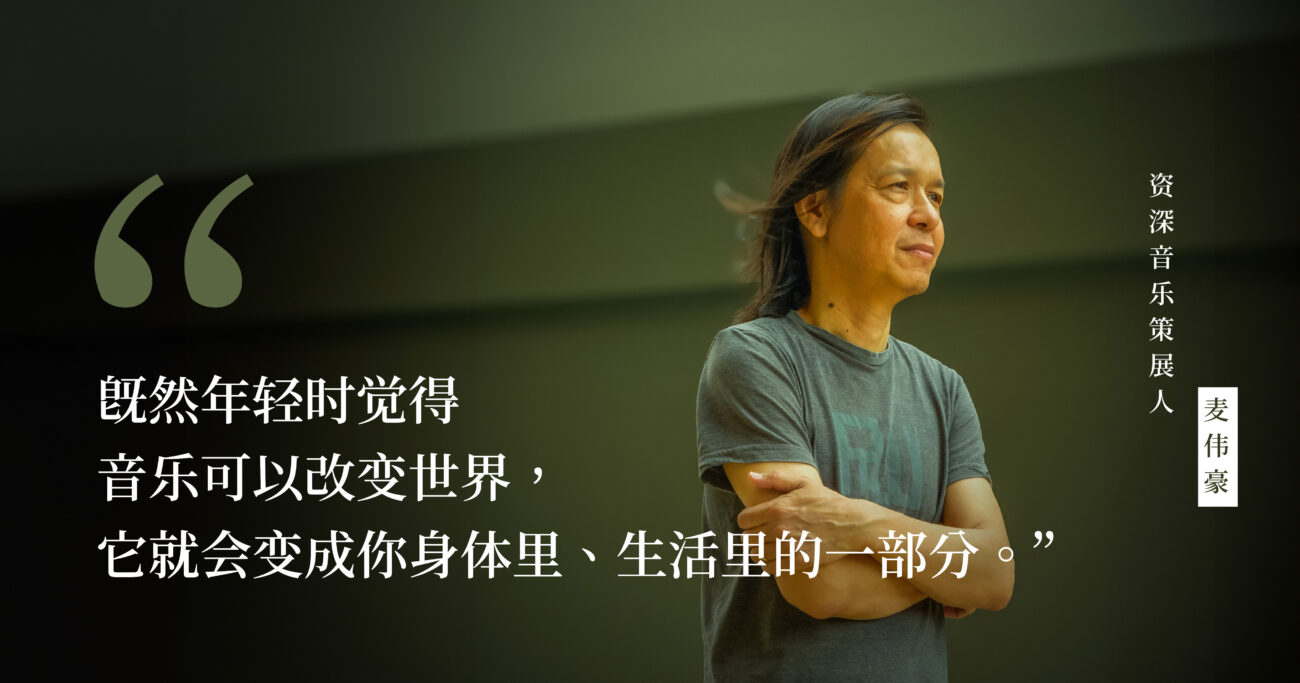我几乎不对外提起这件事。也许只有几个亲近的人知道,比如我的家人、羊男和几位比较要好的朋友。那天,我又提起这件事了。
这件事和一个小学作文题目有关系,那就是“我最难忘的一件事”。
最近提起这件事是因为陈老大来寻羊的时候,提起女儿的中学考试题目竟然是“我最难忘的一件事”。一听到这个题目,我就毛骨悚然。也就把这件事告诉了老大。老大只问,这件事写过了没有,没有就写出来。
可是……这样会对大家心目中心爱的老师不敬。老大说写吧,没事儿,后面加上可怜的孩子。虽然我已经三十九岁了,可是一听到可怜的孩子,突然又回到那个可怜的孩子了。经过两个星期的深入思考,我想放过这位可怜的孩子,写出来,好好地跟她告别吧。
这件事发生在六年级。十二岁的我,才转到这所学校一年。一年前才刚摸熟的环境,马上又因为被排到另一个班级,而需要再重新认识一遍。
有一天,我的华文老师要我们写“我最难忘的一件事”。我写了一篇奇特的文章,作文里的主角不是我自己,而是我幻想的一个人物。这主角是一个来自印尼的孩子。当时很多印尼人来马工作,我写“我”最难忘的一件事,是在“我”生日当天,“我”的爸爸要跟“我”告别,到马来西亚去工作。“我”如何的不舍和难过,从课室追出学校,试图留下爸爸。
这篇作文是我第一次尝试写创造出来的故事,也几乎是我人生最后一次这么写。写的时候,似乎停不下来,甚至感到卓越的满足感。可是,作文交上,老师改了之后,有一天老师是这么说的:“谁没有拿到自己的作文的,站在椅子上。”
那个人是我。
老师说:“你以为你是谁?你以为你是你的爸爸?你为什么要学你的爸爸写东西?你拿这篇作文回去给你爸爸看!”
那天,我也被打了。手上留着深深的藤条印。回到家我当然没有给我爸爸看这篇作文,因为十二岁的我以为自己做错事,我才不想又被骂一次。我还在压抑,原来我这样写是错的。其实当初若我有拿给爸爸看,可能爸爸还会认为我写得不错。十二岁的我,单纯得有点笨。
从那天起,我只写公函和私函。我不写一切需要创作的文字。初中碰巧在马来中学上课,我差一点就不想多拿一门华文课,我对每一个人说我爱英文。在爸爸坚持之下,也只好另修一门华文课,很多时候是星期六去学校补的。
也许是我只写公函和私函,让当时的华文老师感到不安,他在我中二的时候半鼓励半强迫地逼我交上一篇文章。于是我交了,提心吊胆的交。不久后,此文章还被老师投稿到《蕉风》。老师拿着《蕉风》给我看,跟我说,你看看,你是可以写的。我哭了。
这事儿,我大概没有对很多人提过。也许同班同学也不记得了吧。同学们都很爱戴当时六年级的这位“严师”。而我却一直跨不出创作的门,只要一想编故事,就好像做错事。
我知道我不能把自己没能创作的能力怪在一个老师身上,这是自己的事。也许我应该做的是,放过自己,确切地和这件事隔离,永远的把它留在这里。
不再见,可怜的孩子。
延伸阅读:许书简专栏《小学作文》其他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