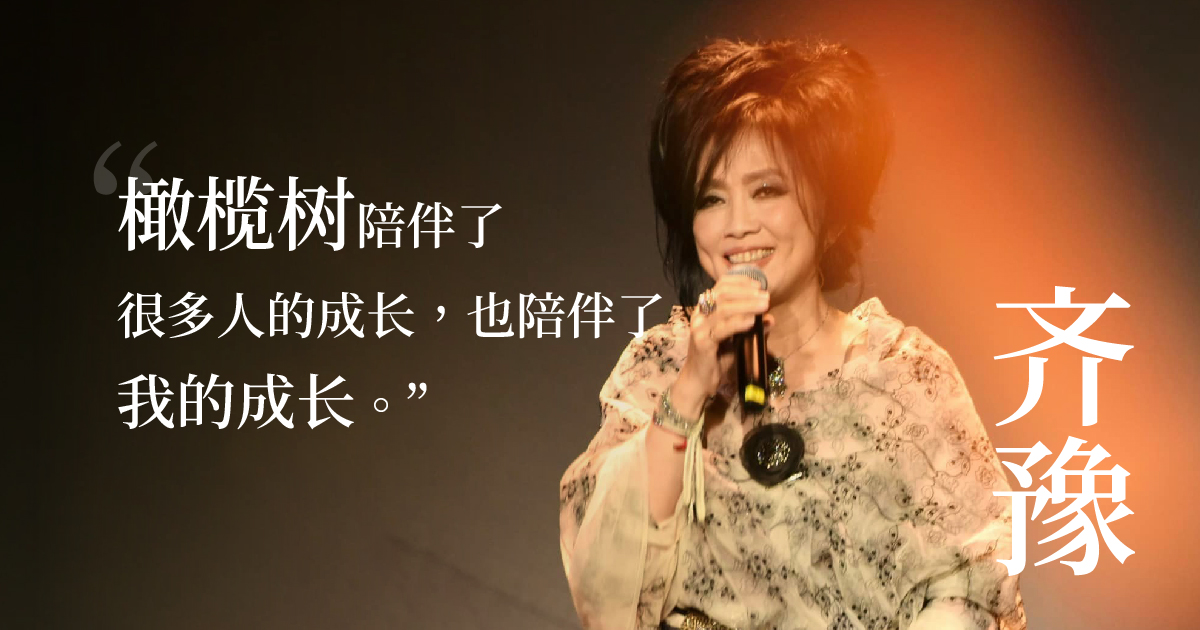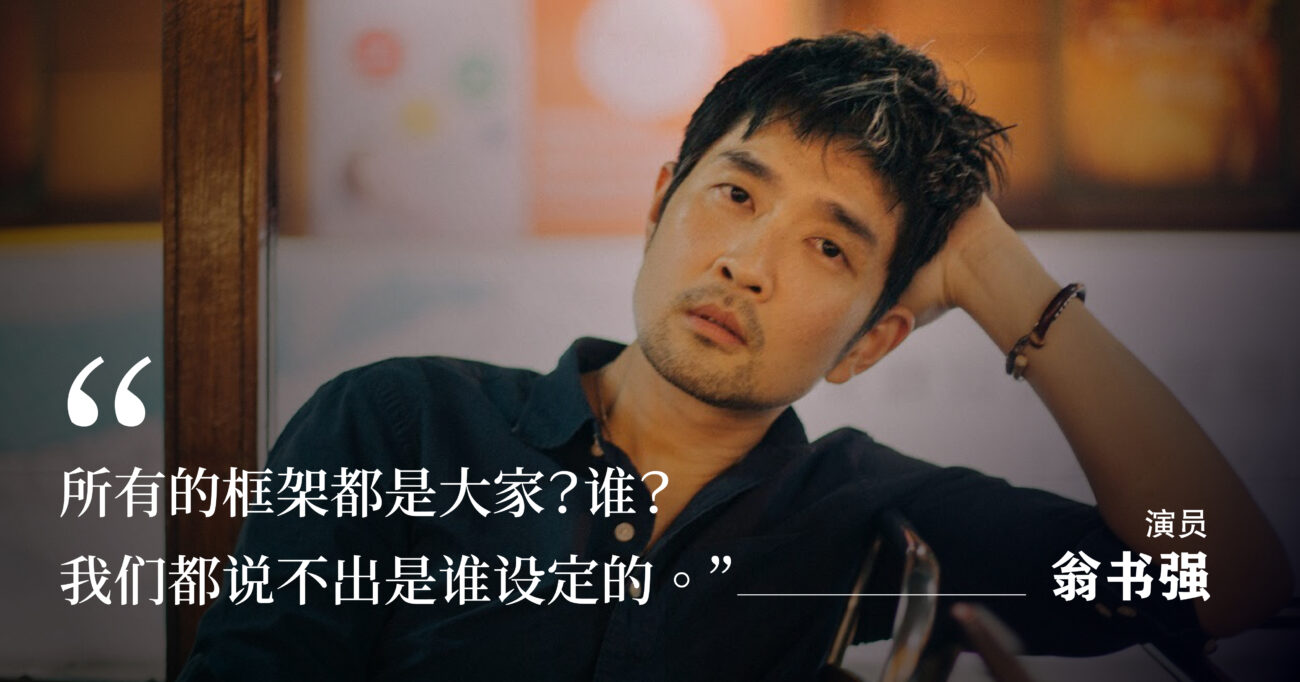读人类学的人应该都知道几年前刚过世的英格兰-爱尔兰裔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他是东南亚民族研究专家,印尼话说得非常流利。
1999年初,伦敦大学政经学院特地办了一场和安德森的对话,他在执教的美国康奈尔大学通过电视直播,和在伦敦的老朋友塔里克阿里(Tariq Ali)隔空对谈。席间有人问到马来西亚的烈火莫熄运动,安德森很客气,先用印尼话问候在座的马印和文莱同学,接着转英语表示,虽然他父亲在英殖民的槟城出生,马来西亚不是他本身的专长,只提了一些两国的差异作为提醒。我记得他还说了一个故事,大约是:
“当年苏卡诺反对马来西亚联邦,我们这些左派的学生都支持,看作是英美帝国计划的延续,我也一直以为自己能够成为印尼社会的一分子;没想到被之后的苏哈托政权看作是共产党,把我驱逐出境前还有右翼民族主义分子到我住处示威。我很努力学好印尼话甚至爪哇话,很显然这些都不足以让我取得印尼社会的信任。我因此重新思考国家和民族这些东西对人类有什么意义。”
对当时的我,这番话是相当震撼的。安德森当年单纯地以为印尼话说得溜就会被认同,正如马来西亚总有人坚持说同一个语言才能取得“民族融合”,但我们可以预见的是统一语言之后,接下来会不会要求宗教合一?
那时候我在欧洲独自生活已将近十年,与所谓的“祖国马来西亚”各方面都渐行渐远,也准备在伦敦长期落脚。若非烈火莫熄引来其他国籍朋友和同学的追问,意外地成为别人认识这个东南亚小国的“窗户”,再促使我“回国”体验,今天我大概已经是个英籍华人。
我不晓得安德森的这段经历是否影响他后来写出《想象的共同体》这本书,却颇能引起我个人的共鸣。例如他写道:“民族是想像的,因为即使在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从来不认识他们的大多数同胞,并和他们相遇,甚至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相互连结的意象却活在他们的心中。”
旅居伦敦时候,我们这些“勤工俭学”的人和那些家境富裕,无需打工只需专心求学的马来西亚留学生基本上没有交集,因为彼此的社交圈子不同;和那些拿政府奖学金,几乎以马来人为主的留学生,更是几乎没有来往。偶尔想念马来饭或叁峇的滋味,到伦敦的Malaysia Hall秀几句马来话进去饭堂吃饭或看马来西亚报纸,除此之外,我想不到和其他“马胞”有什么关系,毕竟我们彼此非但不认识,连利益都不同。
所以我越来越不相信民族或国家这回事。人类如此划分,图的不外集合力量保障自己的利益,或允许政客操弄对他人/他国的恐惧或优越感,没有多少利他的成分。我们不可能一边嘲笑中国人的民族主义,一边在马来西亚当二等公民还自我感觉良好。中国的民族主义和马来西亚的国族主义,其实不过半斤八两。
最后,一个家财万贯不见得与你分享,大权在握却不断发表种族主义言论的人可以骗得千万人为其感动落泪,而那些每天辛勤在油棕园、工地、工场、咖啡店打工,甚至在家里替我们照顾老小的所谓外劳反而被视为他者般警惕、防备甚至排挤,连个公交月票都不让他们享有,这样的国家有什么可爱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