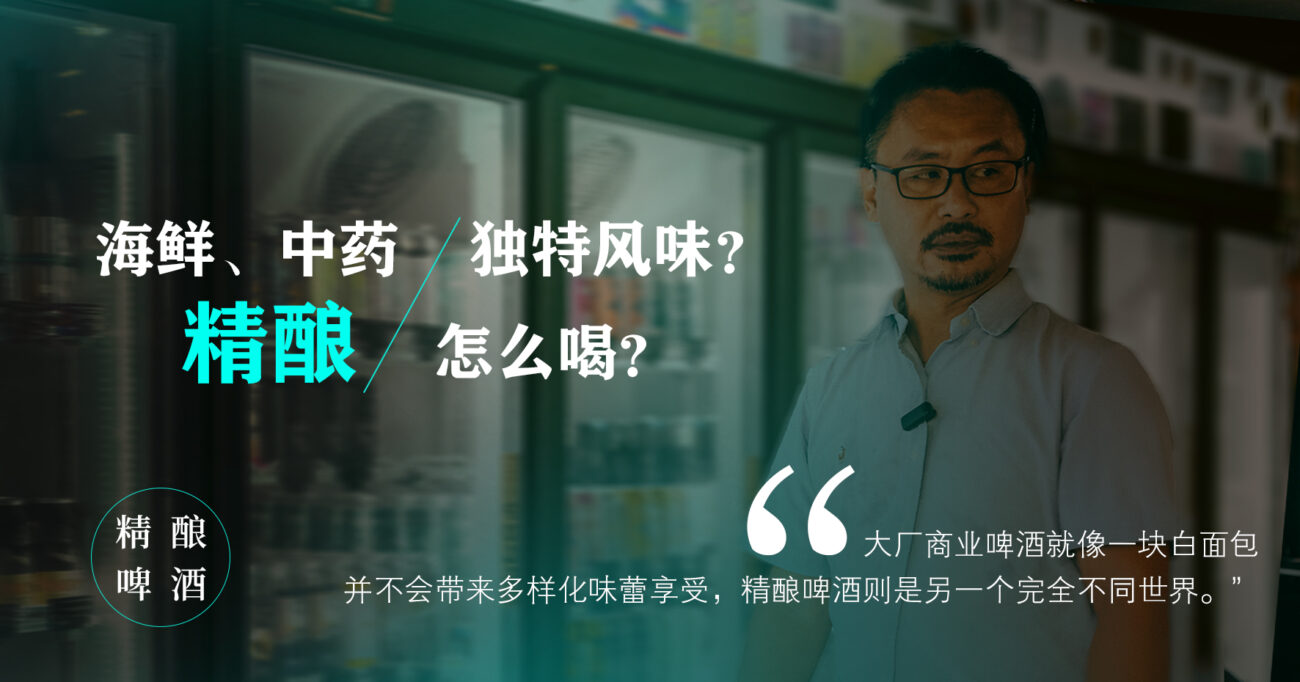我推着坐在轮椅上的他从病房走入电梯,当电梯一关,他用无奈的眼神看着我说:“我很难过,这将会是我最后一次出外吃晚餐。”
我没有多回覆,点了个头,给了他微笑。
我们都知道,临终的他时日不多。前一天,他要求医生准许他出外吃一顿饭。我们团队立即开会,医生及护士叮咛我说要准备一瓶随身携带的氧气筒、多种相关药物,而且还打电话给相熟的救护车司机,万一发生任何紧急状况,请他随时准备载送我们回院。
为什么是我陪他去吃晚餐呢?
他是一名70多岁的独居老人,无依无靠,已经在病院住了三个月之久。而他住在这里多久,我就陪他多久。我出现成为他的医疗社工,也全因为我们病院上上下下没有一个员工不被他骂过。
就这样,我成了他的“监护人”,当晚需要带病人出去吃晚餐。他要去的地点不是豪华餐厅,也不是去吃全城闻名的美食,他只想去他以前居住的社区附近一间茶室,吃一碟海南鸡饭以及喝一杯热茶。
电梯一打开,不远的前方就是病院大门口的德士车站,我们坐上德士,往茶室奔去。
一路上,他很安静。我也不想干扰宁静的时刻。抵达茶室,他用颤抖的手指稍微了指一个角落,告诉我:“那是我常坐的地方。”
因为从病院到德士、再到茶室,我们移动了他两回,所以当下坐在轮椅上的他很喘、脸很白、手很抖;一直冒冷汗。然而为了照顾自己的尊严,他和我说他暂时还不需要氧气筒。

他叫我去点了一碗苦瓜汤和一碗白饭。他说海南鸡饭,他吃不到了,太油,很难消化。有不少街坊及美食档口的小贩也同时走过来,和他打招呼。他一一挥手、点头、微笑。大家询问他的状况,他就用食指指着我,希望我就像他的经理人一样代替他一一回答。气喘的他只是负责点头及微笑。
那一刻,我懂了。他想要出外不是为了苦瓜汤或者海南鸡饭,他是来找他的朋友告别的。我就像一个代言人,一一告诉大家 Uncle 他现在住在哪里。该说的我都说,不该说的,我就和他一样,微笑及点头。
小贩端上一碗热腾腾的苦瓜汤配上一小碗白饭,坚持不收费,请他吃。虽然他没有亲人,可是这里的街坊及小贩们,让我感觉就是他的“家人”。
我们坐在那儿一个小时,他很用力吃饭,半碗也吃不到。
离开之际,他和大家挥手、微笑、点头。他比任何人都懂,这将会是他最后一次见他们了。坐在德士里,他的目光没有离开茶室。
回程坐在德士里头,他感触地与我说对不起。他说:“阿量,对不起,耽误了你的下班时间,不好意思。”
三个月前,我认识的他脾气暴躁,生病的人特别容易暴躁,这我很能谅解。如今变成如此柔软及谦卑的他,我看了,心里即感恩也难过。
德士把我们载回病院。电梯一打开,再一次,我推他进入电梯,他对我说:“我们完成了。谢谢你,阿量。”我们俩不约而同点头、微笑。
对于日渐衰退的身体,接下来的日子,他要接受长期卧躺在病床,需要护士全天候地服侍。然后在昏迷状态中,渐渐死去……
这一次出外,也意味着这是人生最后一次的出外了。当我把他送回到病房,他对我说:“陪我聊聊天,好吗?”
我没有拒绝。今天晚上的时间,本来就是留给他的。我拿起一张椅子,摆在床边,坐下,看了看挂在墙上的时钟,8点45分。
就这样,带着氧气罩的他,依然坚持和我再谈半小时之多。
他说:“我不要自己一个人。我不要我死的时候,没有人看顾我。”
他说:“我愈来愈气喘。”
他说:“我很难过。”
是的,我都在听。大部分时间,我只是在听。眼前这位男性长者,虽然气喘,但是全然打开心门。可惜,那里头只有寂寞、焦虑、害怕;还有难过。
他坦言:“做人,做到这样,我真失败。”
说到这里。他哭了。
我不想安慰他。也不想换个说法,更不想用正能量的话语填满这充塞着死亡的空间。我就是安静听。他对自己的人生做出任何解读,我都给予允许以及尊重。难得他愿意哭,我就安静陪伴。
他说对不起。我说没关系。最后,他还是决定今晚不要哭,因为,他还得要在今晚深夜与寂寞共存。他不想让寂寞得逞。越哭泣的话,寂寞越得逞。
他说:“可以了。你走吧。不要再耽误你的时间了。”
九点半,我还是选择留下来再与他多谈一会儿。 因为,可以谈话的时光,应该也不多了。医生也曾经和我说要是癌细胞蔓延到他的脑部,他就会开始昏迷。现在的背部疼痛,已是迹象之一。所以,我珍惜可以与他谈话的时光,虽然已经工作了一整天。再继续听一听他的生命故事,直到十点正。
他说:“走吧,阿量。你累了,真的要回去了。明天早上,还有很多病人需要你。”
坦白说,我越来越喜欢他的真诚及柔软。一个当初怒气冲冲的老人家,如今充满了很多关怀,虽然他自己没办法解决自己的问题。走之前,他说:“阿量,很感谢你。我知道这些陪伴都不是你的工作,你已经做出了超出你该做的本分。我很感动,也很感谢你这三个月的陪伴。我不知道怎样报答你。”
我比谁都清楚知道他今晚除了和他的“家人们”告别,他也在今晚和我告别,毕竟,他已经把我当成是他的“家人”。只是我们俩看破,都不说破。
我也趁着这个机会和他说:“其实我也很谢谢你。看见你如此真诚地和我分享内心世界,我觉得和你很投缘。我不觉得很有压力,反而我能付出多一些,就是多一些。谢谢你让我陪伴你。”
站在门口,我给他一个深深的鞠躬。他合掌看着我,点头、微笑。
隔天早上我回到慈怀病院,床已经“空”了。我再也看不见他,他在当晚和所有他重视的人告别后,在深夜里悄然离开……
那一个夜晚,其实已经过了十个年头了。我写到这里,依然无法忘记那个晚上的道别,尤其是他的点头及微笑,还有对谈。
我当然没有告诉他有关我父亲死亡的故事。年少的我没有智慧去陪伴父亲去世,错过了很多说声谢谢以及对不起的机会。当我能真诚和他说声“谢谢你让我陪伴你”,其实这些言语背后透露出我也在圆着一些我无法陪伴爸爸离去的缺憾。与其说我协助他,实质上他也同步在疗愈着我和爸爸之间未完成的事。
所以,你说,人生啊,到底是谁在帮助谁,谁才是助人者,还真的说不准啊!所以,他的生命哪里失败,至少十年后的冯以量依然不曾忘记那一晚的告别会。
延伸阅读:冯以量专栏《就是生死》其他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