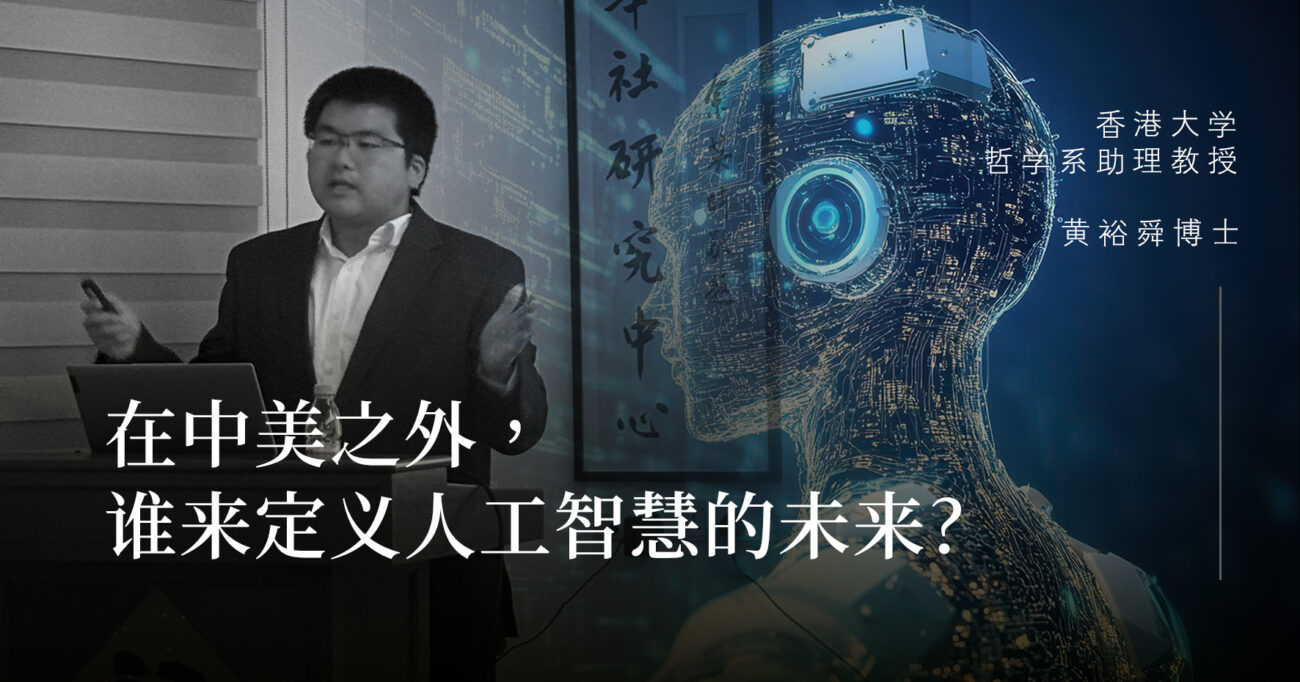奈米小说集诗、散文、散文诗和小说于一体,文体比微型小说更小。它如同灵感的碎片,跳脱固定布局,浓缩题材,借题发挥,劝喻讽颂,感怀伤逝。要如何描述阅读奈米小说的感受?这种感觉就像,每读一篇方路的奈米小说,便在心里大病一场。久病成疾,然后又在下一篇奈米小说中平复如故。不药而愈,如此往复。马华作家方路,在文学的沃土笔耕不辍,硕果累累。虽被文字缠身,却也未将农科专业背景始乱终弃。他巧妙地将农科的理论转移到文学上,“我是以轮耕的方式写作,好像种植农作物。这个阶段写诗歌,可能接下来就写小说,诗歌的养料就得以保存。源源不绝。”从2017年的《我是佛》到2020年的《忧伤牛》,再到即将问世的第三本奈米小说,在耕地之中盘根错节、不眠不休地生长,用海南咖啡浇灌,吸星洲之灵气,此间飞禽走兽东奔西走,魑魅魍魉出没横行。方路的奈米小说,没有悲戚,却字字泣血;不谈信仰,却编织出宿命感的大网。
与方路相约在一间海南咖啡店。他从外面进来,径直向卡座中的我走来,突然站住。正当我疑惑之时,只见他目光掠过狭窄的卡座,又打量自己的腰身,哑然失笑。
换了一个位子。刚一落座,发觉邻座男子握着手机,屏幕内外笑声如雷鸣,像搭了一个戏台。
再次换位子。一波三折,终于坐定。定睛细看方路,乌黑鬓发,白须满腮。头发胡子,黑白分明。举手投足间颇有些绿林好汉的风度,正气十足。缘何深夜敢与满纸鬼怪互诉衷肠,一望而知。

“在新闻组不受新闻写作影响,在台湾又不受台湾文学影响”
他一落座便热络寒暄。方路原名李成友,提及笔名的由来,他笑称“后来变成几个版本,那是他们自己诠释的”。他解释说,“第一个来源是我很向往方修,还有方北方的风格。最初写作的时候很想追随他们的方向、道路。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我是写实主义的。”
“我选这个笔名初时的概念是受这两个人影响。后来就延伸到别的意义了,象征找出自己方向的路。”
方路的写作生涯也是一波三折。“写作是从中学开始,但是有一个问题,中学那时候是在乡下。真正接触文学是在去了台湾之后。去台湾之前的文章,其实我自己都没有留下来太多,手稿都没有留下来。”不免有些遗憾。

在交谈中,他神态自然,丝毫没有矫揉造作之态,每想起一件趣事便笑着分享。“有人评价我看起来不像作家,不够文青,不够文艺。”方路在《星洲日报》新闻组,但写起诗歌散文比副刊还副刊。谈及作品风格的形成,他幽默地总结道:“在新闻组不受新闻写作影响,在台湾又不受台湾文学影响。”
回首台湾留学的过往,他侧重强调“在台湾留学,是吸收他们的养料,而不是学他们。”香港作家西西对他影响极大,在台湾时他阅读很多西西推介的西方作家,也是这个因素使他不完全受台湾文学影响。“西西让我接触南美洲作家、文学,其实那个氛围很适合用在马来西亚。”在方路看来,马华文学与南美文学因受地理因素影响所以有颇多相似之处。
作为在椰风蕉雨中滋生的马华作家,方路的文字如雨水冲刷过的顽石,带着粗粝感,在荒芜中又散发着血腥气。他对马华文学的发展有着深刻的感触,“马华文学超过100年了,其实本土的才是最原始的。马来西亚文学受本土的发展、局势影响,基调更现实。写作与政治的关系是很微妙的,不可能脱离。”在马华文坛中,作家对马华文学中的相同主题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对疼痛也有着不同的表现手法。与其他地区的华语文学相比,马华文学的基调更为真实、残酷,表达更为野性、难驯,文字最终成为所经历的年代的载体。末了他也一阵见血道出马来西亚作家的现状,“马来西亚都是业余的作家,必须靠工作来维持生活。”
“我是以轮耕的方式写作,好像种植农作物”
方路穿梭于不同文体中,有时上天揽月,有时遁地穿行,来去自如。“我写诗,散文和奈米小说,心态完全不一样。诗是抒情,散文是我真实的故事,真实的阅历,别人学不到的。散文可以去向很深的地方,我还在发掘自己没有抵达的记忆。散文是记忆,小说是虚构,刚好相反。”

奈米小说正值轮耕之时,在方路的文学土壤上开出妖异的花朵,疾风吹拂,足以蛊惑人心。方路坦言,“诗歌是最难的,诗歌我用最多的时间,克服之后才写别的文体。如果我最开始写奈米的话,成果可能不太一样。其实奈米小说我写得比较从容。不是刻意写出来的。奈米对我来讲是掌握得比较熟练的一种文体。”
奈米小说从播种、除草到施肥,说是方路的“专属农作物”一点都不为过。“这种文体目前在马来西亚是没有的,它比微型小说还小,在中国又称为小小说。”
由于读书时学的是农科专业,他便将农科的理论移接在写作上,“我是以轮耕的方式写作,好像种植农作物。这个阶段写诗歌,可能接下来就写小说,诗歌的养料就得以保存。源源不绝。”

方路称奈米小说的写作意图是“保温”。“写了两本我就停了一阵子,吸收养分。写短篇小说的timing还不到,奈米就可以保温。”
“你会发现在15本书里面,采取的是轮耕的形式。文学不能拔苗助长,要有一个过程,要用一辈子来规划。”他对待写作态度虔诚,更讲求文火温养,水到渠成。奈米小说洋洋洒洒落于纸上,有如灵感的碎片。待有一日,方路将其捡拾整理,便顺理成章结成小说。
“有些人是觉得可惜,每一则可以推展成短篇小说。将一些深度的题材浓缩,似乎有些浪费。我未来的工作可能会将题材发挥,扩展为小说。奈米小说是跳脱固定布局,但小说应具备的场景、人物、对话、情节缺一不可。”
谈及奈米小说风格的独特性,方路表示“创作一定要跟保传统碰撞。作品的风格像人的气质一样,样貌是看得到的,气质是要靠感觉的。有些作者可能用打扮的方式去写作。”
“创作对我来说是两个人生:自己活着和文学活着,死亡就是分水岭”
“奈米小说的书写是从2013年开始的,刚开始写的时候我也没有分类,就一直写一直写。几乎每天要写一则,大概是200、300多字,有些很短。写了一段时间才分类,看回自己的作品才来规划,分成六个章节。第二本也变成这个风格。明年是第三本。”

得益于万物生灵的朝夕相处,又加之目睹了人世间的际遇和不幸,奈米小说自方路的身体里汩汩流淌而出。“有些人是要靠很多刺激物,我是没有。我是面对电脑,灵感就开始来了。”
严格来说,是汩汩流出的灵感和《星洲日报》的保安催生了奈米小说。方路的写作模式是白天写新闻,晚上写小说。“有一个分水岭,在疫情的时候。2020年3月之前所有的创作都是在报馆完成的。那时候家里没有电脑,常常在报馆写到凌晨两点多,同一个地方,同一个电脑,不能够太迟,一定要完成。训练了我一定要在某一段时间内完成创作,再慢一点保安人员会来催。”
在无数个寂静的夜里,报馆幻化为《倩女幽魂》中的兰若寺,妖气横生,一灯如豆。方路正气十足坐镇于书桌前码字,奈米小说缓缓流淌而出,白纸黑字,有人有魂。方路将这种现象归因为磁场作用,“发现是磁场的问题,写作的磁场。星洲的磁场刚好可以吻合我。”
从农历七月初一至农历七月十五,每日一篇“异小说”。方路幽幽地讲道,“7月是中元节,感觉是自然来的。其实这三年里面,每到七月灵感就自然而来,不是刻意的。那种感觉你推不掉的,不是制造出来的。”能够坐下来与鬼怪促膝长谈,方路确是现代版的蒲松龄。
奈米小说始终笼罩在雾蒙蒙、阴森森的氛围中,读时画面感极强,读者仿佛听闻芭蕉树下悉索有声,又像人叹气。小说中频繁出现以死亡为意象的题材,方路解释道:“因为死亡是人生最后的总结,是必然要接受的一种过程。虽还没到那个时候,就已先处理,是为自己结束之后留下一些温度。所以创作对我来说是两个人生:自己活着和文学活着,死亡就是分水岭。那是一种微妙的感觉。”他淡然谈论死亡的议题,眼里没有丝毫波澜,反而充满了向死而生的豁达、从容。
方路对死亡有着敬畏之心,对亡魂有着怜悯之情。他在第二本奈米小说《忧伤牛》的《无头魂》中写道:“母亲每次讲阴故事时都会强调,不是每一个鬼魂都是恶心肠的。”许是人的世界错综复杂,跟鬼怪在一起反而黑白分明。“奈米小说里很多有关于死亡的意象,皆来源于童年、少年的印象。有一些学者发现一些情节是可以串起来的,刚好从别的体裁反射过去。所以先读散文,有一个脉络,会更容易理解奈米小说。”读者在阅读奈米小说时可从方路散文中的个人经历发现端倪,“不可能永远告别,只能放下,用别的体裁发挥。”他一字一顿地说。

方路的奈米小说就像一个说书人在故事的高潮之处戛然而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众意犹未尽。又如一个端茶师傅穿梭忙碌,斟满的茶水将溢未溢,在众人的屏住呼吸中,一直到最后都不洒一滴。
《诗经·周南》有云: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意思是:让我姑且饮酒作乐吧,只有这样才不会永远伤悲。 方路的奈米小说立足于对万物生灵的尊严、价值关怀而创作,哀而不伤。就如同他在前两本奈米小说的自序中所写:“一瞬烟花。一瞬涉哀。”而对于文学来说,电光石火,一瞬便是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