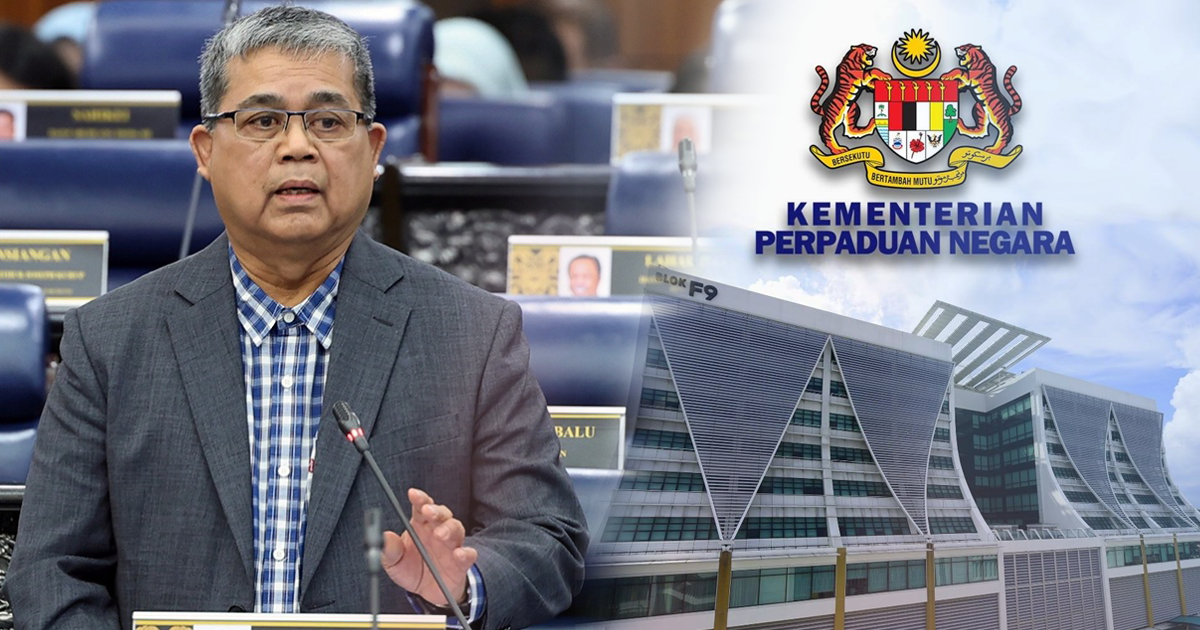“魔术不见了!”弟弟若涛来电,我一怔,不知如何反应,像忽闻久违的朋友骤逝,该难过吗?如果他多年未在生活中泛起半点涟漪,离开,就如点水飞去的蜻蜓。但魔术并非久违的朋友,他一直守在身旁,我把他从小养大,名字也是我取的——只是我许久许久没有和他好好相处,而且是有意识的拒绝相处。
魔术会来到我们家,是爸爸的意思。他口头上说希望有狗帮我看门,我倒觉得是他自己喜欢养狗,知道我会嫌麻烦,便找个让我难以拒绝的理由。当时爸和我住在两对面,既然狗要保护我,就该住在我家。我的确嫌麻烦,但这可是他老人家的意思,反正我也喜欢狗,从小就和狗一起长大。
我接触的第一只狗儿是伯恩山犬,那时我两岁左右,已经记不起来了,听父母说气候不对导致牠性情暴戾,不久就送走了。我对狗的记忆是从“英雄”开始的。英雄与我同龄,和魔术一样是狼犬,甚通人性。比如有一次他无意间推开门廊未上拴的小门,小朋友们兴高采烈的叫道:“狗狗会开门!”英雄看大伙高兴,竟然再推一下,大家鼓掌,他又再表演。还有一回我被妈妈责骂,躲到屋外一角哭泣,英雄轻轻靠近舔舔我的手背,静静陪在身边。
后来我们饲养了过动的狗儿“班比”,常常横冲直撞,我们兄弟俩个子矮小,特别害怕。每当班比冲过来,英雄会用身体阻挡,咬着他的脖子制伏在地上,英雄果然英雄。英雄在我十二岁时病逝,我对他最后的记忆是某日放学回来,见他趴卧昂首、双目通红,那时他已病了好些时日。翌日放学,就再没看见英雄,妈妈说他病死了。回想起来,前一天还看他精神抖擞,也许是父母和兽医决定让英雄安乐死吧,只是无法向年幼的我解释。
其实对英雄真正的最后记忆,是在他死后,那时我已上初中。某个大白天我如常在书房做功课,窗外似有黑影一闪,我猛地抬头,仿佛看见一只狼犬纵身跳开。我认定是英雄回来探望了,却又因为天国的规矩不能让我瞧见,所以在我抬头之际匆匆躲开。我为此事写了一篇《忆亡犬》,参加校内的散文比赛得奖。
英雄走后,家里又饲养了品种不明的“幸运”和“美丽”,是兄妹。美丽活泼吵闹,幸运则相反,有点呆。一天我们突然发现兄妹俩联手制伏一只矮小的棕色狗儿,也不知道他是怎么闯入庭院的。那狗儿样子精灵,身型近似腊肠犬,我们一看就喜欢,便收养起来,我为他取名“精明”。幸运和美丽很快就知道主人特别关照精明,再没有欺负他。
精明也很通人性,和我很要好,常常一起玩耍。门廊内本来是狗儿禁区,但他个子小,可以钻过栏杆的空隙,我们看着他可爱,也没有制止。我坐在地上陪他玩时,他喜欢钻到手臂底下让我搭着他的肩。我家出入都得用钥匙,久而久之精明一听到钥匙当啷当啷的声音,就会守在门口。
数年后某日,精明不知怎么从后门钻了出去,滑落屋后的大水沟。那里野狗群居,各路野狗以为精明抢地盘,一瞬间群起攻之,还好园丁发现,拿着锄头冲下去把野狗赶走,救了精明。精明全身打颤,我察看他的伤势时不小心碰到后腿的伤口,他回头就咬,我及时把手抽开,他看清是我了,才让我为他涂药。这是精明做的第一件蠢事。
多月后的某个清晨,精明在大门打开时冲了出去,被车子撞死了。这些年来同样的大门开关无数次,他从未越界,也许他终究怀念流浪的自由。这是精明做的第二件蠢事,也是最后一件。我睡醒时妈妈告诉我精明的死讯,我在她怀里痛哭。
美丽后来被贼毒死,幸运很幸运,逃过一劫,大概是呆呆的没有威胁到贼人吧。我不记得是精明拿幸运当榜样还是幸运模仿精明,有一次大门打开时幸运逃了出去,我眼睁睁看着巴士撞上他,他跌进车底在轮子间滚了几圈,从车尾窜了出来,飞似的跑回屋内,从此再也不敢出门。他看来分毫无损,多年后看兽医时才发现头骨歪了些。幸运是老死的,真幸运。
以后好久都没再养狗。我们从独立洋房搬到半独立式,为的是地方小容易打理。爸爸本想建大房子,让我们兄弟俩成家后也同住。地买了,蓝图画了,连模型也做好了,扰攘年余,他转念又想孩子未必要和爸妈住在一起,况且将来两老要打理这航空母舰般大的房子,那是无休止的恶梦。楼上要呼唤楼下,大概没扩音器不行。他毅然放弃了经营了整年的计划,改住小房子。
我本来不喜欢爸爸经常改变主意,让人无所适从,他说:“发现不对或有更好的安排,那就改呀,难道看到墙壁了还硬把头撞上去吗?”我在多年后才体会如此浅显的道理,有的人就是为执着而执着,听说某友的父亲坚持盖他梦想中的航空母舰,劳民伤财之余,为了内外设计以及将来生活的安排,和妻儿媳妇争闹无休。竣工后才发现真的是把航空母舰建在陆地上了,实在用不着,遂又为“我早就说过”等言论再吵一通。
爸妈千挑万选找到了喜欢的房子,坐落公园旁,热闹的八打灵市中难得的清幽。屋主不卖,爸爸急了,愿意付比市价高的价钱。高多少呢?我本来没过问,八个年头过去我着手售卖这房子时,市价比当年的买价还低,我笑说当时是另类“逼迁”了。
爸爸贷款给我买下对面的排屋,我迁入新居,虽近在对面,老家还是少了一把声音,弟弟又不多话,也许爸爸觉得无聊了。当年他主掌报馆日日冲锋,退休后的清闲日子也并非不享受,但总该有些事情寄托吧,于是想到了养狗。我是这样推想的。
“你家里人少,应该养狗看门才好。”爸爸说。
我假装拒绝:“养狗麻烦,况且我不是装了防盗系统了吗?”
“那不一样,有狗贼会比较怕。”
我总是拿我爸没法子,答应他的那个星期,他说就领着大家到士拉央的狗主家去挑选小狗。魔术小时候是全黑的,只有半只手臂大小,在众狼犬中最亲近人,爸爸就相中了他。爸和狗主讲价,狗主分毫不减,爸也不坚持,就把魔术买回去。

那是我第一次见识狗儿的证书,祖宗三代都有记录,比人的报生纸还清楚,血统纯正。既然是我的狗儿,名字便由我来取,当时我初学魔术,就干脆唤他“魔术”,把犬业协会的手续办好,报上新名字,还得向市议会申请执照,以免被捕犬队当野狗捉走。
当晚魔术住在新添的笼子,成夜呜咽,想来不习惯受困,只好放任他在客厅行走,新笼子就只用了那么半次。我家向来把狗养在户外,次日魔术就在庭院活动了,爸爸来探望,喜欢得很。一星期后,爸爸语重心长的说:“魔术好像吵到你们的邻居了。”
“哦,是吗?怎么没听说?”
“他们当然不好意思当面说。而且,你家院子小,魔术长大了会需要更多空间。”
“可是,他现在还小。”
“趁他还小,让他适应单一环境就好,半途转换环境,他反而适应不来。”
“那怎么办?”我装出一副六神无主的样子。
爸爸摇摇头说:“只好养在我家了。”
“可是,我需要魔术看门啊。”
“小狗能看什么门。况且,你装了防盗系统啦!”
魔术从此就住在爸爸家了,不过他始终是我的魔术,我到宠物店买让他磨牙的玩具,到书店搜罗关于饲养狗儿的书籍。虽说我们养狗多年,可是从未正式学过如何训练狗儿。原来狗儿在其地盘内必须要有首领,而这首领不一定就是主人,如果主人威严不足,狗儿会自认首领,把“主人”当成“马仔”,从此后患无穷。
爸爸才不理会这些烦人的理论,嘱我处理。魔术长得很快,三个月左右吧,就渐渐没了小狗的可爱模样,很后悔没为他多拍几张照片留念。最早的训练是这样的,我每天用半小时和魔术坐在院子一隅,他要站起来,我就把他压下去,久而久之,他就把能限制他行动的人当作首领。
接下来魔术就得上最重要的一课:“来”。不管他在干什么闯什么祸,只要他能听懂“来”,就可及时制止。训练狗和训练人差不多,不外乎赏罚,只不过人有时要权有时要脸有时要钱,狗就只吃狗粮,有时摸摸头就很高兴了。懂得“来”了,我还教会魔术坐、趴、等、装死、翻滚等等。魔术很聪明,尤其让我骄傲的是他学会“等”,大盘狗粮放在面前,主人不点头他不会吃。这殊为不易,动物依随本能,饿了就该吃,能听话克制食欲,那是超越动物的界限了。
印第安人传说很久以前动物和人类平等,后来天神决定区分他们,大地裂开,一边是人类,另一边是动物。裂缝越开越宽,在几乎不可逾越的刹那,狗跳了过来,选择和人类站在一起,成为人类最好的朋友。狗是始终如一的忠诚,我们任何时候回家,魔术总是兴高采烈的摇尾相迎,任何时候和他玩耍,没有不尽情奉陪的。
魔术住在爸爸家,和爸相处的时间始终比我多,于是他接手训练魔术,十分享受其成果。魔术在爸爸的调教下学会了“三连跳”,我觉得不可思议,因为狗总是本能的做最简单直接、最不费力的事,要到某个目的地,循直线走去就是了,要怎样才能让他跳呢?
在学会三连跳之前,要先学会基本的“跳”,爸爸拿着大呼啦圈,命令魔术跳过去。魔术如果会思考,当时的潜台词一定是:“干嘛?从旁边走过去不就对了吗?”一般情况下狗的确没有跳的理由,可爸爸就是坚持,也不记得耗了几天,魔术终于弄懂了爸爸的意思,跳过呼啦圈,爸爸高兴极了。
能跳一次,大概就能连跳几次吧?爸爸在庭院搭起三个横杆当作障碍,命令魔术在一端等着,自己走到另一端,对魔术命令道:“跳跳跳”。魔术绕过横杆信步而来,爸爸把他牵回原位,再试一次。这回,魔术从横杆底下钻过来。爸爸很快就想到了怎样和魔术沟通,他把魔术牵回起点,和他一起跑,到了横杆前手一提喝一声“跳”,魔术立刻就学懂了。真是言教不如身教,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爸爸几乎每天都和魔术跑步,我不时也和魔术到公园玩。魔术喜欢玩球,尤其是捏下去会发声的小球,他可以不停的咬,挤掉了里头的哨子还不甘休。他会把抛出去的球衔回来,却不肯归还,径自趴到一旁享受咬嚼的乐趣。带魔术出门最怕遇见猫,那大概是唯一能让他抓狂的事,四十公斤的大狼犬发足追猫,你得使尽全身的力气才站得住。
话说魔术童年只有猫般大小时,有一天散步遇见野猫。野猫对他丝毫无惧,作势攻击,吓得小魔术转身就逃,还得让主人出手帮他赶猫,狗的尊严荡然,和猫的梁子就这样结下了。他们的恩怨常常让我们头痛,野猫最喜欢在墙头斯斯然走猫步,惹得魔术狂吠不休,照理说猫应该闻声而遁才是,但他们赖在墙头,似乎有意戏弄无法攀墙的魔术,最后还是要劳动我们拿扫帚赶猫,这梁子又结得更深了。
可是魔术除了对猫凶悍,对所有人都友善得不得了,无论是来派报的、修水管的、装修的、老朋友、新朋友、找错地方的陌生人,一律亲切待之。魔术巨大的体型还能唬一唬人,稍加相处就发现他一点防范之心也没有。如果他是一只玩具犬也就算了,作为守门者就让人啼笑皆非。
装修工头阿成的样子浓眉大眼凶神恶煞,而其实为人温和。一天爸爸对阿成说:“帮个忙。”
“什么地方要修补呀,周先生?”阿成问。
爸爸顽皮的笑笑:“不是,帮忙打我。”
“什么?”阿成傻了眼。
“对,你在门口假装和我拉扯,作状要打我,记得样子凶狠一点,我想看看我的狗有什么反应。”
阿成答应合演一场戏,当作客户服务吧。后来爸爸得意的告诉我们,魔术看见他惊恐拉扯的样子,咬牙切齿了,这下证明了魔术还是懂得护主。他们怕魔术当真攻击阿成,立刻转笑脸拍肩膀, 魔术大概多少被弄糊涂了。
对魔术的测试还有一次,爸爸带他到公园,抛球让他追去,自己躲到树后偷看他找不到主人慌张的样子,待看清楚魔术果真在意主人,才出来呼唤他,让他扑到怀里。魔术当真是家里一分子了,客人造访,十之八九会惊叹:“好大!”我们会暗自骄傲,然后吩咐魔术让开,免得吓着了客人。一回爸爸的朋友看魔术体型健硕个性沉稳,认为品种优良,建议带他去配种,酬金还不错,爸爸几乎就要答应。
“魔术算不算‘做鸭’?”妈妈这样问起。
“我们是不是就成了‘龟公’?”若涛很逻辑的跟进。
“还是推家庭成员下海的‘龟公’。”我进一步推想。
本来是说笑,但爸爸好像挺在意,次日就回拒了。魔术一直都是“处男”,所幸他始终自律,每次到公园遇见其他狗儿时,没有发生什么让我们尴尬的事情。
这公园的土壤种满回忆,我们在这里和魔术奔跑过、玩耍过,树叶还呼吸着当年的笑闹声。有一年的体检,我的胆固醇指数难得下降,爸爸说这都是魔术的功劳,让我们的运动量增加,收养他是对的,我也乐于附和。不记得是否就那一年,爸爸没做体检,到次年,发现癌细胞已经扩散。
看过了专科医生,爸爸问家庭医生的意见,他略带笑意:“那我还可以抽烟吗?”
医生皱眉,反问:“什么?还抽烟?”
“减少成一天一支,可以吧?”爸爸半开玩笑的说。
“你这病抽烟是主因,就不要抽了啦!”医生没好气。
“好好好,不抽了。”爸爸还是笑笑。我觉得爸爸不是单纯的开玩笑,而是不甘愿承认自己多年的习惯造成生病,祖母不也是烟瘾奇重,邓小平不也是,都是年过八旬老死的,况且他近年来已逐渐减少了。
爸爸半点时间不浪费,他从书店和网路收罗癌症的资料,很快就决定谢绝亲友的偏方,专注于医生制定的疗程。我们兄弟俩轮流送他到医院接受化疗,他总是没要我们陪,过后才接他回家。“没什么”他说,更辛苦的是化疗后的副作用,虽然新药已不会使人呕吐,还是常让他抽嗝不止。头发开始脱落时,爸爸才没耐性等待一些必然的结果,索性剪了个光头。
“光头了魔术还认得我吗?”“当然认得。”明知爸爸开玩笑,我还是回答。他生病期间,已没气力和魔术玩耍了,因为抵抗力减弱,医生告诫爸爸减少外出,当然也不要接近狗只。
化疗效果甚好,癌细胞受控制,下一步是在新加坡动手术切除部分病变的肺叶,也顺利完成,肺癌算是治好了。多月来重重阴霾,我们层层拨开,终于见到曙光。爸爸回到家中休养,精神尚好,但身体十分虚弱,因为肺叶部分切除,加上手术失血供氧不足,连走路也不能,只能躺着,复原需时。
既然缺血缺氧,爸问医生输血可否,医生答应让若涛输血,可是效果有限,爸爸还是大部分时间躺着。那时,魔术已经多月没和爸爸外出了,他知道爸爸就在屋里,可是怎能明白生病这回事呢?狗儿不会控诉,始终静静在门边守着。
有一天突然接到妈妈的电话,说爸爸连躺着也呼吸困难。我赶回家载爸爸去医院,他起初还拒绝,在我们坚持下才答应,当时他寸步难行了还不让我们扶,但那也不是不可理喻,因为爸爸本来生龙活虎,骤然得病,经过多月煎熬原以为康复了,却又得修养多时,这下子又发生呼吸困难的毛病,怎不气恼?
在车上,爸爸吩咐:“不要开太快!”这是爸爸对我说的最后第二句话。
到了医院,医生为爸爸戴上氧气罩,顿时舒服了许多,对我们说:“和刚才比起来,感觉像天堂,你们先回去吧。”这是爸爸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也是我最不该听话的一次。当晚情况有变,爸爸的呼吸能力下降,医生得到他的同意,让他昏迷接上呼吸机。待通知我们到了医院,他已在昏迷状态,无法再对话。
医生说爸爸的肺部有细菌感染,要在呼吸机的帮助下待机能恢复。下来的日子我们只能盯着仪器显示血液中的含氧量,始终不见起色。他久卧床上,医生嘱我们帮他按摩手脚,我才意识到少年以后甚少握过这双牵着我成长的手,现在握着爸爸还知道吗。后来,我们连气功也姑且一试。最后,接到医院的电话,要我们准备。
准备什么?有的事情是不可能准备的。我可以一星期前告诉你,一年前告诉你,十年前告诉你,五十年前告诉你,到了那个关头,你依然要崩溃,而且你必须崩溃,不然你怀抱着那么多的悲痛,刹那间灵魂就会如内爆的星球般消失,徒留永恒的黑洞。
我越来越得承认,我心目中的巨人不会再站起来,三十多年来我生命中的船长,终于要扬帆独航到天际那不容回航的国度,留给我指南针和共同画下的海图。而我下来的旅程,是航在自己的泪海上的。
从盖上一方白布到撒下一撮泥土,中间的事情我记忆模糊。我不记得是怎么告诉魔术爸爸过世的事,在心里头说的吗,还是说出口了?魔术没有反常的表现,我相信他心里是知道的,狗儿有狗儿的哀悼方式,就是静静的守着。
收拾爸爸的遗物时找到一个从来没用过的烟灰缸,是我小时候送他的生日礼物,中间画着可爱的卡通,写着“戒烟”。我常想如果当时我不断唠叨,他会不会就戒烟了呢?我并没有唠叨,我原以为爸爸当然有自己的想法,儿子不能动摇什么。可是现在我知道,如果当年我坚持,爸爸很可能会听,儿子要我长命百岁,怎会不听?
如果啊当年我坚持,可那是回不去了的如果,回不去了的当年,我却对因果有了更深的体悟。我开始做运动,克制饮食,我在心底答应爸爸要照顾好家人,那就必须照顾好自己。从此我得扛起许多新的责任,从前事无大小都可以请教爸爸,现在得自己决定、自己承担,再不能推卸说是爸爸的意思。有一晚,我梦见爸爸,就那么一次,他对我微笑,转身就走。
若涛上班时妈妈在家独处,太孤单了,爸爸刚走,我们不放心。于是我建议搬家,找一间稍大的房子,让妈妈、若涛和我一家同住,妈妈就不会觉得寂寞。我们找到适合的新居,可是新社区没有围篱,不许公开养狗。我们把魔术养在地下室外的空地,对一只狼犬来说空间嫌小,跨不到十步就踏遍了,能补偿的只有不时带他跑步,可是附近没有公园,也不能放任他奔跑。
生活中的杂事渐渐侵蚀了我的时间,照顾魔术的担子落到若涛肩上。有一段日子,我的书房设在地下室,魔术就靠在落地玻璃窗外,安静的陪着,我偶尔望望魔术,一种亏欠的感觉淹没心头,在排山倒海的记忆来袭前,我关灯上楼,让魔术暂时消失。而身为魔术师,岂不知道消失的物事,从来只是被隐藏起来罢了?
也不是没想过把魔术送人,可是他是一头老狗了,没谁要收养,况且我们始终觉得有照顾他终老的义务。直到三年后一天,大荒电影公司进贼,遂有人萌生养狗的念头。大荒办公室是一栋单层住屋,庭院宽广,若涛和大荒同人相熟,于是献议让魔术迁居大荒。这本来一举多得,魔术重得宽阔的空间,大荒有狗看门,而我们也不觉得把魔术送走了,感觉上还在自己的地方。
显然,魔术的感觉和我们不一样。
“魔术不见了!”大约一周后,突然接到若涛来电。后来听见这消息的朋友总会问:“怎么不见的?”这问题我没问起,魔术是自己走了,至于在什么时间从什么洞口,不重要了。邻居告知最后看见魔术的时间,我们开始搜索,循地图走遍附近每条街每个公园。我总期盼在下个转角会看到黑影一晃,像当年看到窗外的英雄般,就找到了闲逛的魔术,而那隐约的恐惧始终挥之不去,生怕在下个转角看到的竟是当年的精明。
魔术自小被养着,除了狗粮什么都没吃过,没有在城市求生的经验。我们猜想,魔术会不会想念老家了?回到那最初的公园找了几遍都徒劳。我们联络宠物协会、市议会、发传单、发电邮、上部落格、上网站、上论坛、上面子书,始终没有消息。
魔术,仿佛魔术般的消失了。
魔术原来是一道魔法屏障,一直为我遮挡着那些深埋在地下室的情绪。魔术终于老了、累了,魔法用尽后,他选择消失。英雄病死,美丽被贼人毒死,精明遇到车祸,幸运老死,都是一路走来,而魔术,是我放弃了他,选择在自己生活的分秒中追逐,最终他也放弃了我。那第一时间守在门口迎你回来、任何时候都只因为你存在而快乐的狗儿,那全世界最忠诚的朋友,你能想象被全世界最忠诚的人背弃的感觉吗?那是因为我有多么的不堪啊!
“狗能上天堂吗?”一部电影中的老人牵着老狗,怯怯的问神父。
“不能,狗没有灵魂。”神父歉意的说。
老人失声痛哭。
忽然我是那个老人。爸爸离开,魔术离开,我紧系着他们的心被撕下两瓣血肉,痛醒了我的无知。爸爸让我更珍惜时间,而这狂热的追逐啊,让我选择忽略魔术,满心以为自己权衡轻重,终究能心安理得。然而已扛上的责任岂是说放手就能消失呢?魔术是家中一员,陪伴退休的爸爸和我们度过快乐的时光,我却没有让他在有限的余生安然度过。
张永修问,会不会是一种告别?有的宠物自知大限将至,会自行出走不让主人看见。我想不是,魔术健康很好,却让我联想离开是否最终极的忠诚?他主动使我无暇承担的责任消失,然后以那必然的愧疚告诫我,我再承受不了身边的人受伤或离开。消失的魔术,想让我的世界亮起来。
我还在等待魔术的消息。如果等不到,只祈望有一天,再让我梦见爸爸在最初的公园。他依然微笑着,也许看见我了,也许没有,他往那遥远的天际抛出一粒发光的金球,然后和魔术一起追飞而去。
后记:整整一个月后,大荒的同事在附近遇到邻人遛狗,狗儿十分眼熟,一问之下,恰好是在一个月前收养的。当时夜深,他在雷雨中遇见仓皇无助的魔术,他把车门打开,魔术毫不犹豫跳上车。他给魔术取了新名字,后来魔术听见“魔术”也不会回应了。
本来安排要把魔术归还大荒,可是魔术在邻人家快乐,他们也十分疼爱魔术,因此打算让魔术长住在那里。几天后,我正盘算着何时探望魔术,若涛忽然来电:魔术死了。前一天好端端的,次日一早就不动了。我再看到魔术时,他看不到我了,当时宠物协会的工作人员把遗体从冰柜取出,新旧主人一同在雨中撑着伞,看着魔术下葬。
魔术魔术般的消失了,而所谓消失,从来只是被隐藏起来罢了。
编按:本文原刊于星洲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