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高度发展的时代,人类社会似乎已被高楼和灯光覆盖。此时,仍有人沿着化石与遗骸的线索,逆向追索时间深处。
林泽昇是古脊椎生物学兼动物考古学工作者,现为马来西亚古生物学学会会长。坐在人来人往的商场咖啡厅,他有了感慨:“我们再也不知道原始的地貌和生态。19世纪时,我们身处的这座商场是什么地形,身边有什么动物走过?”
这并非突如其来的好奇,而是人类理解自身的必要路径。跳脱人类中心视角,时间和自然的辽阔,终究教会人们何谓谦卑。
林泽昇对史前生物的热爱从小开始。那是一种纯粹的喜欢,他比喻:“就像现在的小朋友喜欢看视频。”
1993年,《侏罗纪世界》(Jurassic World)电影推出,风靡一时,也吸引了还在念中学的林泽昇。电影中,人类发现恐龙DNA,利用克隆技术复活恐龙;此时现实中进行的古生物学革命,正发现恐龙是鸟类的直系祖先。

尽管电影世界是虚构的,却在他心中埋下一个确切念想:原来还有一种职业,不是律师、牙医、老师或医生,而是古生物学家。只要从事这个职业,就可以研究史前生物。
高中毕业后,林泽昇远赴中国研读生物学本科,主攻古脊椎生物研究;而动物考古学就像是一把钥匙,为他的古生物探索之路打开更多可能性。
2000年左右,林泽昇从文献中得知,大马某些考古遗址曾出土动物遗骸。顺着这条线索,他主动联系婆罗洲文化博物馆研究馆藏品,也开启自身对动物考古学的志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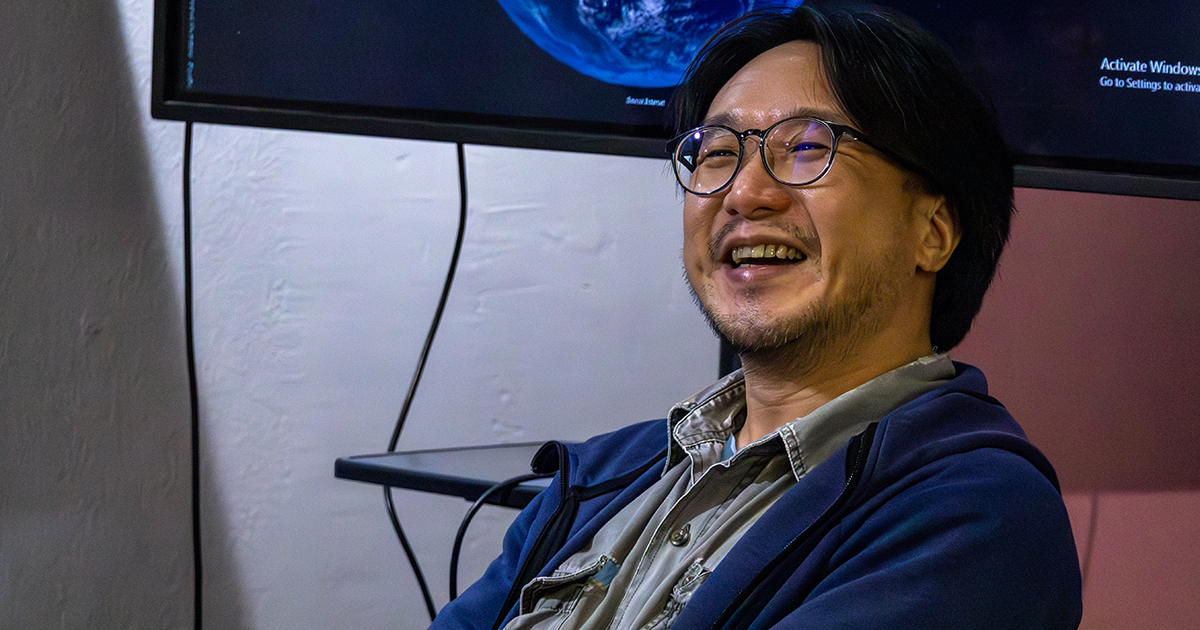
许多动物与人类居住环境紧密相连,被驯养、捕猎或与人类共存。理解它们的生命痕迹,有助于我们理解古代人类社会环境。只研究人类文物的话,没办法知道这些。
古脊椎生物,和远古人类文明息息相关。跳出人类中心视角,从动物线索切入,反而能更完整地理解人类社会演变。
学术研究、野外考察,皆紧贴东南亚土地
2017年末,林泽昇获得奖学金,前往英国剑桥大学进修动物考古学硕士学位。然而,他的研究步伐仍然紧贴东南亚土地——研究问题核心与相关动物遗骸集中在东南亚,奖学金条件也规定在婆罗洲文化博物馆进行馆藏研究项目。那一年,他是博物馆的研究员,也是客座研究管理员,主要考察尼亚岩洞发掘的动物遗骸。
几番学术路径延伸,最终将他带往马来亚大学。2020年起,他在马来亚大学地质系担任助理研究员,协助主导马来半岛石灰岩洞穴中的古脊椎生物学研究,并指导研究生开展田野调查。
走出学术屋檐,古生物学、动物考古学在最真实的土地上,何以实践?

野外考察,相当于渺小之身走进大自然的未知,却仍在里头探索一些答案。此时,对土地熟悉的原住民,就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
“考量安全性问题,我们会雇用当地受过训练、拥有执照的原住民向导。”尽管野外考察以科学研究为主,与原住民交流,却也是一种无形中的双向馈赠。“我们提供一些科学研究信息,他们则讲解当地文化与习俗。”
“我们会抓住这个机会,给他们灌输一些科普知识,让他们知道家园后面的山地其实不是鸟不生蛋的荒地,而是有科学价值的学术研究基地。当地的保护意识,就是这样慢慢地培养起来。”
在洞穴和山林中度过的时间,打扰过毒蛇巢穴、发现过老虎的新鲜足迹;团队结伴行动,互相提醒告知,大抵都算有惊无险。

如若发现动物遗骸,在带回研究室前,如何初步判断它们的物种与习性?“最原始的、几百年来延续的方法,就是直接靠眼睛观察。只要掌握动物身体部位的标志性特征,你就能马上分辨出来。”林泽昇表示。
至于稍难鉴定的骨骼碎片样本,就要带回研究室检验古蛋白。检验结果有二——一、精准确认物种;二,鉴定结果呈现负面,无法确定是哪一种动物。这个时候,只能大致将其归类为灵长类、哺乳动物或蛇类等较宽泛的分类。
马来西亚仍未拥有相关仪器与设备,一般上将样本送到国外大学,由当地研究团队协助操作。
布展、导览,让知识走入群众
问及马来西亚古生物与动物考古环境的困难,林泽昇表示,我国相关学术环境至少落后印尼、泰国等东南亚国家五十年。不仅研究人员数量严重不足,研究方法落后,资金投入也不充裕。
然而,资源上的匮乏不是最大阻碍,造成我国相关视野缺乏前沿性的误区在于——人们普遍认为大马没有古生物学与动物考古学的研究材料。相关误解将影响社会对学科的支持,因此,提升公众认知非常重要。

在婆罗洲文化博物馆任职期间,他不仅参与馆藏研究,也协助考古展厅的内容设计与布展工作。
“研究员的任务是最后把关。博物馆里的职员和年轻学者负责布展,研究员负责提供最新科学研究成果,并确保知识细节准确。”
他坦言对布展陈列并不特别理解,甚至称得上是“门外汉”,但仍希望博物馆能够将“高处不胜寒”的研究成果,转化为普罗大众愿意消化的知识。若兼具人性化与科学化,博物馆将成为自然与历史教育的重要平台。
然而,现实中仍面临不少结构性挑战——政府单位能否长期针对博物馆投入资源?若是私营化,公众是否愿意负担入场费用?这些都是绕不开的忧虑。
尽管阻碍存在,林泽昇始终怀抱豁达心态:“文化的事情急不来。希望从年轻一代开始培养,从他们这一代开始深植改变意识。”

快闪导览,也是轻盈且有趣的教育方式。林泽昇曾以大象骨骼特征为主题,在布特拉再也自然历史博物馆为公众讲解故事。一次导览20至25分钟时间,全程免费,行程也极其随性;只要他得以从研究任务中暂时抽身,便在社交媒体公布导览地点与时间。
“公众不用付一分钱给我,只需购买博物馆门票,就能约我进行讲解。”
简单的形式,让科学研究贴近公众,也让原本静默陈列的骨骼重新变成会说话的故事。
人、猿:人类和动物的界限,究竟在哪里?
如若得以返回过去,林泽昇最想看见哪一种史前生物的生活画面?
采访当天,林泽昇穿了一件印有动物图案的深色T恤,他要我猜猜看:“这是什么动物?”
“Orang Utan(人猿)。”
他点头补充:“现在只有沙巴有人猿,但我想要看见西马的人猿。史前人猿与现代人猿体型也大有不同,可以亲眼看看的话,一定对相关研究有帮助。”

人猿也称红毛猩猩,这种灵长类动物智力程度高,却也处于濒危状态。通过研究,东南亚各地的人猿甚至有不一样的族群、不一样的习性。
林泽昇对人猿的兴趣,源自一种跳脱人类视角的觉察。整个亚洲动物界中,与人类最接近的物种就是人猿——生而为人,研究自身族群往往带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盲区;抛开所谓先见,从动物视角切入研究,能够将不够全面的观看补全。
人与动物的差别究竟多远,抑或,人类本就是动物的一部分?
若是写作与演讲时提到动物遗骸,林泽昇会刻意强调是“非人类动物遗骸”,只因他认为——“人类也是动物,尽管这个观点并不被所有人采纳。”他相信,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的关系,还能用更广袤的视角定义。

“我一直在反思‘人’的定义。这种思考至少涉及两个面向,一是人类社会问题,二是文化的本质。”
性别二元或多元、战争、朋党主义……林泽昇认为,许多当代社会的难题,实则千万年之前的动物社会就有所端倪,甚至可以从远古动物世界得到解答。
古生物学与动物考古学的独特之处,在于把时间尺度无限拉长,每一个研究对象至少以千年、万年为计算单位。当看到当代社会的矛盾与危机,他不会只以内近百年的人类历史去衡量,而是将其放在更宏观的生命与生态框架下思考。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比如性别概念。特别是在马来西亚,身份证的性别选择趋向二元,只有lelaki(男性)和perempuan(女性)。”他指出:“可是如果研究动物或人类发展史,你就会发现性别这个概念是非常具有活动性、非常多元的。”
此外,人类自认有别于动物的特质之一,便是有文化。这一点也让他相当纳闷。
“黑猩猩没有文化吗?很明显有,动物学家珍·古德(Jane Goodall)就花上大半生在做相关研究。人猿没有文化吗?它们也有,生态研究从2000年开始就发现不同地区的人猿有不同习性,差异大到你可以把它作为不同的文化原型看待。”

当天空下起雨,人猿会就地取材搭起棚子,所采用的原料并非随意信手拈来,而是随着区域性有所不同。这些观察背后是文化的雏形,也像极了数百万年前,人类演化的最初轨迹。
把握时间尺度,危机也成为改变的机会
即使古生物学与动物考古学在未来高度发展,从表面上看,它们似乎没有直接的、务实的经济效益。石油价格不会因为相关研究降低,电费同样会逐年上涨,人们也依然要缴税。
“可是,作为基础科学,这两个学科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自身的历史、思考自身的存在。”
而一切理解与思考的核心因素,是“时间”。

古生物遗骸或化石在风雨侵蚀下仍然留存,它们让过去、现在与未来在同一个点上汇合。这一跨越时代的中轴线,正是深邃的时间尺度。
面对当下的人类社会危机,林泽昇认为,最重要的是思考如何把“危”转变为“机”,而非囿于狭隘的二元对立。即便古生物学本身,也有一段倾向于“危”的历史。
谈及19至20世纪的动物学家野外考察方式,仍是存在一定的争议性质。他们猎杀动物、获取标本用于分类学研究,同时也用于解剖学和生理学研究。对林泽昇来说,这些是当时唯一的研究方法,处于“无可厚非”和“惨不忍睹”并存的矛盾阶段。
“然而,跨过时代去指责他们,有失公允。当你伸出食指指责别人,三只手指就指着自己。”林泽昇认为:“他们的研究对我们有很大启发性。原生态野外调查、环境记录,让今人有一个系统脉络,去进行跨时代的了解和对比。”

对生命的尊重建立在尽可能全面的理解之上,才有机会脚踏实地自省与调整,而这种理解往往非常复杂。大自然浩瀚到足以把现在和过去连结起来,长河的两端有无数可能性,却让人们意识到世界并非想象中单薄、对立。
自然这个老人已经有数十亿年龄了,你难道不想认真去听他的故事吗?
人类只是时间长河中的一环,我们的所谓文明,不过是自然谱系中短暂而渺小的注脚。学会聆听自然的故事,或许正是找回自身位置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