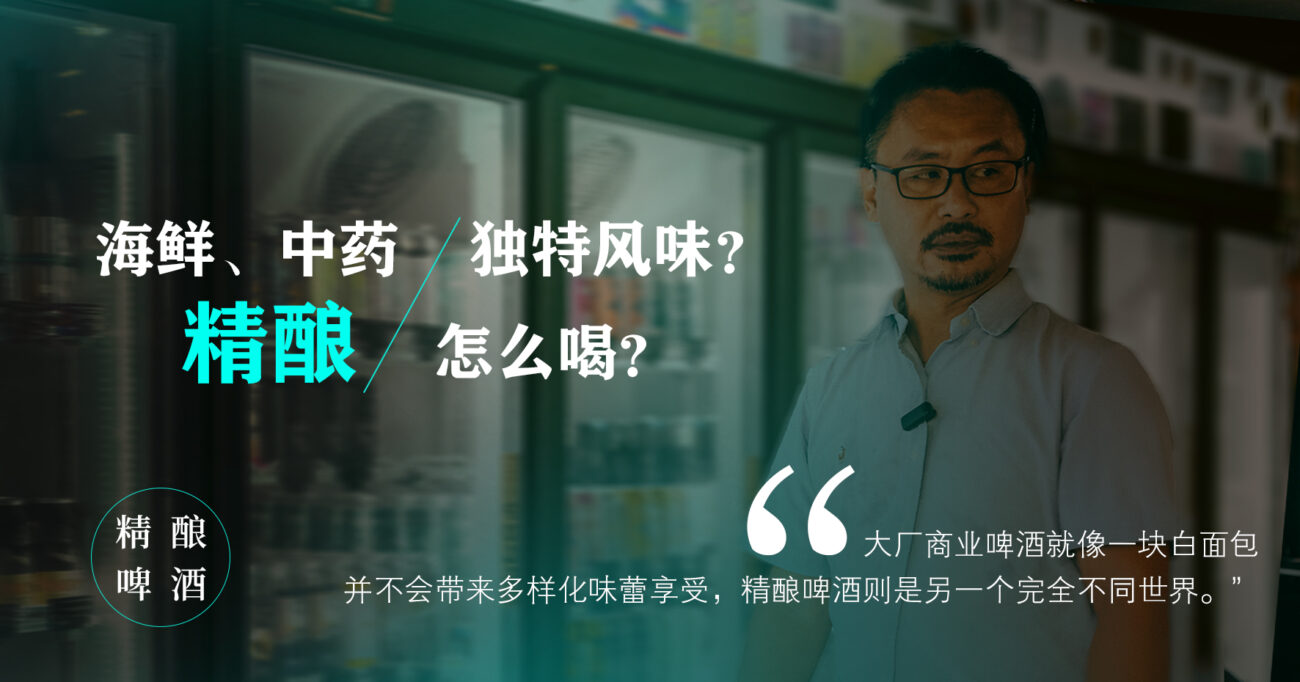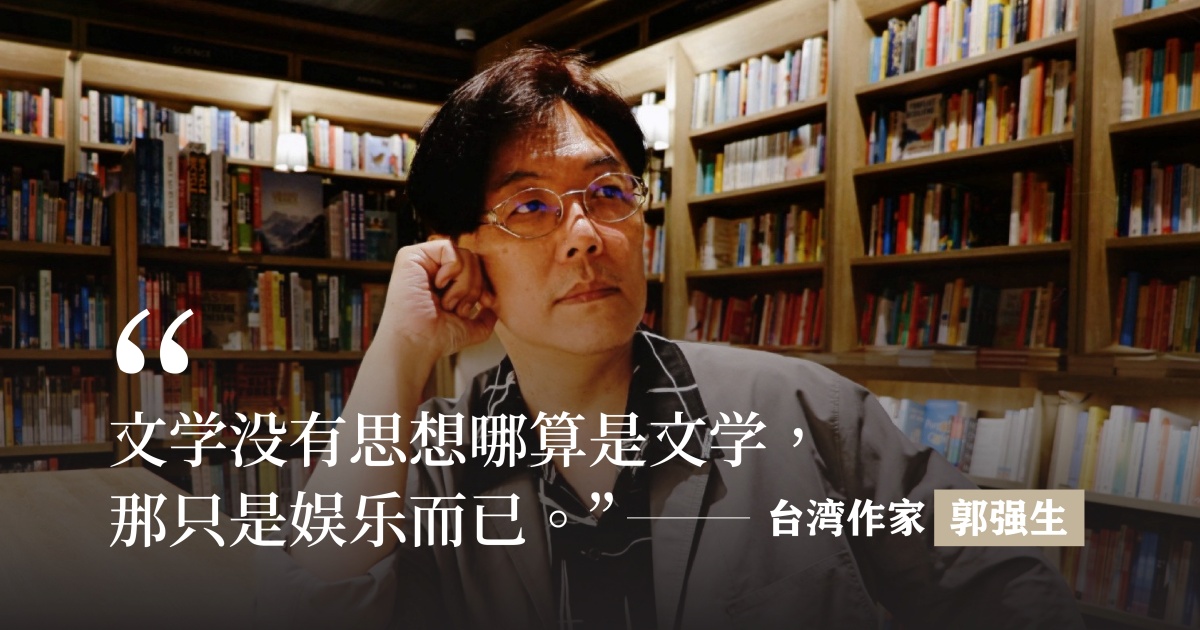近日很多人对马来人尊严大会似乎颇为悲愤。
我人生第一次认识到“马来人尊严”,是我十三岁的时候。那时刚从台北回到槟城不久,马来话没懂几句,从北海坐公车到大山脚上课。那时公车是上车付钱的,依地点不同车资也不同。司机问我去哪里,我不会说,就用英文答了,结果他说:“Ini Tanah Melayu, cakap BM la.”(这里是马来人的土地,说国语啦!)
因为他的声量很大,所以全车的人都看着我,后面还排了很多人,我当下觉得自己好像做错了,脸很热很红,就转身跑下车跑得远远的。后来我等下一班车,就给到终点站的车资然后跑到后面去坐。
在那个年纪,只要一离开华语语境,很多时候都处于这种失语的状态,希望自己不会遇到任何需要开口的时候。

再大了一点,就学会这个世界的“尊严”处处,如:在英国,白人叫你讲英文,不然“滚回中国去”,或在台北时,计程车司机问你“台湾人为什么不会讲台语”,在香港踢足球时,球场上的年轻人叫你“北归”,在英国的唐人街餐厅,大妈服务生抓住你问“为什么你说中文却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
有趣的是,这样的情况其实比他们对你友善的时候,更不令人尴尬。比方英国人说你的英文说得好棒啊,马来文演讲比赛评审表示感动,闭上眼睛听不出参赛同学原来是华人啊,中国人在你面前一堆同志同胞祖国。
再更老一点,就意识到其实都是场域和权力位阶的问题。在能力范围内,会制止那些强迫马来人讲中文的中国人顾客,或那些痛骂菲律宾和中国员工英文讲不好的新加坡人。
但我想我也不是完全无罪的,在某个忙碌的时刻,我一定也曾在一些英文不好的劳工面前,露出不耐的神色。年纪越大越要小心翼翼了,可能在一个刹那自己就压迫了谁,再也无法修复。
如我无法忘记自己十三岁时在公车上的那刻,那是我对老马统治的记忆,不是双峰塔,不是吉隆坡全新的国际机场,是自己心中那份无法抹去的孤独,如自己是多余的。
所以这两年,常常都想问(套个流行的句式):老马那二十多年做过的事,你是忘记了,还是害怕自己想起来?

只是可能老马也会说,他年轻时也受过白人或华人的践踏之类的。这个世界有十分之七是海洋,所以有太多的盐。
其实那些关于尊严的事,或尊严的聚会,就像一群无产阶级异男,在喝酒的场合聚在一起,喝了两杯以后,一起高喊要找回男人的尊严。
结果还没来得及做什么坏事,就气虚了,还是乖乖地回到老婆的身边吧。
不然若尊严到底,就真的只能抱着尊严痛苦一辈子了。
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