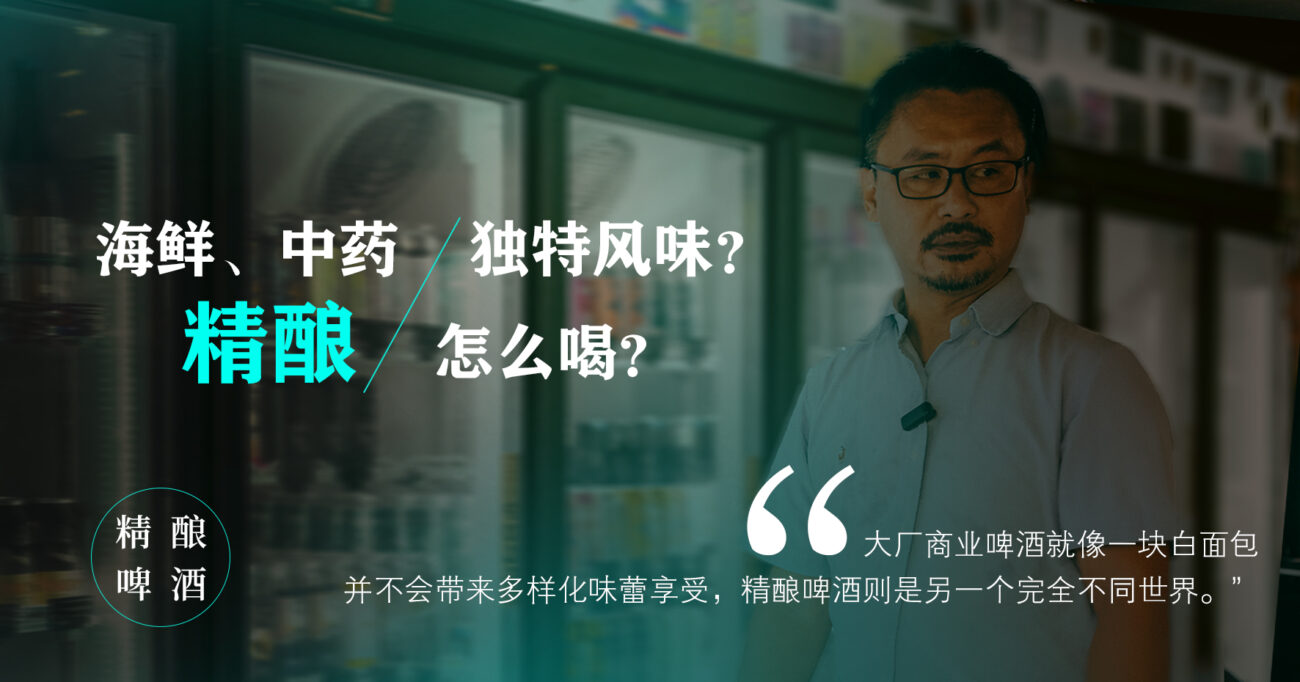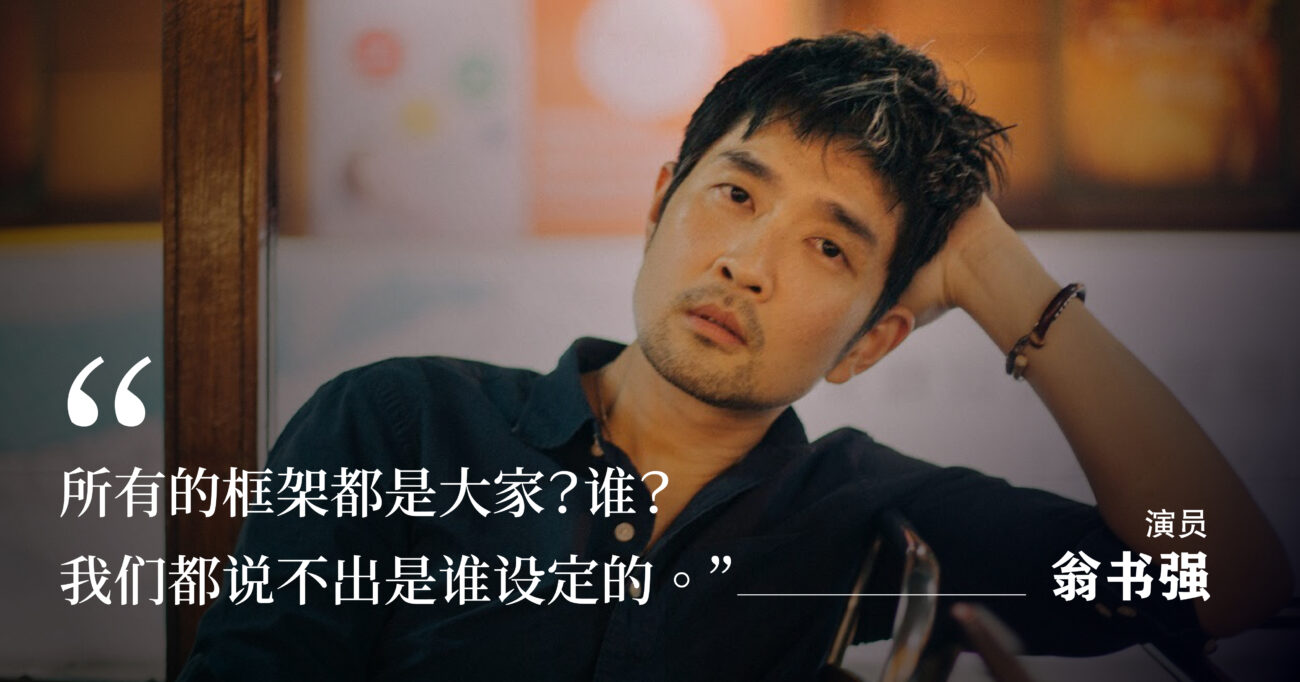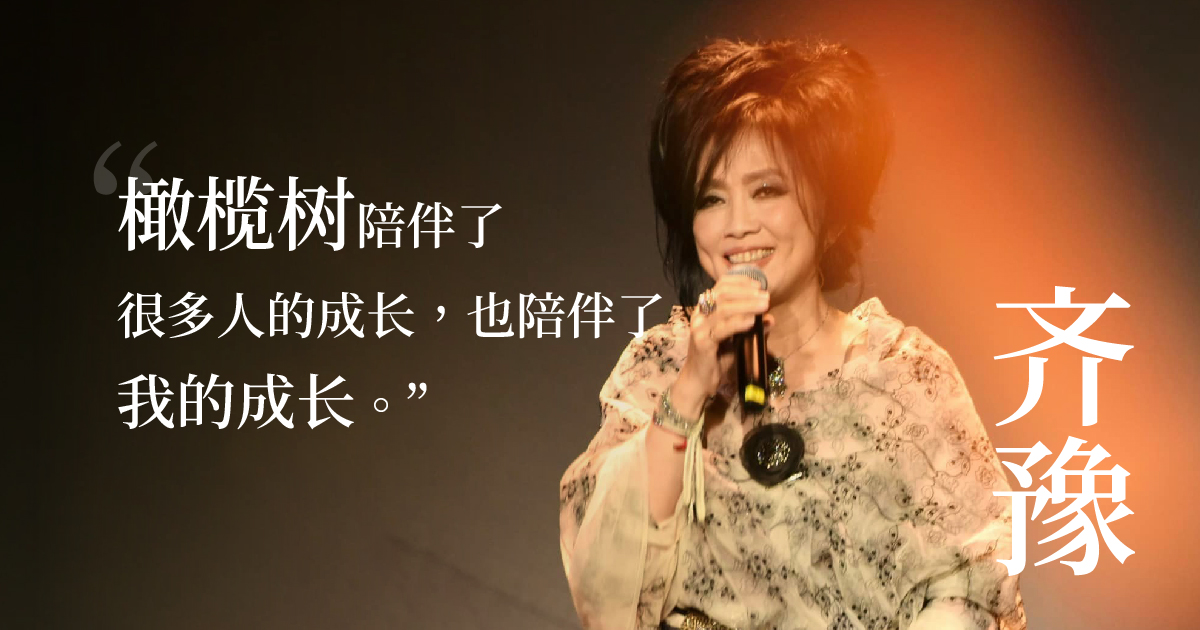砂拉越长屋沿河而起,每条河流亦有美丽的名字。位于柿伽洛尼亚河(Sungai Sekaloh Niah)一区,屋长(Tuai)长孙沃尔特·卡洛斯(Walter Carlos)笑说,一般上族人庆祝丰收,每日都会“喝至天亮”。一周七天,至少有三天醉倒呕吐,白天睡醒又继续挨家挨户探访。 适逢达雅节,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拿督斯里张庆信率西马半岛媒体造访砂拉越民都鲁长屋,体验传统伊班的节庆生活。
血液里的勇敢 猎首习俗消逝之后
伊班人有融在血液的民族性,那是勇敢与好斗的气魄,他们口中的“Keberanian”。从前在山林对抗野兽、捕猎,总是用尽身体的力量——喝酒、竞技与生存。除了祭祀活动,达雅节期间原住民也会在屋外斗鸡。
每年的6月1日及2日,砂拉越达雅族群都会欢庆丰收。Hari Gawai,意味节日与仪式;而达雅一词本是原住民的统称,含括伊班(Iban)、毕达友(Bidayuh)、加央(Kayan)、肯雅(Kenyah)、加拉毕(Kelabit)与姆律族(Murut)。
灯照不佳的长屋走道(Ruai),一位穿戴犀鸟羽毛头冠的长老站在面前,腰间挂着一把配刀。刀柄为木,垂落两搓黑色毛发。殖民时代,伊班人以猎首闻名;长老便说,人们腰间的配刀称为勇士刀,在詹姆斯·布鲁克(James Brooke)的年代以猎首为主。
相传,古老长屋门外悬挂头颅骷髅;眼前刀柄上两撮黑色毛发,便是他们猎杀后取下的头发。长老笑着要我们别怕,随着猎人头习俗消逝,如今绑着的仅是寻常发丝。伊班族勇敢、好战,传统习俗仿佛蒙上神秘面纱。
米灵仪式 祈求平安幸福
长老从腰间拔出的刀,刀锋锐利,无疑是一件武器。他说,无论是下田或劳动,日常生活都需要。
达雅节期间,伊班族进行米灵仪式。他们准备以竹片编织成圆形的托盘,铺一层香蕉叶,再把烟草、槟榔、米、烟丝、小饭团、爆米花、生鸡蛋、米酒等祭品摆放之上。

接着,他们抓起一只公鸡,口中念念有词,倒提着公鸡围绕祭品转七圈。此时,长老用腰间配刀在鸡冠划开一个破口,鲜血流出。拔出鸡羽毛沾血,最后往高处撒一把米,祈求幸福与平安。

时间的恩泽 虔诚酿造米酒
一间长屋,容纳了二十数户人家,屋长的房(Bilik)往往设在最中心。在我们与屋长(Tuai)长孙沃尔特·卡洛斯(Walter Carlos)聊天的当儿,喧闹包覆了整间长屋;就在房外,来自城市与伊班的两群人正“斗酒”。“呜——哈”,一杯杯顺滑的米酒(Tuak)下肚,没有任何一方示弱。屋外虽然下起了雨,但气氛正热着。
沃尔特拿出两瓶装在透明塑料瓶的米酒,要我们猜何者味道更好。左边颜色浅浊,右边较深;后来他揭晓,深茶色那瓶酿了一年之久,米的风味尽情释放。

然而,来自Rumah Branyai ak Siang的马修加里尔(Matthew Jalil)说,现在族人喝的米酒已不如以往多。一是酿酒难,许多米会在酿造期间耗损,首七天打开酿缸品尝一口,若是味道酸涩,便得整缸倒掉。
“太浪费了”,他说。若是味道正常,他们会继续置放约一个月,“两升的酒加入四升的开水,再加一公斤的糖”,这是马修最喜欢的比例。
探访了数家长屋,没有一户人家的米酒味道相同;或许,这便是自家酿品的独特魅力。一瓶瓶让人喝上瘾的雨林米酒,时间的馈赠之物,有的味道香醇,有的回甘。然而,他们相信一杯酒的幽微口感,往往能带出酿酒人的心境与个性。

酒能怡情、暖身,自然也会乱性。在达雅信仰里,酿米酒是神圣之事,他们祭拜天地与稻神,米酒更有召唤神灵的功能。一旦喝多,或许召唤了心中魔魇,一不小心就会打起架来,因而马修这些年已经少喝了很多。
原住民与长屋 命运共同体
如今,长屋已不再如想象中破旧,新式长屋以水泥砖头替代木板,有的还装有冷气、50寸电视机摆放客厅中央。他们逐渐与城市生活接轨,但住在长屋里头,命运始终相连。
刚从砂拉越飞抵隆市,便收获长屋失火的消息。就在民都鲁实巴荷鸟功长屋,午夜十二时火势从其中一间房蔓延开来。当时,居民正欢庆达雅,一瞬间人声鼎沸,在清醒与微醺中逃亡。
消防局收获消息第一时间出发,但抵达该长屋需要穿越一座油棕园。因位置偏僻,设备不足,几十户人家的安居之所,在短时间内遭火焰吞噬。
他们的生活,就在节日与欢声中烧成废墟。长屋原住民,与长屋本身,即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流着一样的血,共享民族的勇气,同时也要承担流离失所的风险。沃尔特的家,以水泥堆砌而成的新式长屋,也是因几年前在旧址遭遇火灾。他们被迫如游牧部族一般,寻找新的土地,再一次建构家园。
居住空间与交易场所

用电要小心,用水也费心。新新旧旧的长屋,每一间住着不同的人与灵;马修带我们走一圈他的房子,从客厅穿过厨房,最尾端是通往河边的后院。尽管在大街上已经有排水系统,但房屋里的水管还未建设——洗衣、烧菜、洗澡都需要走一段路到河边取水,这是他们的日常。
“从前生活穷,我们只能住在这里。”原住民多数以农耕维生,以前多种稻米,但马修表示现在都种油棕了。平常日子,他们带着工具下田;除了居住空间,长屋仿佛也是交易场所——每天从田里回来,他们带着各自的收成,便在房门前贩售。

“靠自己种的蔬果,一天还可以卖到二三十块”,马修说。以物换物,守望相助,这片净土仍未被文明侵袭;于此地生活的人,也总会找到自己的办法。
异族通婚,伊班小孩说中文
我们在雨天走进数间长屋,有的华丽,有的孤寂;木制高脚有之,水泥瓷砖亦有之。
长屋睡在时间之河,早已不如想象中拥挤,节日的喧嚣无法完全掩盖它的寂寥。抬头一看,蜘蛛网悬挂在天花板,每间房门上挂有牌子,刻着号码与主人家的姓名。而那些人去楼空的房子,也早已丢失了名字。
马修的家算是热闹,住着五个人,尽管他已有五个孙子,但留在身边的孩子并不多。有的去了城市发展,有的离开长屋,在市镇寻找更独立与稳固的房子。说起自己孙子的名字,有好几个是中文名——这些年来,异族通婚越来越普遍,伊班族与华裔或巫裔成家。
当地人说的“半菜”,指的就是混血孩子。他们体内留着两种血液,更在两种文化时空中成长。

穿梭在Rumah Luking ak Jebut长屋,迎头碰上一位长相清秀的九岁伊班女孩Louissa。她从美里来,在这里住了好几年。谈话半途,她突然说起中文,这才发现许多伊班孩子都会多种语言。家庭经济许可的家庭,更会把孩子送去华小升学。
后记:
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人与人的距离很靠近。穆斯林家庭坐在长屋一角,与伊班婶婶欢庆达雅节。雨越下越大,今天是无法看到斗鸡了。但临走前沃尔特送了一支米酒,那是神灵与族人的祝福。
我想我会记得他,这位伊班少年,双眼通透如琥珀,眉目间有一股神话般的清澈。
沃尔特的全名是Walter Carlos luang ak James,我们花了好一些时间拼写。他解释,伊班人喜欢把父亲、祖先的名字都放一起,如河的支流汇聚成海。他们相信,只要一直携带着先辈的名字,所有好的习性都会流传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