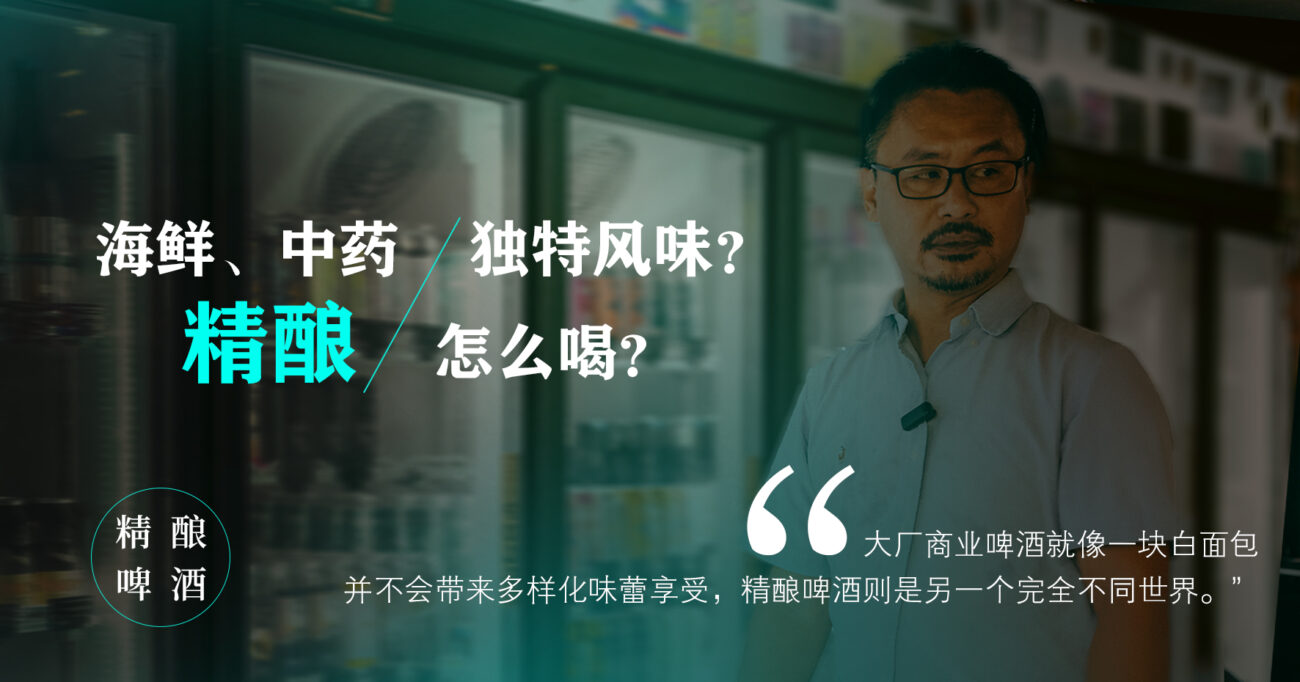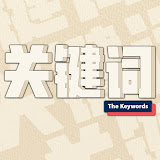《花样年华》里,周慕云眉头微蹙,神情凝重地咀嚼一碗云吞面。金鱼尾巴的云吞,表皮薄如蝉翼、晶莹玲珑。内里虾和猪肉抱成一团。轻轻漂浮在碗中。一缕缕银丝面乖巧伏在云吞旁,佐以鲜亮的油菜。碗中的花样年华,热气蒸腾。
《花样年华》外,周慕云的原型——香港作家刘以鬯在50年代作客南洋,于1953年任吉隆坡《联邦日报》总编辑。这位苦闷的南来文人,将自己称为“卖文为生的稿匠”。南洋的天气,指缝间好像能捻出水珠。人也被浸湿成一粒云吞,白里透红。他会不会在人声鼎沸的摊贩,蹙着眉,精打细算,将一千字的稿费换算成数十碗云吞面。
刘以鬯生于上海,1948年移居香港。正值而立之年的他,靠一支笔在异乡讨生活。他卖文售字,并饶有兴趣地计算:在香港,一千字的稿费可以买多少碗云吞面。

他在香港一向负责副刊编辑,副刊地位在当时的报馆并非主要居首。他在小说《酒徒》中宣泄自己的不快,鄙夷现世“文章的好坏取决于有无生意眼”。对媚俗的文章嗤之以鼻,并称其为“心智十分不平衡的知识分子用自我虐待的方式去求取继续生存”。郁郁不得志,遂南下新马。

王家卫是最懂他的人,细嚼慢咽他的小说《对倒》,消化为电影《花样年华》。周慕云也与刘以鬯的人生轨迹有重叠之处。王家卫镜头里那个吐着烟圈的周慕云,是报馆码字为生略显惆怅的刘以鬯。

遥想刘以鬯在50年代的吉隆坡,报馆的风扇像哑了嗓子,发出吱呀吱呀的哀怨声。他伏案写作,写“盖着亚答的浮脚厝”,写“深夜的热带风”,写“马来姑娘美得像一朵淡黄的槟榔花”。蓦地抬起头,眼睛里也慢慢升腾起雾气。一场椰风蕉雨将至,淋湿全部的记忆。
“向卖茶妹要两杯羔呸乌”
在南洋的潮湿天气里,在摊贩的氤氲热气中,在他用筷子挑起银丝面的那一刻,会不会想念上海的小馄饨?
又或许南洋的美食已令他乐不思蜀?
在《星加坡故事》里,刘以鬯写道:“我甚至有意尝一尝风味别具的马来饭,但是陈君怕我吃不惯,偏要拉我去吃上海菜。”陈君是他在新加坡报馆的同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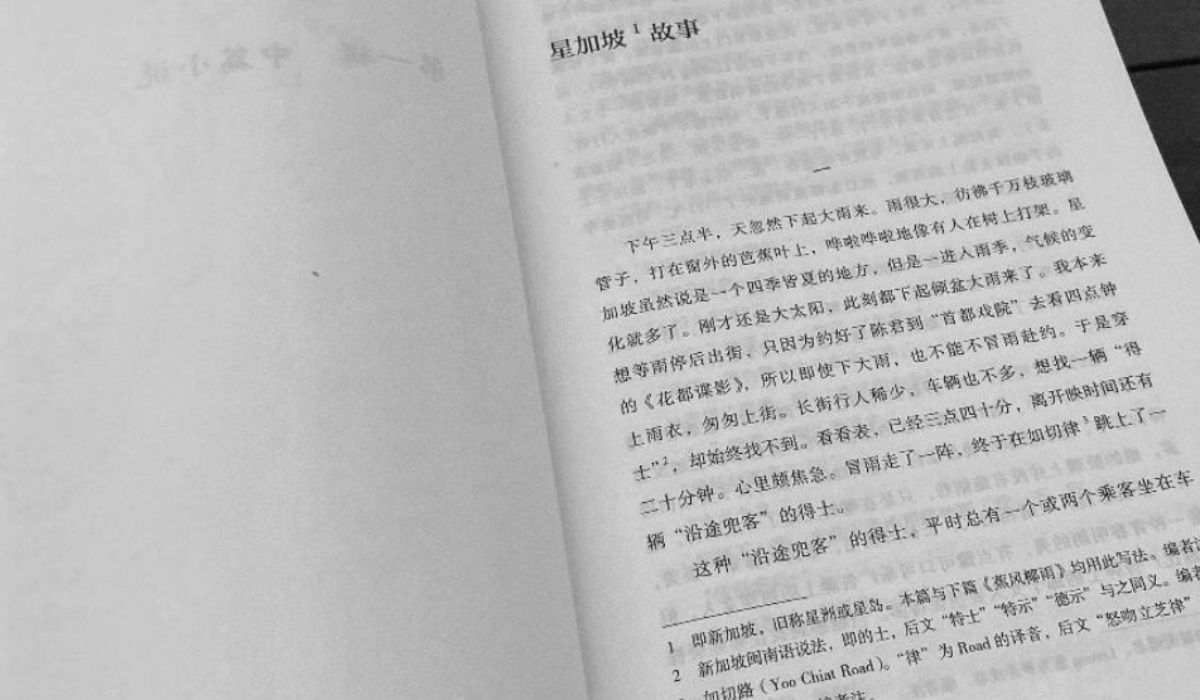
到了吉隆坡,他也定会如《星加坡故事》中那样“向卖茶妹要两杯羔呸乌(Kopi O的译音),也许会放肆叫上活色生香的马来饭,红艳艳、黄澄澄的酱汁,异域香料的迷幻香气,一扫煮字疗饥的苦闷。
刘以鬯在50年代的吉隆坡,将咖啡店音译为“羔呸店”。欣赏不来烈日下奔走揾食的狼狈相,常常在咖啡店解决一日三餐。他虔诚祈祷“羔呸店的头家能够找个马来人来卖咖喱。”得知家附近要摆粿条档,当作一件大事,记挂在心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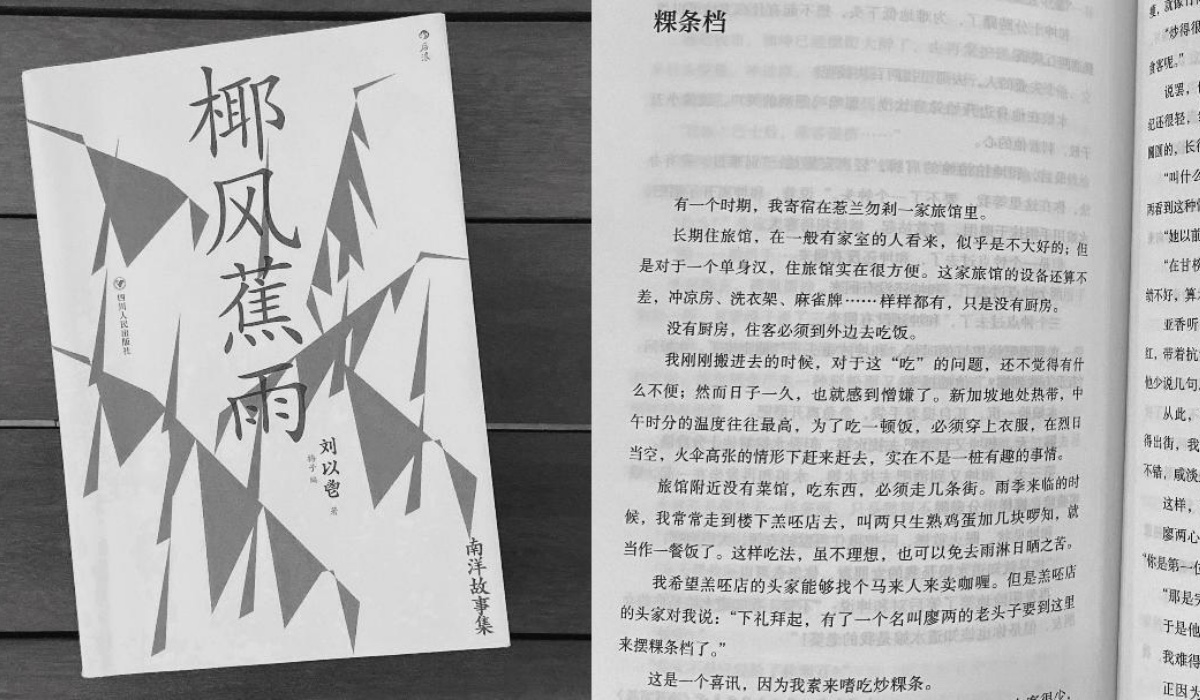
他在书里写情人间的约会,“到马来巴刹去吃沙爹”;“下午一点时候,请你到来歌梨城餐厅吃午餐。”小说的女主白玲则娇嗔地说,“又想看我割猪排的姿势?”在被白玲放了鸽子后,男主难掩惆怅,却不忘街边的一碗红豆冰。“冲完凉,长街已有不少来来往往的行人,热辣辣的阳光照得我心烦。我当即穿衣下楼,在街边的咖啡店里,喝一杯红豆冰。”

“在热带地区,穿西装多少有点傻相”
马来亚的天气,午后外出归来,人像刚从水里捞出来。如果像周慕云一样梳油头,恐怕发丝也是软趴趴地蜷曲着。报馆气氛沉闷,刘以鬯自有取悦自己的方式。看戏、约会也要细致打扮,“在热带地区,穿西装多少有点傻相,倒不如脱下上装,打一根领带,已算是相当‘隆重’了。”
刘以鬯在《链》中塑造的的陈可期也是个很讲究衣着的人,“皮鞋永远擦得亮晶晶的,仿佛玻璃下面贴着黑纸。左手提着公事包,右手拿一份日报,用牙齿咬着香烟。”与周慕云的装扮如出一辙。

刘以鬯在50年代的吉隆坡,最常读的是《南洋商报》,又常常以“葛里哥”的笔名在副刊发表作品。下班从报馆走出来,手臂间也许夹着一份《南洋商报》,无精打采走向云吞面的档口。

依照刘以鬯的兴致,草草结束晚餐后,可能会跳上的士,直奔戏院。歌梨城戏院正重映他百看不厌的《蝴蝶梦》。以前在上海,他常常去霞飞路的国泰剧院看戏。

“夜已深,大雨仿佛忘记了慵倦,街灯发射着凄怆的光芒。”车窗外大雨滂沱,50年代的吉隆坡,是一艘在大雨中前行的华丽邮轮。
“报馆里‘气压’很低,乱得像茶楼”
“生锈的感情又逢落雨天,思想在烟圈里捉迷藏”。刘以鬯笔下的文字总是潮湿的,混合着烟草的一丝辛辣。
《花样年华》中,周慕云在报馆一边深吸一口烟一边写字,时而轻抚着额头。烟雾在灯光里翻滚、盘旋、升腾、缭绕。
《花样年华》外,报馆编辑刘以鬯只身南下,怀才不遇。层层烟雾在手指间穿梭,纠缠不清。烟雾里翻滚的是苦闷、压抑、惆怅、愤懑。

刘以鬯是异域新客,在南洋流转于不同小报。50年代的南洋,时局不稳,报业和文坛成了各种意识形态角逐的重要场域。报业竞争激烈、命运多舛,刘以鬯常常面临报馆倒闭的窘境。
他在《星加坡故事》中描绘郁郁不得志的报馆编辑,将报馆形容为“乱得像茶楼”。“报馆里‘气压’很低,同事们因为支不到薪水,牢骚特多。”
又写道:“ 为了解决生活问题,开始撰写一个中篇小说,售与一家出版机构,暂时拿稿酬来维持了一个时期。”这些小说中的描写都是刘以鬯的亲身经历。高峰时期,刘以鬯同时为13家报馆供稿,每天写13000字。

他自嘲道:“我白天写娱乐别人的作品,到了晚上,有了时间,写我自己喜欢的作品来娱己。”
报馆是失去色彩的游乐园。他挽起衣袖写作,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耳边是否播放着他喜欢的“Kiss Me Again,Stranger”,“似诉似泣似叹息”。
“那些消逝了的岁月,仿佛隔着一块积着灰尘的玻璃,看得到,抓不着。他一直在怀念过去的一切。如果他能冲破那块积着灰尘的玻璃,他会走回早已消逝的岁月。”这是《花样年华》片尾荧幕上浮现的一段文字,也是小说《对倒》中的一段话。

遥想刘以鬯在50年代的吉隆坡,热腾腾的马来亚,湿漉漉的马来亚。人也被浸湿成一粒云吞,白里透红。在云吞面的档口,他满目愁云地咀嚼,一旁的《南洋商报》被卷成Swiss Roll。额头和发丝间已是汗涔涔,眼睛里也慢慢升腾起雾气,所有的记忆都是潮湿的。
延伸阅读:王茜专栏《马来茜亚》其他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