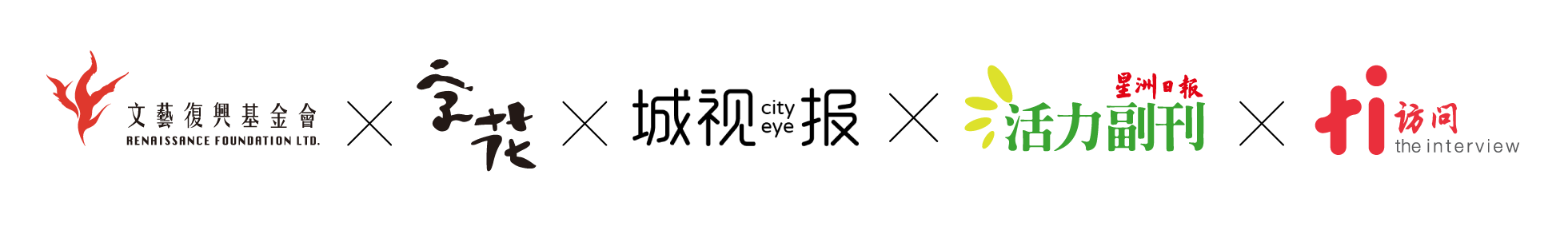我去看中医。中医问我,睡觉时是否常做无用的梦。我说,有梦,但没有无用的梦。她给我开了药,说是调理身体,也有驱散梦境之用。我带了药回家又不敢吃,怕吃下后会如杰克斩掉魔藤,从此断了我的梦根。后来还是受不了那痛症,只好冒险把药小心翼翼地嚥下,又在睡前看了套惊悚片(我每次在睡前看电影都会做梦)。幸好晚上还是做梦了,我暗自庆幸缪斯女神还是宽容大量的。
我在槟城做梦如吃药一样规律而频繁。两天前梦到一条闯进家里的小鳄鱼,昨天梦到对岸突然发生大火,滚滚浓烟噬掉蓝天的一角,而我入神地注视那如野人肆意跳动的火舌。有时候做的梦很普通,关于一个女孩躺在床上盖上被子做梦。或许那叫现实,或许那叫旅行。
我经过土库街又称银行街又称Beach Street又称Lebuh Pantai(听说这条街一共有六个中文名字),进了唐人厝。厝即屋子,又解作磨刀石。可唐人厝不像磨刀的石头,倒像一把磨得锋利的刀,走廊窄窄长长的,里面一个人也没有,安静得能听见爱丽丝滑下兔子洞的声音。一不留神,我又做梦了。梦里异常昏暗,地上尸横遍野,尽是支离破碎的影子。我往左拐进一个幽谧的房间,娇艳鲜红的极乐鸟花蛰伏在黑暗的角落里伺机而动,桌上一排土著木雕张开空洞的嘴,魅惑我去探索潜意识的尽头;墙壁上的镜子无限延伸折叠,陌生的符号拨乱着我的大脑回路。我往前走了几步,一个人影在走廊尽头晃动,我一回头,竟看到无数个自己。

我把这种迷离的状态归咎于睡眠不足和福柯的理论,还有属于外来者的异质目光。我尝试摆脱这种所谓“旅者的凝视”,直视眼前空间的真实面貌;但我背着一身疲惫的记忆,和渴望解读一切的欲望。我看到的是镜里过滤后的风景,镜看到的是我诚实的倒影。陌生化的蜘蛛继续吐丝,我掉进梦的罗网里,直至一切再次扭曲变形,以喂养我对城市的想像。
我拿起放在雨伞架上晾干的影子,推门离开。我知道今天晚上又会做梦了。
编按:“开故”作家育成计划是由香港文艺复兴基金会和文学杂志《字花》于2022年首次举办,为有志文字创作的朋友提供故事写作课程及指导,最终选拔一位优秀学员,于海外城市驻留,丰富其写作及人生经验。
槟城和香港都曾是殖民地,汇聚多种文化社群,同时在历史长河形成独特的华人社会,值得深入探索,故与《城视报》合作,带来优秀学员黄言丹,展开三个月的槟城之旅,产出《背着岛屿的人》每周专栏与《纸造人》短篇小说,于星洲日报、访问网、城视报三大媒体同步发表。
延伸阅读:黄言丹专栏《背着岛屿的人》其他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