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听过这么一句话吗——二十岁以前不相信社会主义,你的心是黑色的;四十岁以后还相信社会主义,你的人是不可救药的无知。
自我懂事以来,从山脚下出发,到过香港,去过东京,不间断的读书为学,超过十五年。虽然没什么成就,但自认书读得够多。但我必须老实说一句:我至今仍不知何谓左派、何谓右派。
我只知道社会主义(socialism)和自由主义(liberalism)。我把前者称为左,后者称为右,但今天的自由主义却不重视个人自由,而去相信社会主义者发明的“集体自由”。
我也知道大政府干预主义(interventionism)和自由市场(free market)。我把前者称为左,后者称为右,但今天很多所谓右派又支持大政府,左派又大谈资本主义。
世事如此错乱,我思来想去,得到一个结论:硬把世事强分左右,只会造成自己精神错乱。
胡适一百年前就说过:“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
不知是否因为中学时期读过胡适这句话,抑或出自一颗年少热忱的真心,我怀着一颗“研究问题”的心,到了香港城市大学读经济,尔后到了日本东京大学研究可持续发展。我保住少年热忱的心,化作仍在坚持做这件事的人。

求学时期种下的理想种子
二十岁以前我是相信社会主义的。
其实,与其说相信什么主义,一般人在少年时期都自然具备一颗热忱的心。这颗心,总是想要改变、总是想要挣脱,于是驱动着少年人去做事情。少年时期叛逆、冲撞、高傲,是这颗心的直接反映。这些是少年的本质,英文叫quality。
本质这种东西,是中性的,不好也不坏。若保守住本质,加以善用,则少年必定前途无量。
在中学时期,我的校长庄秀凤,就在集会及各种活动的演讲上,强调“梦想”的重要性。
当年开口闭口说“梦想”是陈腔滥调,岂知今天的学生连“空想“都保不住了,个个都很焦虑(先进的美国已有学者把研究结果写出来,即《失控的焦虑世代》,推荐家长们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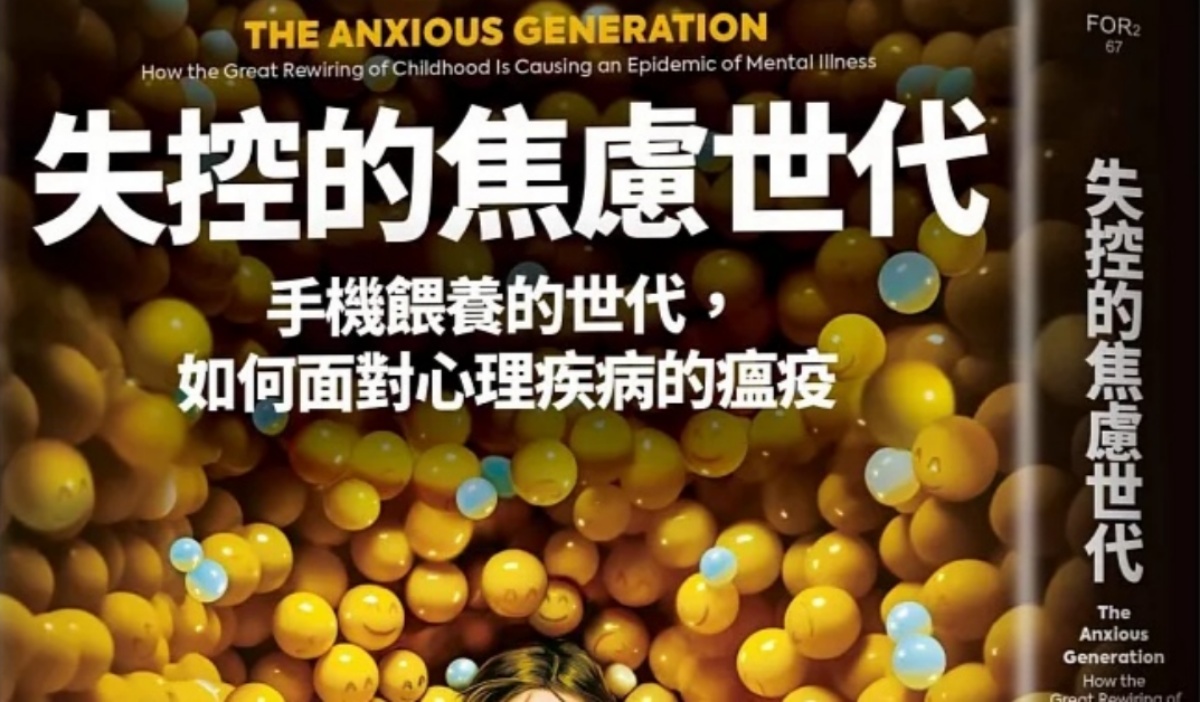
在我刚走进大学的殿堂时,我抱着满腔热血,到大学图书馆的书架寻觅“武功秘籍”。
当时我的偶像是切·格瓦拉(Che Guevara),我于是找到了他的几本著作。在那之前,我只看过《摩托车日记》。我在想,能不能通过多读几本他的书,来真正认识我的偶像的理念(对,当时没有AI、上网还很不普及,而我当时在香港漫游倚靠的是一本几百页的旅游地图书)。
当年我还没二十岁,但我的社会主义少年英雄已经让我失望。阅读切·格瓦拉的著作,我什么都没学会。在失望之余,我返回书架上,发现在找到切·格瓦拉的同一排架子上,放着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我至今都还记得那本书的主题——世人皆说知易行难,而孙先生则一反其道,主张“知难行易”。当时我简直拍案叫绝,喊出:对啊,不然我们来读大学干什么?正因为“知难”,我们才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知识。知一旦得,行自然易。求知,是为了让行动变得不再困难。
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思想,但不是充满智慧吗?不也是一种真理吗?
比起先是骑着摩托到处流浪,而后在山林中荷枪实弹打野战杀人放火的切·格瓦拉,中国的国父孙中山先生给我年少热忱的心种下了温恭俭让的种子。

在香港遇见我的经济学英雄
我大学主修经济学。教我们入门课的老师自己写了一个课本,买课本附送一张简表,上面摘录课本上出现过的所有供应与需求模型的不同变化。满纸的交叉图表,让我看不懂经济学到底在学什么交叉。
我有一位来自新山宽柔中学的学长,大概跟我有同样疑惑。他比我长一年,手上时时拿着书,却不是经济学课本,而是一名叫做张五常的经济学教授写的书。张五常在香港大名鼎鼎,著作等身,只是当时已退休。学长把这位学者介绍给我,打开了我一片广阔新视野。
张五常写了一套书,叫《经济解释》。当时是香港A-level(相当于马来西亚STPM)的经济学指定教材。里面只有文字,没有半个图表。满满的经济学知识,我甘之如饴。

张老最敬重他的老师,这些人后来都成了他的朋友;而他最好的朋友,反过来被世人误以为是他老师。这位好朋友是高斯(Ronald Coase,中国译为科斯)。
高斯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本来是英国人,后来移民到美国。他俩惜英雄重英雄,都毫不讳言彼此对彼此的影响。
无独有偶,高斯自认他年少时亦相信社会主义,但在求学路上,他渐渐发现一个血淋淋的事实——社会主义者仰赖大政府解决社会问题,但政府中人却往往更关心自身的利益,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是如此!
他原文这么写道:
“My socialist sympathies gradually fell away and this process was accentuated as a result of being assigned in 1935 at LSE the course on the Economics of Public Utilities. I soon found that very little was known about British public utilities and I set about making a series of historical studies of the water, gas, and electricity supply industries and of the Post Office and broadcasting. […] These researches were interrupted by the war, when I joined the civil service […]This war-time experience did not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my views but I could not help noticing that, with the country in mortal danger and despite the leadership of Winston Churchill, government departments often seemed more concerned to defend their own interests than those of the country.” —- R. H. Coase, Law and Economics and A. W. Brian Simpson
有良知的人,不可能不对社会主义深恶痛绝。高斯真是英国绅士(gentleman),他温柔敦厚地说:“在战争期间我所见的并没有真正影响我对社会主义的观感……”
伟哉高斯。

研究张五常或高斯的思想,不能帮助我们考试得分,因为大学课程更重视快速学习,完全不能招待思想慢慢的累积。但我在毕业后找工作面试时,都会提到他们对我的影响。我很庆幸,我自学的没有让我沦落成一个只会画图表拉曲线的经济技工,而是一位懂得两三条经济学真理的学生,终身受用。
另一位对我有很深刻影响的学术英雄,是经济学大师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他的两本通俗读物,虽然成书于半世纪前、讨论当时的美国社会,然而套用于今天的时势依然适用,放诸四海而皆准。
他在《资本主义与自由》里开宗明义,阐明自由主义(liberalism)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让他无法接受的是:传统的自由主义是主张市场经济的,今天这却被标签为保守主义(conservatism)。
他原文这么写道:
“Because of the corruption of the term liberalism, the views that formerly went under that name are now often labelled conservatism. But this is not a satisfactory alternative.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iberal was a radical, both in etymological sense of going to the root of the matter, and in the political sense of favoring major changes in social institutions. So too must be his modern heir.” —- Milton Friedman, Capitalism and Freedom
假如自由主义真有如此壮烈的历史渊源,那么今天美国所谓右派的反扑,不是弗老所寄望的吗?且慢,“知难行易”,先把全书看完吧!
弗里德曼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者。他的伟大,在于他钻进了象牙塔的巅峰,却同时走入人群,深入浅出的宣扬纯正的自由思想。读者若感兴趣,到Youtube搜他的名字,让你如梦初醒,或感当头棒喝的至理名言,俯拾皆是。

查理柯克的正面影响
查理柯克在十三年前得到一位有钱人的赏识,这名有钱人叫Bill Montgomery。
Bill劝查理不要读大学,而是去发挥查理最大的长处,并亲自出钱出力,帮查理创立一个非营利组织,即“美国转折点”(Turning Point USA)。
这个组织是干嘛的呢?其本质就是一个走进大学的组织——在大学里摆“言论擂台“,拉起“Prove me wrong”的布条,邀请大学生和教授们前来对社会议题进行思辨。
查理虽然不读大学,但他去过的大学比世上任何人都多。他自己勤读书,在擂台上不是乱七八糟的挥拳,而是有条有理的使出一招一式。他把自己的想法说一遍,让对方把想法说一遍;然后指正对方,也让对方指正。
查理心知,如果他能打倒对方,对方明天也能站回起来(“Anyone who is persuaded in one evening is not really persuaded. ”)。
但因为查理摆出了擂台,把自己深信的道理有条有理的讲出来,一遍又一遍,他就给愿意听讲的大学生形成了一种久长的影响(“You must turn the issues over in your mind at leisure, consider the many arguments, let them simmer, and after a long time turn your preferences into convictions”)。
请读者注意,我在括弧里面引述的话,不是查理说过的话,而是弗里德曼在通俗书《Free to Choose》里说的话。
查理没有半纸经济学文凭,却深得弗老的心。
一言以蔽之,查理的正面影响,在于他展示了一个人如何勤读书,把好的内容读进心里去,并且活出来。

像查理那样go to college
我在上一篇专栏文章说过:真理本无分左右。左右既分,真理何在?这是每个社会的有识之士应共同追寻解答的大哉问。
所以,我才号召大家:“go to college”——不是go to那些卖文凭的学店,而是要像一位college student,怀着无限饥渴的好奇心,多读几本书,好书重复读几遍,把内容读进心里去。
Go to college,就是号召大家多读书,提出些问题,一起研究;少谈些主义,也不要莽撞冲动,只须尽自己的能力把自己的真理活出来。
今天我已成年,但我仍不可救药的保有少年时期热忱的心,只是我不再无知。
今天的少年人,还抱着热忱吗?还有求知欲吗?他们正在受怎样的影响?
查理柯克在生时的作为,得到社会很大的回响,同时引起很大的反弹,甚至有人对他产生极端的厌恶,进而将他杀害。查理的嫌犯就向他不男不女的跨性别男同性恋者剖白,说自己受够了查理造成的厌恶(hatred)。

查理柯克是一位摆渡人,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我不是指暴力,而是指辩论),尽其力把年轻人引导到好的知识上面去。好的知识就包括弗里德曼的思想。
弗里德曼是真正的大师,其学术修养博大精深,其思想快如闪电,其辩才如洪水滔滔滚滚,深深影响了像查理这样的有为青年。查理只是希望更多的年青人可以和他一样受用于大师的影响而已。
在我少年时期,除了得到非常慈爱的中学师长引导,社会上也出现了一批“论道”的有识之士。这些人当中包括独立评论人,如唐南发、许国伟、郑丁贤;也包括朝野政党人士,如刘镇东、魏家祥。他们在电视上公开辩论,看得我热情滂湃,滋养了一颗少年热忱的心。
今天如有幸遇见他们,我必当面向他们重复的、真诚的道谢,尽管大家如今可能走在不同道上。
追求真理的路,必定是寂寞的。
采菊东篱下的陶渊明在隐居时,就有人劝他出山,说:“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意思是说:整个世界都一样,你为什么想不开?
所以,在追求真理的路上,必定有人来劝你不要那么傻,快快放弃。
这时,你必须像陶渊明一样回应:“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意思是说:你说得有道理,但我有我的坚持。
永远保有少年热忱的心,并义无反顾的告别无知。
▌延伸阅读:张恒学专栏《学而时习》其他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