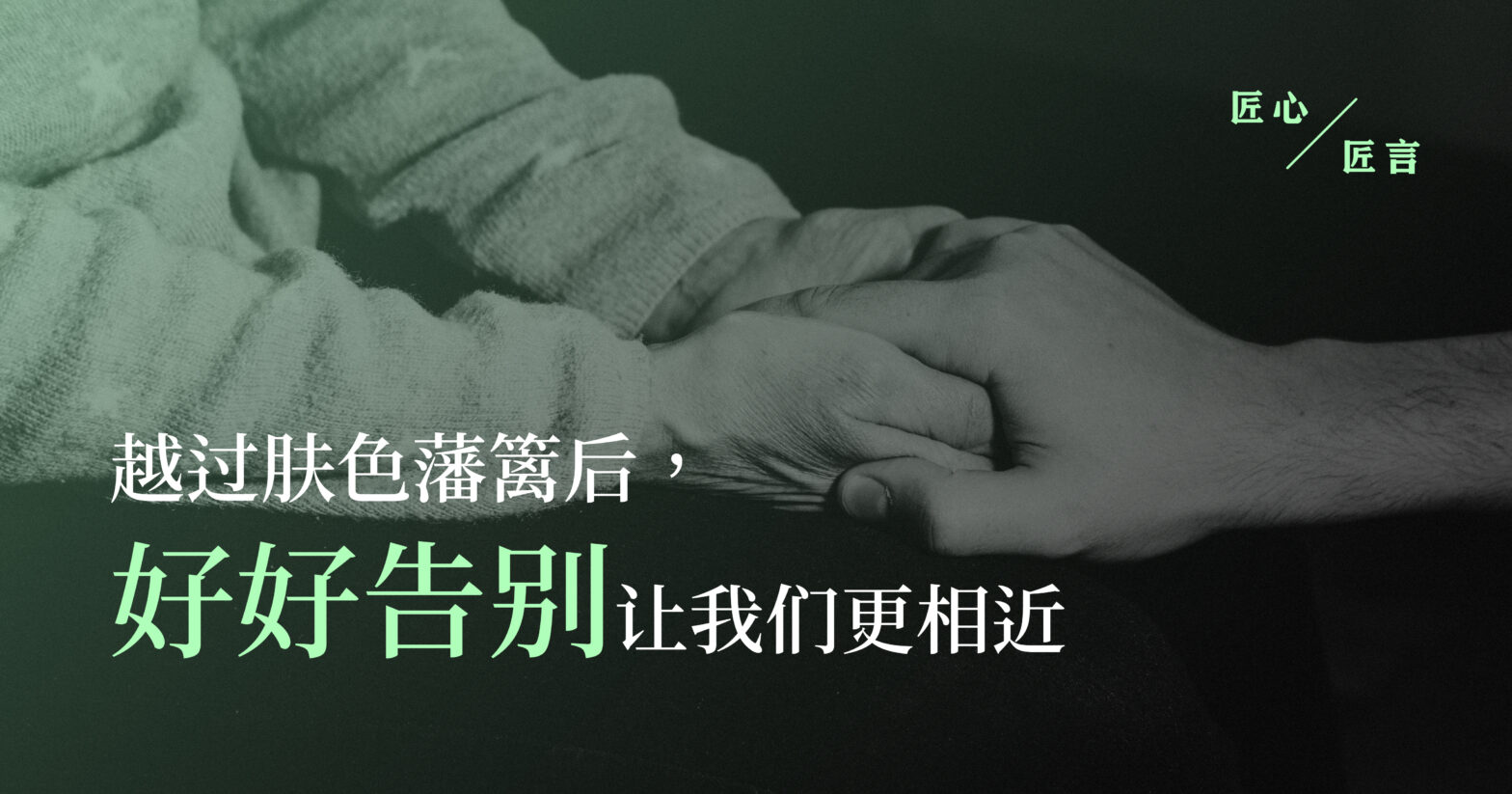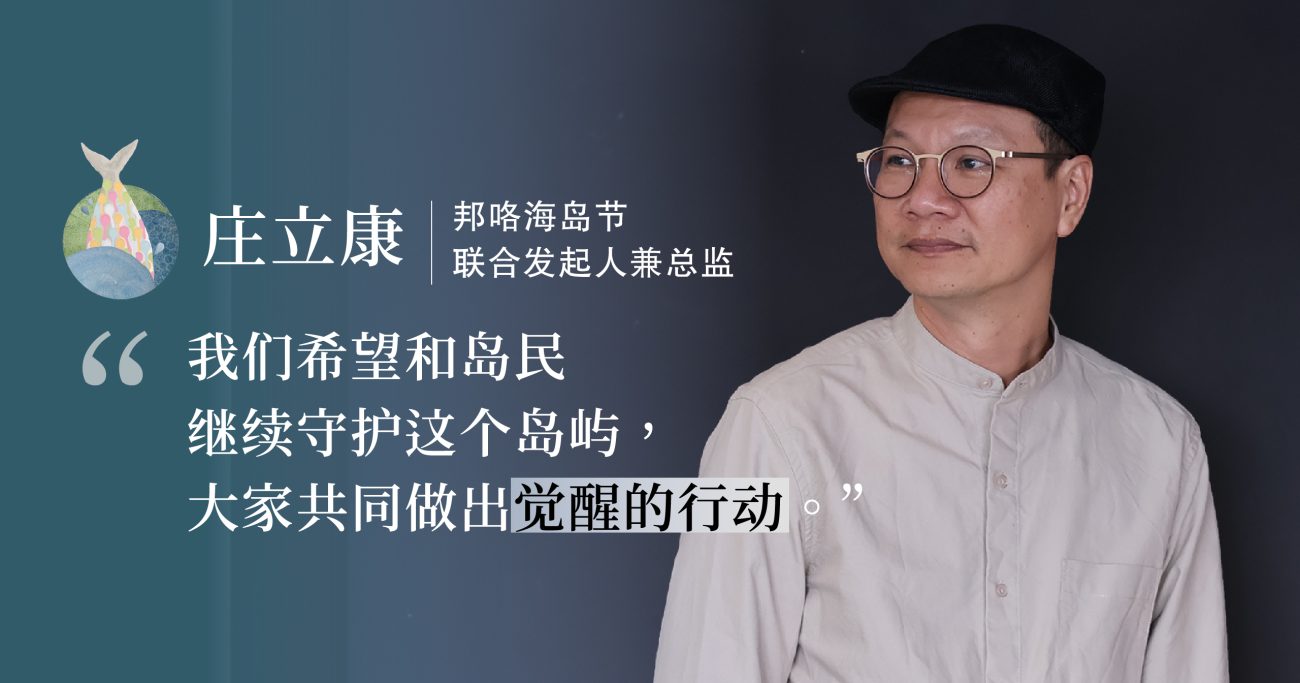我从没想过,有一天我会成为殡仪师,还是一名在华人殡葬业工作的穆斯林殡仪师。
第一次走进孝恩,我只是个兼职的服务员。就在不远处,我看到不同灵堂里,即使都在主持仪式——一个光着头、眉心平静;另一个却头发浓密,动作利落。当下我有些疑惑,问身旁的同事:“为什么他们的样子这么不同?”

同事解释说:“没有头发的和尚是佛教的师父,有头发的是道教的。”每次讲回这件事,都像闹笑话。但对华人习俗一窍不通的我,竟然当上了殡仪师。
那一瞬间,我觉得仪式很有意思。我没想到,来自另一种文化的我,会在这里被自然接纳,也被给予空间学习与参与。那种尊重,是我后来回头看才发现的珍贵。
学会新的语言 陪伴家属
父母会反对吗?他们只是说,“看你自己”。当然也要分得清,工作与信仰的界限。只是我没想到,这条路一走就是七年。
七年前,我连华语都不会,更别说广东话。很多老人家、师父都讲广东话,我一句也听不懂。家属看到我是马来人,难免会质疑;我理解那种担心,但也只能用行动来证明。教他们上孝、引导上香、鞠躬,解释仪式的意义、提醒细节……

师父念经,我看不懂那些字,就跟着拼音读。时间一久,对经文的起伏和音调比较熟悉,都念进了脑子里。有时,家属跟不上师父的速度;我就站在旁边,用手指着经书上的拼音,小声提醒:“到这里了。”
慢慢地,语言不再只是工具,它成了我跨过去、靠近他们的一座桥梁。
仪式教会我的事
华人的祭祀仪式里,有很多细腻的讲究。比如道教的灯笼,一个写名字,一个写岁数。
福建人的供桌会指定放青苹果;道教拜荤,佛教拜素。
孕妇不能随便靠近棺木,而出殡前要准备一对筷子,以及一个包着姜的红包。若是出殡之后姜还没坏,就拿来煮水给孕妇喝。筷子则要一直收着,直到孩子出生后吃的第一口饭,就用上它。
这些习俗看起来繁琐,却都是家属表达爱、保护与祝福的方式。也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我开始理解,殡仪师不只是执行仪式,而是守护这些意义的人。

你可能还是会好奇,殡仪师究竟是做什么呢?从接送大体开始,搭灵堂、摆供品、送殡、火化、收骨灰,到最后盖上骨灰瓮的那一刻——对家属来说,那是最后一次告别;对我来说,则是一份交托。
让人心里舒服
城市里的仪式有一套标准的流程;可一到偏乡,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
有些地区的殡葬生态较封闭,外来团队会被视为竞争者,气氛因此变得紧绷。有时他们会用言语、举动来制造压力。
那些夜里,我们必须安抚家属情绪、又维持仪式顺利进行。内心其实紧张,但我们不能让家属察觉。
做殡仪师,始终有种微妙的感觉——你明明在处理死亡,却必须让活着的人安心。更重要是让他们感到舒服。
殡仪师处理的,其实正是与人的关系。人心都是肉做,安抚人的情绪,永远比设置灵堂、安排仪式难得多。几年前,一个丈夫去世了;一年后,儿子也走了。出殡那天,原本一个完整的家庭,只剩下妻子一个人挨在棺木边。
到了即将出殡的时间,我们原先要准备封棺仪式。但那位母亲抱着儿子的棺木,哭得整个人像是散落的骨架。
半小时过去,悲伤像浪,还在暴打海岸。我们站在旁边,久久未能封棺。

那时我突然想:如果棺木里的那个人是我,我的父母会怎么样?那一刻我第一次意识到,即使信仰、文化或背景不同,失去的痛其实都是一样的。
说最后一次话
做这份工之后,我像是彻底变了另一个人。以前,我的脾气比较暴躁,也比较少打电话回家。但在那之后,我好像变得比较柔软。在处理家属的丧事时,也总会想到老父母。
我们没人知道自己的时间。
很多年前,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却因为一点小事吵架了。情绪在我们心里发酵,一两日过后,因为内疚,决定晚上去找他吃饭。到了他的家,门打开,我问他妈妈:“Ibu,Aiman在哪里?”
“Aiman 不在。”妈妈说。
我以为她说的是Aiman出门了,直到她说多了几次,眼泪忍不住流下来,我才知道她说的“tak ada”,是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我很生气自己,生气在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并没有对他好一点。他就这样在睡梦中离去。我每次都在想,为什么要吵架呢?想要和好的时候,人家已经下葬了。

后来在封棺之前,我都会给家属一个一小时的时间。在灵堂里,只剩下他们以及自己即将永别的亲人。有什么想说,但曾经不敢说的,就在那个真空时间里完整说出来。
这次错过,即是永别了。因为离开的人往前走,就再也不回头。
人生没有U转
很像我们开灵车。开灵车有一个禁忌,就是不能U转。所以很多时候在“游街”之前,我们会先去熟悉路线。而我很记得自己第一次开灵车的那一天。
平时,灵车上有司机以及家属。但那一次,死者单身,因此二十几分钟的路程只有我和他。紧握方向盘,车子尽量平缓前进——可偏偏在行驶期间,车后突然传来“砰”的一声震响。
我的心跳得很快,只敢用眼尾偷瞄望后镜。心里反复念叨——“拜托,千万不要起来。”经历了一阵内心风暴,事后才弄清楚,是因为有个锁没扣紧。
那之后,我花了一年才真正不再恐惧。为什么人会对死亡恐惧?很多时候是因为不了解。当你知道自己是在帮他完成最后的路,你就不再怕了。
我太太也怕,总是担心灵魂会跟着回来。我说,不需要怕的,我们做的事是对逝者好。除非你做亏心事——老一辈常说,才会怕“跟你回家”。
过了几年,她也安心了。
后来我才明白:所有宗教,最后都是教人善良、教人好好告别。
而在殡葬现场,我亲眼看见不同文化的人都在做同一件事:用自己的方式,送爱的人最后一程。原来,我们比想象中更接近彼此。
编按:本文乃作者口述之内容,由访问网记者梁馨元撰稿。
▌延伸阅读:《匠心匠言》其他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