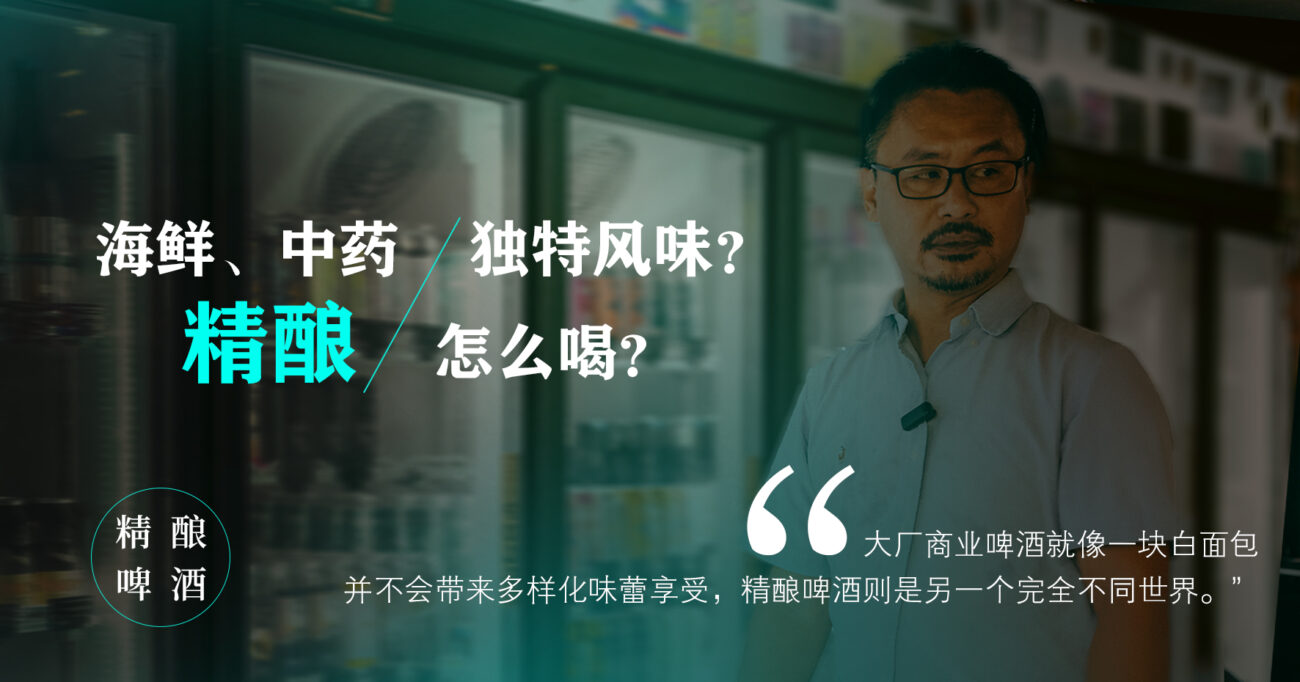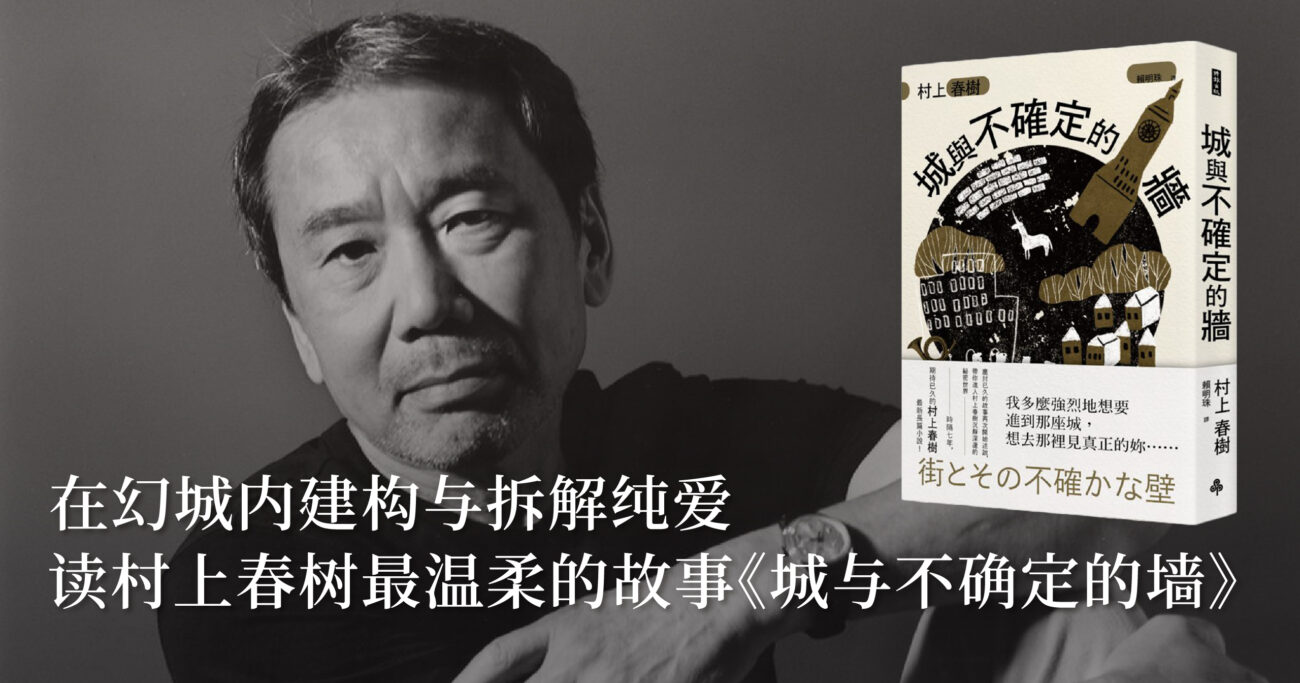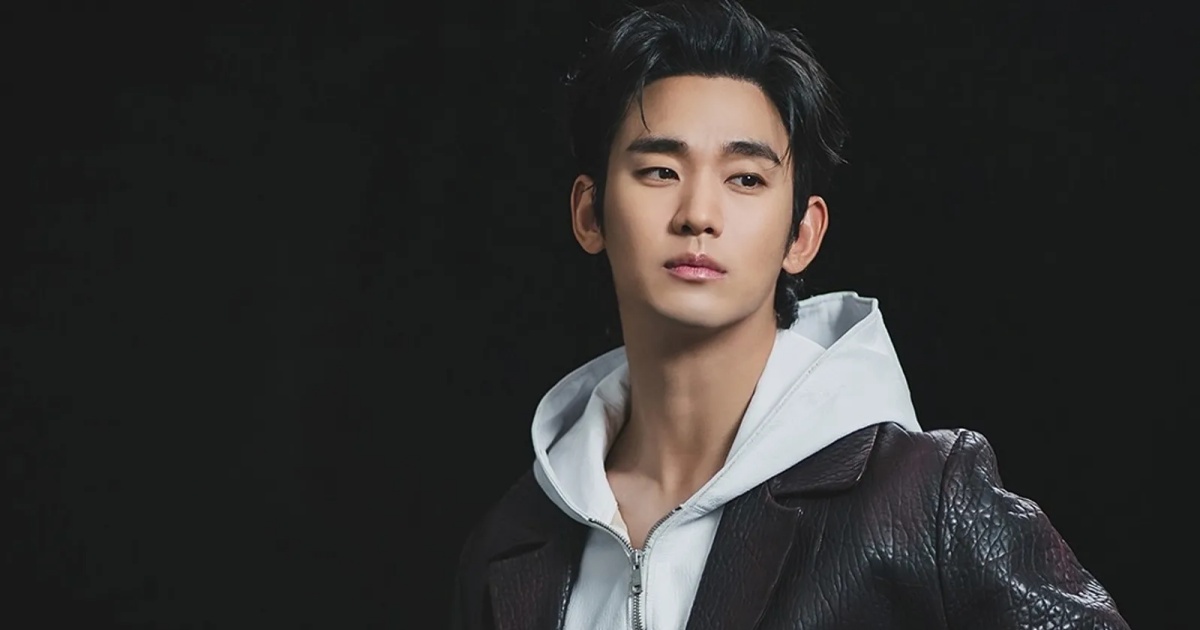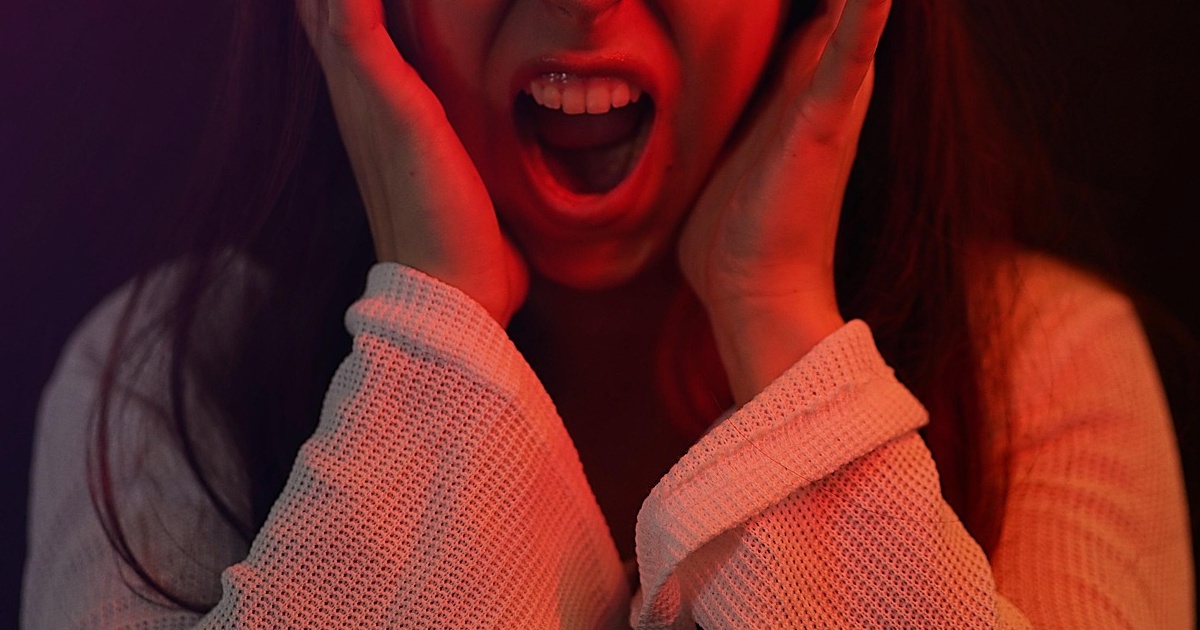听天汤,2021年改组于台北的摇滚乐团,前身为2012年成立的显然乐队,现由主唱兼合成器阿琺Alfa、吉他手Angus和贝斯手许升睿组成。
如果要用一句歌词形容显然乐队与听天汤,便是〈这一切都是假的〉中,“众神的阳台偶尔也会孤独/对街的地狱飘来了歌舞”。歌者与歌者的眼睛身处低处,透视天堂之外的寂寥,以歌唱对其进行批判或赞颂,阿琺妩媚的声线诠释世间的苦痛与洒脱。这一种美,似乎比天堂纯粹无瑕的乐曲更加悦耳。
〈低贱的人〉与社会竞赛之抗衡
某天点进阿琺在TedxTalks平台上发表的演讲“给不想比赛者的比赛”,其中提及〈低贱的人〉歌曲与MV制作过程。这是我发现显然乐队的起点。
人生仿佛一场永无止境的比赛,一场征选,一种不靠近顶峰就是向下堕落的攀爬。就连独立音乐这个看起来如此自由的领域,也会在团体起步之际与其他乐团竞争拿下三十万到八十万不等的补助。“写音乐之前先写企划书”,这是独立乐团必经的第一个比赛规则。边念研究所边起步玩团的阿琺,无比厌恶人生中种种无法逃离的比赛,于是写下〈低贱的人〉,“让我做一个愚蠢的人/避免知识和权力之间的矛盾/让我做一个低贱的人/用劳碌向资本家交换应得的青春”。
这首简单录下的歌曲在网路上红起来,而靠着流量、商演和贩卖周边带来的收入,显然乐队在成团第四年发行第一张专辑《我最讨厌摇滚乐》。《我最讨厌摇滚乐》,以摇滚乐本身为载体批判摇滚乐商业化,指控独立音乐复制娱乐产业生产明星的方式,并且尝试真正地描写社会底层处境。随着专辑在主流平台上卖得登上排行榜,则引发了阿琺的第二个疑虑——“我原先想颠覆的东西,会不会实则在自己的商品中,不断被复制?”
于是,阿琺决定利用比赛第二回合的规则——拍MV,当作回到理念正轨上的一个转弯。〈低贱的人〉MV制作,以类似艺术计划的方式,通过MV影像创作比赛,征集与主旨契合的影像。显然乐队发布的公告中,设定素材限制而不公布评分标准,最后却是采用最不符合当初设下的“比赛规则”之作品。如此举动,反映出人们在社会规训之下,对于“比赛”的弔诡预设——“比赛”最终要采用的,一定是最好的东西。荒谬的MV征件与“颁奖典礼”引来一波攻击和舆论之际,实则带出的拷问是:当这场荒谬的颁奖典礼结束,回到现实中公司里、学校里、社会上,一切有形或无形的比赛和规则,难道就不荒谬吗?如此呈现方式打破第四面墙,贯彻歌曲〈低贱的人〉主题之精神,让听众碰触社会竞赛无时无刻深植在人们心中的肮脏现实。
回到歌曲本身,“你长大以后要做个读书人/嫁个好老公过幸福的一生/大家都想要做个有钱人/那谁来刷油漆,谁来擦地板/谁来当他们脚底下的穷困”,几句歌词写出社会普遍对“成功”、“匮乏”的刻板观念,以及定义之落差。然而,值得思考的是,如若人们要复制所谓的成功,需要付出多少自我,作为接近权力结构顶峰的代价;而歌词中所描述的“他们脚底下的穷困”,往往是社会底层所面对的困境与现实。
显然式浪漫:对立里看矛盾,脏污里找光亮
从显然乐队到听天汤,歌曲中从不消失的是对立、讽刺之叙事,构成一种诡谲的美,并且在这样的美感中,向现实、孤独、爱等命题发出叩问,题材或大或小,共同点是包覆在矛盾且具有两面性的底色里头。私心选择〈钥匙掉了谁来救我〉、〈这一切都是假的〉与〈夏天的夜里没有晚风〉,为显然乐队歌曲的特色做出解析。
〈钥匙掉了谁来救我〉首先以墙外人的视角,描绘无法进入家里的焦虑情绪,却也以全知视角写下墙内人所面对的险恶与悲哀——正在拟定遗产争夺计划的二楼夫妇、女儿从没来探望过她的一楼老奶奶、吵架了往窗外扔家具的三楼情侣。仿佛福柯的全景监狱,屋里的人们在用钥匙把门打开、踏入屋檐下那一刻开始,便被仿若不在场的命运支配而不自知,往后被世俗在身上打下的烙印所禁锢,在自己的屋子里把钥匙丢了,已然走不出这个空间。“我家的门被自己反锁/钥匙掉了钥匙掉了谁来救我”,“几个爱过我的穷小子/没办法为了理想而死”而无法与理想主义的“我”缔结,种种缘由使“我”无法找到钥匙。如此,墙外人渴望墙内的生活,却无法走入屋檐下,会不会反而是一件好事?
〈这一切都是假的〉和〈夏天的夜里没有晚风〉于2020年释出,曲风开始在早期摇滚的基础上加入慵懒的调性,类似从显然到听天汤的过渡。
〈这一切都是假的〉,从歌词、编曲到阿琺吟唱的间奏,以及MV中踏出的舞步,皆是飘渺的。“忘了注意的时间/从我手中溜走/这一切都是假的”,“忘了游戏的分寸/开始互相追逐/这一切都是假的”——如果这世界曾经让我们感到幸福,或伤害过我们的一切都是假的,我们对这些事物的观感会不会因此有所改变?“众神的阳台偶尔也会孤独/对街的地狱飘来了歌舞”,当主观情感凌驾于在一切事实之上,我们对事物的观感其实只在于一念之差,就如众神的阳台与地狱,实则只隔了一条街道,孤独与欢庆也仅是因为自己的选择而得到的结果。
〈夏天的夜里没有晚风〉中,“把杂乱的修一修变的朦胧/把老旧的放对位置变成复古风/剩的烟还够今天抽一口接一口/冰箱里没有食物但至少还有酒”,移动家具、抽烟、冰啤酒,是尝试逃离闷热沉闷的夏天乃至生活,而做出的举动。“艺术圈的朋友过得像上班族/上班的朋友都在谈论艺术”,则写出每个圈子的人都过着与外人视角看来有所落差的生活,并且多少渴望从自己的圈子的枷锁中解脱。而“我什么都不想管只想去爬山”,是歌者在生活一切束缚之中做出的一点抽离;“夏天的夜里没有晚风/生而为人只求做个好梦”,也只是现代人在纷扰日常之外的一点点奢求。
歌里种种对立与矛盾的叙事,糅杂造就一种“显然式浪漫”,即是把一切看似不应同时存在的词句摆设在同一个场景之下,营造出一种冲突的美感。世俗意义上的美,是无暇、陈列完好且在光亮之下供人观赏的;但在脏污之中发现或创造的美,更是得来不易,是显然乐队在世界洪流中呈现的面貌,也是他们的声音不易被沖刷之理由。
从〈帝国〉到〈新帝国〉,调制尖锐中的优雅
伴随新成员加入,听天汤成团初期的贝斯手Ken拥有爵士音乐背景,乐团的音乐风格开始加入爵士与蓝调元素。〈帝国〉与〈新帝国〉的对比,或许可视作显然乐队跨越到听天汤的直观变化之一。〈新帝国〉沿用〈帝国〉的歌词,在一切转变之中,听天汤一样唱着“你是我的太阳/把你挂在我城墙/已经开始想像/你渴望我的模样”,保留显然时期的尖锐强硬,但编曲变得柔和许多,并且在渴求拥有外物的基础之上,加入充满自尊的诉求:“贪心不足/吃不完的都叼走/与日俱增的爱/值得开采”,“喜欢我就说/不要成天欺负我”。你可以作为狂风暴雨袭击我的生命,前提是你也必须如我爱你一般爱上我,并且我的骄傲允许你留下。
听天汤首张EP《财富自由身体健康》,是因疫情引发的生存之思考。其中歌曲〈楼中楼〉,不断重复吟唱“鱼儿水中游/鸟儿笼中囚/富贵险中求/和平东路上的楼中楼”,写出年轻人在台北追求理想的缩影。多少人“明明已是生者却烦恼着如何生存”,“神没有手人类才能负责创造”,但这种创造究竟是为了基本的生存,还是为了自己真正希望创造的事物?在遇见同路人时,又怀抱“当这样的我给你拥抱/你会高兴我们终于遇见抑或浑身上下拍脏”的疑虑,但人们终究因为看见对方身上的共性而接近,“只因你是心灵丰富的孩子/造你以探索总要你打先锋/所以容易被磨耗/给你⼀整个拥抱/能否让我们都不致于太潦倒”。为了喂饱肉体与精神,年轻人们在生计与人际之中穿梭,期许为自己编织出一个接近美丽结局的故事。
〈骆驼〉这一单曲,则像是一种与乐团起点〈低贱的人〉契合的显然精神延续(或者说,这种精神贯穿显然乐队与听天汤的音乐,从未走远)。“物尽其用/人有家可归/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别管谁剥削谁”,道出产业中上位者之心态,将创作者的才华当成剥削以及赚钱的工具。而“沿路的山/金粉在闪烁/沙漠在呼唤/呼唤我呼唤我”,创作者为了理想的呼唤,踏上眼前闪耀的道路,仍有可能面对“投资有赚有赔/人生有笑有泪/只怕到时候有人反悔”的情境。
2024年,听天汤发行了第一张专辑《同年同月同日死》,我认为其中〈别停在这里〉最能体现绝望之下的优雅。歌曲中不断重复“别停在这里/无动于衷”,无论靠近的是亲吻、阳光,或是牢狱、死亡,都别停在原地,因为生命只能往前。所以,在我们还渴望活着时,“给我一个吻/让我沈迷其中/对我说个谎/让我忘记苦痛”;我们也可以为死亡提前做好预备,以便拥有一场得体的葬礼,“送我一首情歌/让我在牢里能歌唱/为我挑件礼服/穿来我葬礼上/别停在这里/望着橱窗”。这样的歌咏,仿佛是在对命运低语:我来世间一趟,只是为了在顺境逆境中都能够以自己的步调享乐,根本懒得作出所谓抵抗。
纵观听天汤时期的音乐,在描述哀伤和愤怒的基础之上,加入一种“你奈我何”的慵懒,优雅的剂量又被增加。从显然乐队到听天汤,流动的能量看似负面,但正是因为眼睛足够通透,直视了这些因现实而生的谷底,才建构出真正无须外物衬托的生命力。而这种生命力,在〈楼中楼〉“可我们都忘了在灵魂那通透玉润的光带进生活/忘了本来我们都会发光/不再需要钻石、美妆、镁光来添加/因为想要有光那里就有了光”、〈儿童〉“而纯真并不依赖刻意守护/我们发芽的那一刻已经成为了树”等歌词中,皆有所体现。
这支来自台北的乐团,总是让我想起骤雨连绵的十一月末,从阳明山林语堂故居俯瞰台北市区的阴天。我想显然乐队与听天汤带给我的感受,是年轻而潮湿的眼睛,偶然站到高处观望万家灯火中每一个渺小生命流动,进而凝结的种种心得——也正因为年轻,有不易磨损而无法隐藏的尖锐,以及未经过多修饰的真实。
最后,“就让我们相濡以沫/如果他的存在是为了实验/验证每⼀个⼈都有⾃己的专属地狱/即使空洞还是光鲜亮丽/失去作为普通的权利”。在种种竞赛之下尝试接近世俗,却发现自己在世俗中无法认可或不被认可的地方而自愿拉开距离,展现外表或思想上的差异。即便被人们视为不务实、看起来过于离地也无所谓,人生本是一场无须预设结果的实验,在这个过程中,年轻的人们逐渐通过选择,将往日向往的自我逐步建构起来,便已经达到意义。换个角度来看,人生最重要的仅是在脏污和纯粹中来回穿梭,只要有一个当下让自己觉得触碰世界的真实面貌(无论是丑陋或美丽的一面),便已达到体验的目的,无须为其赋予意义。
而低贱和优雅、脏污和纯粹,它们真如字面上的意义,是对立而不应并存的吗?——显然乐队和听天汤,已经用他们的音乐,告诉我们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