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宝法王噶玛巴的桃色新闻,在信众的心间掀起滔天巨浪,也让我再一次对自己的“毫无感觉”,有浅浅的好奇。
我对西藏喇嘛犯任何所谓的戒,都没有感觉,也向来升不起批判心,仿佛那是天经地义的,本来就没有守得很严,假象是人们要的,是制造的。
西藏民族的集体有他们自己的价值观,食肉不食肉,男女不男女,看他们出得了那么多双修佛像和唐卡,就知道那是DNA里的东西。
我不认为一定要用力去依照华人或任何其他民族的道德标准去批斗,才显示得出自己的⋯⋯什么?要显示什么?
只是离开了西藏,到了别的地方,就得由那个地方的标准来衡量,到了国际,看看有没有一个国际标准,要安身立命,就得守戒。

是僧人就守佛陀的戒最干脆,天下太平。
喇嘛的淫欲之盛,我也见识过,只是当时我无知而天真,对宗教代表人物怀抱无性天使的梦幻想象,不知自己身在虎口边缘,但我命中有守护者。
那时我在印度南部一个人流浪,吃午餐,两个青壮年喇嘛来搭台。我一见喇嘛,心生欢喜,十分恭敬,多少年修得与喇嘛同台吃饭,很超然似的。
两个喇嘛身边跟著一个洋人,美国人吧? 他一句话都不说,我不晓得他是跟喇嘛学习的还是做事的还是干嘛的,总之他静静在旁边。
吃完了饭,喇嘛说,他们就住在餐厅楼上的旅社,邀请我上去坐坐,他们祝福我。
噢⋯⋯我那不可告人的纯洁少女心,马上说好哇好哇我们走!
进到房间,喇嘛说,来,床上坐。
我觉得好奇怪,女人噢,不应该随便坐别人的床,祖母有教的嘛,但喇嘛是神圣的,他们叫我坐床可能有神圣的意义咧?
我就坐床沿,两个喇嘛各坐一边,把我夹在中间。我开始感到不安,说不出来的不安,但心中对宗教代表人物的刻板神圣想象,瘫痪了我的女性自我保护本能,我想不到东西,心理退行,变成非常幼小的女孩子,无法反应现实。
那个洋人,就坐在床前的单人沙发上,静静看著我。
喇嘛在和我聊些有的没的,我觉得他们靠太近,很怕,但依然不能决定这是什么状况。
最后,我的莫名恐惧胜利,我要出去,我不想被什么神圣的喇嘛“祝福”,我还是做个没有福气的孤独者比较好。

洋人一直盯著我。
我软弱的嗫嚅: “我想走了,谢谢你们,我有点事……” 话才说完,洋人唬的站起身,立刻打开门,我冲出去。
离开的时候我还很难过,觉得自己好没用,好丢脸,充满了对自己的不喜欢,根本不敢去怪罪什么人。
就这样。
女人傻起来,可以这样。
我甚至不能明白,洋人的意思是什么,他好像很不喜欢我在那边,我很幼小的女孩子心理,不太理解他的爱护。
那是西洋骑士式对女性的保护。
同时,他也有他的挣扎吧? 西洋人进入东方宗教,困惑会很深。
我的法国老公马修也被印度神棍伤过心。
我依然不晓得,要怎么去批斗喇嘛的行为。
西藏有西藏的开放面向,在印度,女性的不受尊重也很惊人,我一个人走来走去其实很危险但我不知道。我一直遇到很善良的人。
大宝法王噶玛巴的这个桃色新闻,我不讶异,虽然过去我曾经渴望,再流浪一次,去见法王。噶玛巴千诺。
纯洁的想象早就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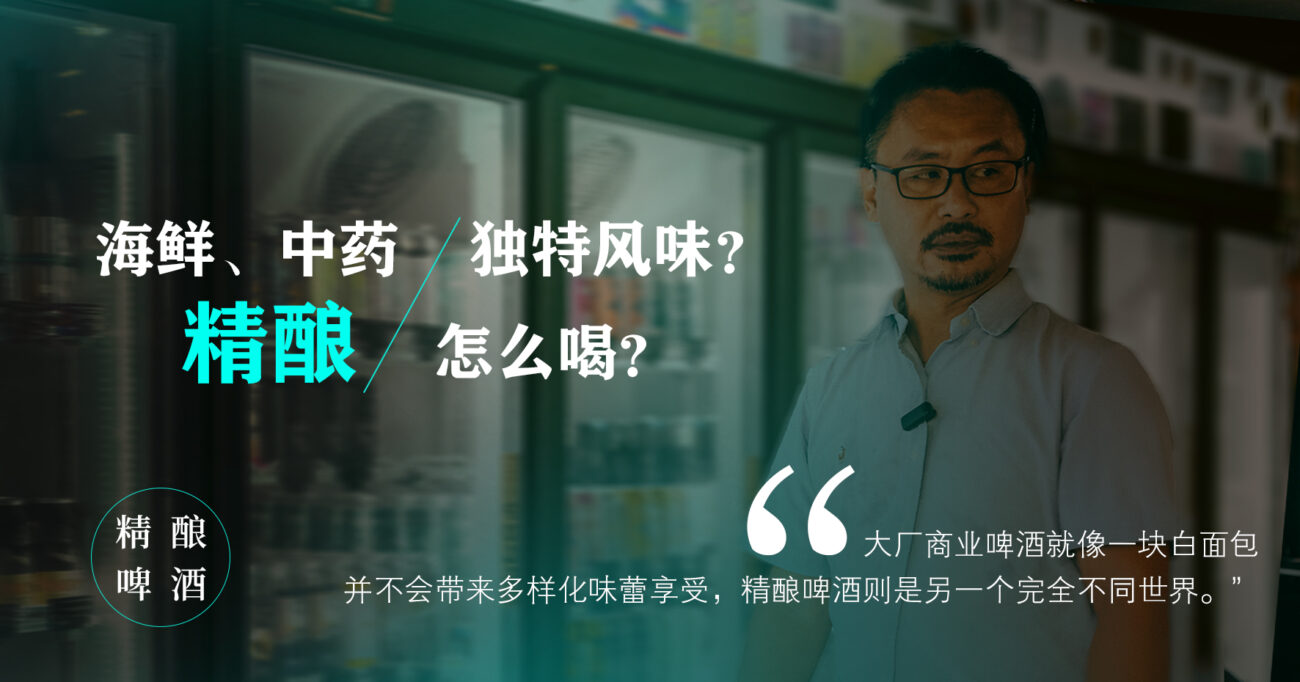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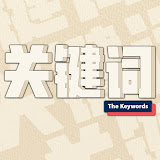














还没成佛之前 还是人,跟平.人無疑。只是修法方面比常人多点智慧和精进。
你可以不用想像,而是實實在在去了解佛法。看得出,你並不了解藏傳佛教。